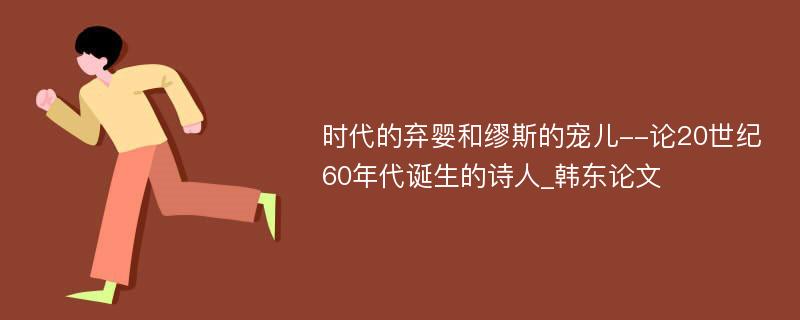
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试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宠儿论文,试论论文,诗人论文,年代论文,缪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朦胧诗之后的诗歌格局中,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一直是一支核心力量。无论是在198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还是在取得了坚实成绩的1990年代诗歌中,这一代诗人都担当着主要的角色。在新诗史上,还从未像在这代人中那样涌现出这么多才华卓异的诗人。联系到这代人精神生活上普遍简陋的起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当代精神生活史上一个巨大的奇迹。但是存在的逻辑在世纪末再一次显示出其吊诡的一面:这一代诗人还没有来得及作为一个整体登台亮相(第三代诗歌虽然以“代”命名,但也只吸引了这代人中的一部分诗人),许多优秀的诗人仍旧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迫不及待的一代新人已准备将他们送入历史的冷冻箱。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70后”迅速成为文坛新宠,并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占据了人们的视线。当这些比他们晚了整整一个年代的新人在文化市场上一夜闯红,不少1960年代出生、已有十多年写作经历的诗人甚至还来不及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付梓。
批评面对这代人的精神创造时的失语,既有这一代人的文化姿态方面的原因——他们的精神气质更多地倾向于内敛而非张扬,他们的文化策略与其说是功利的,不如说是超功利的——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代人“精神本质上拒绝被‘命名’”(张新颖语)。对这代人的命名似乎只有参照他们前后几代人的关系才能勉为其难地进行。“第三代”是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自我命名,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在一本最近的诗选中,他们被称为“中间代”;而有人干脆将他们称为“无名的一代”。与他们的前后几代人相比,这一代人都显示了某种特殊的性质。
不像他们的上几代人,我们很难给这一代人指明一个公认的共同特征。他们的价值理想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个人烙印。他们也从未获得一种能够使他们互相认同的共同经历。不妨说,缺少共同特征正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特征。对他们来说,个人的价值不是依附于“代”或集体的价值,而是由自我创造的。这正是他们自信的理由,也是他们成年后着迷于艺术创造的重要原因。这一代人不但拒绝被“命名”,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他们不允许自我冰释于这种盲目的认同。他们的上几代人大多走了一个水流归海的过程,他们却努力挣脱大海的怀抱,还原为一滴水。对此,张新颖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他认为由于这一代人“没有旗帜,不能为某一目标聚集成一种力量”,因而“很难形成一种自己的话语系统,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自我表达就极其困难,往往需要‘借用’其他几代人的方式来勉强凑和,常常言不及义”(注:张新颖的有关论述,转引自《“60年代”气质》(许晖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0页。)。
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代人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漫游的气质,甚至梦游的气质”,“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从而使他们成了“历史的观看者”[1]。在他们前后的几辈人中,这代人似乎最缺少行动的渴望和热情。与其在盲目行动中耗尽精力,他们宁愿将激情挥霍在唯美的享乐中。这一切使得这一代人天然地具有诗人的气质。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学课本中的几篇毛泽东诗词,竟唤醒了那个沉睡在这代人身上的诗歌灵魂,成为不少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写作生涯的起点。早期教育中的这种欠缺,固然对这一代诗人的文学修养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好处:在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中没有混入任何先入为主、模棱两可的成见。当这代人第一次与文学遭遇时,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判断的能力,中外古今的斑斓的文学成果几乎同时地显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空白的心灵状态使他们可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平等地对待这些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们日后全面的兼收并蓄的文学修养便起源于这样一种看似偶然的契机。让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这一代人的文学修养几乎完全是自我教育的结果,而这一过程紧密联系着他们追寻自我的精神历程。
这批诗人毋须成为一代人的代言人,他只要成为他自己、完成他自己就行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最易于催化诗歌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会从这一代人中涌现出那么多优秀诗人的原因。肖开愚、陈东东、韩东、吕德安、臧棣、西川、海子、骆一禾、张枣、黄灿然、桑克、王寅、哑石、清平、麦芒、潘维、黑大春、朱朱、周瓒、叶辉、丁丽英……个个名字都是那么掷地有声。
二
这代诗人开始其写作生涯之际,正是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思想、意识空前活跃的时期。他们身历了开始于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目睹了各种思想的交锋和激战。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激发了他们日后对精神领域进行探索的潜在勇气,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在文学上,那时正好是朦胧诗开始广泛传播并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的时候。从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意识演化的过程来看,朦胧诗有两大功绩: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唤醒了人的自觉;在文学层面上,它还是文学的自觉的起点。正是在这两个方面,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朦胧诗的传统,把一种从朦胧诗萌芽的写作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灿烂的写作局面。
这一开始于朦胧诗的人的自觉化运动,通过这一代诗人的努力,演变成了一个推动当代诗歌发展的不断深入的文学的个人化进程。韩东通常被视为一场旨在颠覆朦胧诗的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然而,他穿越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旅行还是起步于朦胧诗的历史的终点。在一篇早年的文字里,韩东写道:“只有作为人的真实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人在艺术中具有无可比的意义。作为人的真实是永恒的。”(注:韩东:《关于诗的两段信》,载《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124页。) 这种对人在艺术中的意义的反复强调,恰恰是对北岛“想做一个人”的愿望的有力的呼应。当然,韩东在这里所指认的人,与北岛所呼唤的人,已有很大不同。韩东的人是一个强烈的关注着自身感受和经验的普通人,一个其社会归属模糊不清而对自我有着极其强烈的意识的人,他甚至就是这种极端的自我意识本身。而在北岛那里,人只有在一种明确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确认他自身。与韩东所指认的人相反,这个人的社会归属十分清晰而自我意识却相当模糊和暧昧。显然,北岛并不关注人的具体的日常的生存状态,他更关心的是人的社会权利和一种被压抑的社会意识。为了与北岛的人相区别,韩东把他的那个人叫作平民,而平民在韩东那里的意思其实就是从其社会属性逃逸出来,回到自身的人。这样,在朦胧诗那里着力加以渲染的人的问题,在韩东这里转化成了自我的问题。而这可以视为这一代诗人一切艺术思考的起点。在第三代诗人那里,这个自我表现为夸张的大喊大叫,带着自我发现的歇斯底里的狂喜,也承受着疏离了社会意识的自我的无穷烦恼。在海子那里,他体现为与人类原始生命力的深刻关联。而对更多的诗人来说,他是“另一个我”、“另一种生活”。到了1990年代成熟的个人化的写作意识中,他变得安静、坦然,日益专注于自身的意识。而在更年轻的诗人那里,已没有人谈论自我或个人化,因为个人化已经是他们写作的前提。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日益自觉化的意识不断内化为写作意识的过程。
这个文学个人化的进程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这一代诗人的写作呈现出异采纷呈的面貌。然而,由于缺少严密的理论阐释,这一自发的文学进程也裹挟着一些负面的不良影响。对什么是文学的“个人化”存在着一些想当然的误解。譬如,把“个人化”等同于“个性化”,把“个人性”简化为自我暴露。当代诗坛的浮躁气氛,与这种误解存在密切的联系。当代诗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自我膜拜和暴力修辞的泛滥,对技艺和普遍性的轻视等等,也都根源于此。对上述问题,一些敏感的写作者早已有所觉察,并在他们的写作中有效地抵制了这些不良因素的侵蚀。而理论上的纠正方案,是由诗人兼批评家臧棣提供的。
在一次书面采访中回答有关诗歌中如何使用个人经验的问题时,臧棣提出了一个“人类独有的生命意识”的概念,并把它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联系起来。他阐述道:“……诗歌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类能力的体现,也就是说,诗歌的意义不取决于个人,甚至不取决于个人的才能……我现在意识到,诗歌所依赖的最本质的东西并不是个人经验;当然,也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集体经验,而是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生命意识,荣格曾称之为‘集体无意识’。”[2] 我认为,臧棣这里的阐述并不是对文学个人化进程的否定,而恰恰是对它的深化和生发,因为在文学的个人化要求中,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对人类普遍经验的诉求。而臧棣以其深刻的艺术洞察力,将这一诉求一语道破了。文学的“个人化”并非“个性化”。“个性化”更多地表现为风格、趣味、语调、形式等可以辨认的文本标记,而“个人化”却是文本生命力的最后依据。从概念上说,“个性”是与“共性”相对而言的,它总是以差异来显示其自身。而“个人化”的标记却不是差异,而是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个人化”的最终目的不是发现自我的个性,而是追寻到我们内部,发现另一个在我们身上深藏不露的内化的自我。这个内化的自我,正是臧棣所指认的“人类所独有的生命意识”,它是人类生命最深层的秘密。因此,“个人化”并不是对“个性”的盲目的崇奉,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个性的逃避。所谓“个人化”,就是不断地一层层揭去我们身上的社会身份、个性、意识的外衣,直到这个“集体无意识”——人类全体的生命奥秘,完全裸露、呈现出来。可以说,臧棣提出的这个“人类独有的生命意识”的概念为我们揭示了文学个人化进程最深层的目标,把诗人的触角引向了人类生命意识的内核,从而把体现于诗歌中的人的自觉推进到了一个更深入的层次。
对于从朦胧诗那里开始的文学自觉化运动的继承,表现得更为戏剧化。朦胧诗获得的崇高的文学史地位和其美学成就的不对称,给年轻一代诗人造成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暗示。为了尽快确立自身的文学史形象,也为了有效地获取世俗名声,一些诗人机巧地采取了反朦胧诗的写作策略。这是第三代诗人的一个基本的写作动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标举的一些口号,韩东的“口语化”、“诗到语言为止”,于坚的“反崇高”,非非的“反文化”都与这种策略有一种暧昧的联系。然而真正通过这种写作策略确立了自身的文学形象的只有少数诗人,最突出的是韩东和吕德安。而多数诗人由于文学态度的简陋和极端化,由于急切的文学野心裹挟的心理急躁,降低了文学敏感,窒息了自身美学空间的生长。而韩、吕二位的写作才能、平衡意识足以使他们避免那种口号式写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留下了最经得起检验和挑剔的诗歌文本。而韩东至今仍对年轻一代的诗歌取向发生着影响。
在文学的自觉化方面,真正继承和发展了朦胧诗传统的,是一批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处于边缘,专注于构建自我美学空间的诗人。这些诗人包括写作倾向颇不相同的张枣、陈东东、王寅、肖开愚、西川、海子、骆一禾、黑大春等等。这些诗人对自身与朦胧诗的差异有充分的意识,但他们不想通过颠覆来确立自身的文学史形象,而更希望通过自我的完成自然地凸现这种差异。因此,他们与朦胧诗的关系,不体现为正与反的、取彼而代之的关系,而是体现为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他们自觉地把朦胧诗的终点当成了他们探索的起点。骆一禾、海子在写作的激情方式上回应着第三代诗人的激进姿态,但他们的文化抱负和强烈的人文精神,又使他们避免堕入第三代诗人的文学虚无主义,在文本样态上显现出与第三代诗人极为不同的面貌。
这一文学的自觉化进程在1990年代由于另一些才华出众的诗人的加入而得到深化。他们至少该包括这样一些名字:臧棣、清平、麦芒、哑石、余怒、丁丽英、叶辉、森子、小海、朱文、鲁西西、周瓒、桑克……至此,文学的自觉成了这一代诗人广泛的共识,当代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稳定、持续、内敛、深入的新的阶段。
三
文学的自觉化在诗歌美学上体现为这一代诗人在诗歌方式、美学趣味、语言和文体意识诸方面的全面自觉。这种自觉,在第三代诗人那里因主体意识的过度膨胀而有所遮蔽,但为一些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边缘性诗人,如陈东东、张枣、肖开愚、王寅等所坚持(韩东、吕德安的写作也在这条线索之内)。1990年代以后,由于臧棣、黄灿然、清平、余怒、桑克、叶辉等诗人的加入,这条线变得更加清晰可辨,蔚为壮观。
1980年代的诗人们,主要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对诗歌仍表现出一种天真的态度。也许不能把这种态度简单地称作浪漫主义,因为在他们的态度中混入了较多的现代主义的因素以及基于实利的盘算,但他们的诗歌方式与浪漫主义确实有很多共通之处。譬如,对情感和个性的迷信,对新奇和怪诞的癖好,艺术上的过分,对形式的虚无主义态度等等。他们把诗歌当成一种纯自发的行为,相信激情的自我表现,把诗歌的美学品质寄托于诗人的个性。结果是,第三代诗歌运动期间产生的大量诗作并不具备浪漫主义诗歌固有的一些优点,而它的种种缺点却借运动的风潮得到了夸张的表现。第三代诗人中能够避免自发性诗歌在艺术上的娇弱症的,我以为只有韩东和吕德安。韩东虽然说过诗歌是望天收,但在他的诗歌意识中还有一些因素,平衡了这一态度的被动性。他甚至说,“这种平衡就是生命,就是一切”[3] (P286)。韩东也相信灵感,但他同样强调对灵感的理解和控制,是一个“懂得如何控制和运用灵感,懂得灵感特殊的敏感性和娇弱性的作家”[3] (P291-295)。而在大多数第三代诗人那里,灵感不过是迟钝和无能的饰词。韩东的主要愿望是想通过口语化把诗歌带入一种经验的直接性之中。在韩东那里,这种直接性是对朦胧诗的故作高深和虚张声势的流弊的一种矫正。但在“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主流中,这种直接性仅仅导致了一种美学上的虚无主义。很多诗人并不具备在诗歌中使用口语的能力,却把口语视为诗歌的护法神,在一个莫须有的神案前大叩其响头。结果是,他们的诗几乎全都成了韩东的不得体的盗版本,有论者戏称为“口水诗”,诚不为过。
1980年代主要的诗歌成就体现在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些边缘性人物,如陈东东、西川、肖开愚、张枣等诗人身上。是他们而不是那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继承并发展了开始于朦胧诗的文学的自觉化进程。在这些诗人身上,文体意识和语言意识的觉醒,扭转了第三代诗歌的自发性倾向,把写作变成一种自觉的、深思熟虑的行为。他们对诗歌的态度是实验主义的。他们拒绝为诗歌预设某种文学标准,而把文学的效果视为检验诗歌的最终标准。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必须在文学效果的范围内加以精密而审慎的考虑。他们把第三代诗人“怎么写都行”的文学幻觉,转变成了“应该怎么写”的问题意识,完成了这一代诗人的诗歌态度从天真到经验的转变。另外两位诗人,骆一禾、海子以一种激情写作的方式回应着第三代诗人天真的诗歌态度,但他们的文化抱负和人文气质使他们摆脱了“第三代”诗人的文学虚无主义。不过,对待诗歌的这种天真态度,也在他们的写作中打下了醒目的烙印,妨碍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海子很多时候是在乱写。他的长诗只有某些片断闪耀着天才的光芒,大多数诗节混乱不堪,对语言缺乏起码的控制。海子并不缺乏天分,但却明显缺少驯服甚至理解这天分的能力,结果反而被这天分所拖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死确实具有悲剧的性质。
1990年代以来,这种文学的自觉已成为大多数诗人的写作意识。它得益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落潮,水落而石出,一些在第三代诗歌运动期间处于边缘的诗人,在1990年代逐渐成为引导诗歌进程的中坚人物,而壮大于一批才华出众的新诗人的加入。这些诗人在19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高潮期已进入扎实的具有个人意味的写作,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至1990年代才逐渐为诗坛注目。其中,臧棣的贡献尤为突出。臧棣在1984年就写出了定下其个人基调的名篇《房屋与梅树》,而那时海子刚刚写出他的《亚洲铜》,西川则要到一年以后才写出《起风》和《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事实上,臧棣的身影在1990年代覆盖了一大批诗人的写作。臧棣是属于那种源头性的诗人,他的写作注定将哺育众多的诗人。
第三代诗人自发性的诗歌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美学意识的贫乏。与其说他们的美学趣味是恶劣的,毋宁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确定的美学趣味。这里显示出例外的,还是韩东和吕德安。韩东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领袖,但他的美学趣味又使他独立于潮流之外,成为他所发起的这一运动的异己分子。韩东以一种挑剔的眼光对进入诗歌的经验进行严格的挑拣。他还有一种唯美的倾向。他相信艺术,对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非艺术色彩有足够的警惕。他在1980年代末就说过“第三代诗歌中真正有意义的诗人正是那些对‘第三代诗歌’这一概念进行背叛的人”[3] (P128)。不同于第三代诗人心态上普遍的自我膨胀和自发性的写作态度,韩东认为“诗是诗人们放弃自我的结果”,为了保证诗歌的质地,诗人需要进行“去粗取精,提炼、舍弃”的艰苦、耐心的工作[3] (P168-169)。他的文本浓缩、精确、细腻,外表单纯然而却是高度提纯的。吕德安的分寸感和语词意识,造就了当代诗歌中最安静、透彻、自足的文本,他和他使用的词语保持了一种最切身的关系。
另一些诗人的美学趣味带有更多的个人标记。西川1980年代的美学趣味带有古典主义倾向,充满自制而不乏感性的魅力;陈东东则是超现实主义和东方趣味的混合,早期的诗犹如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杜牧;肖开愚则是一个驳杂的现代感性的容器,各种不同的美学倾向在这一容器中进行着热烈的反应,显示了奇特的活力和融合力;海子和骆一禾既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也不乏敏锐的现代感性。
在美学趣味上,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批诗人显示了一种更加自觉的文学意识。他们大多受过象征主义美学的洗礼,天性中有一点唯美倾向,同时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有广泛的接触,心仪现代感性,对智性和感性的融合怀有浓厚的实验兴趣。他们追求文本的完整,讲究语言的质地,深爱节制的美德,反对感伤和滥情,把感情视为诗歌处理的素材,而不是诗歌的发动机。一种特殊的个人语调成为他们风格的一个显著标记。而过去中国诗人的声音模式往往是借用的。格律体诗人借用格律模式,自由体诗人也不得不借用他人的模式,如郭沫若对惠特曼的借用,贺敬之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借用。这种情况直到这一代诗人手上才得到彻底改观。他们的自信和个人价值观,使他们敢于在诗歌中采用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语调发言,并使它成为其诗歌美学品质的最突出的特征。这种个人化的语调也带来文体上的一系列变化。这一时期最普遍的诗体还是自由诗。但是,自由诗的自由其实是外行的一个误解,在内行人看来,自由诗是最不自由的,它的每一个词语都是按照文学效果的要求,综合考虑形声义各方面的因素严格拣选的结果。在自由诗中,经验与每一首诗的特殊形式之间必须完全和谐一致。正因为它在形式上是“自由”的,所以它的任何败笔都是不可原谅的。无韵体诗的普遍采用是这一时期的另一显著特征。这也是诗歌声音模式个人化的一个结果。这种形式对个人语调的形成干扰最少,同时又拦蓄了自由的过分泛滥。它体现了这一时期节制和准确的美学要求。
这种个人化语调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诗歌风格上的“轻化”。虽然,韩东已经指出“诗歌在本质上就是轻的”[3] (P288),但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它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学品质。相反,那时的诗人们普遍染上了对“重”、对“大”、对洪亮的声音的狂热症。由此也可见出,韩东与他所影响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之间的隔膜。“轻”成为一种共同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批诗人的身上,如臧棣、黄灿然、朱朱、清平、杨键、叶辉等。对臧棣诗歌风格上的轻,王敖、胡续冬等批评者已作了很好的论述。由此带来的一个次要的后果便是所谓对大词的警惕。由此可见,这一代诗人不再自缚于某种主义的律条,而显示了一种把各种主义融进自身特殊的个性的能力。如果按照瓦雷里的定义,古典主义的特征就是心头带着一位批评家,那么这一代诗人的美学趣味中还有浓厚的古典主义成分,因为这些诗人写作中显现出来的批评意识可谓昭然若揭。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把他们的美学趣味称为象征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加个人趣味的四位一体的融合,显示了一种穿透文学史的意识和综合的倾向。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体现了上述美学特征的诗人名单至少应该包括像臧棣、戈麦、黄灿然、清平、麦芒、桑克、余怒、叶辉、哑石、朱朱等一批诗人。
四
这一代诗人对文学的自觉化的追求,还表现为语言意识的觉醒。这个过程开始于韩东的口号:“诗到语言为止”。这个说法后来经常受到质疑,不少论者指责它把文学的效果仅限于文本的表面意味。但是韩东这一主张是针对朦胧诗过于注重诗的主题深度而无视文本的表观效果而言的,它至少有助于将文本的表观效果置于诗人的视野之内。第三代诗歌运动对活力的信仰,带来了语言的开放性,打破了诗歌语言和非诗歌语言的界限,口语、俗语、方言土语一股脑儿涌进了诗歌的疆域。诗人们放肆地废弃了语法,诗行中随处可见任意割裂的句子、随意并置的意象和词语的非法婚姻。这一时期的诗歌语言就像一个还处于草创期的强大帝国,四方的部落纷纷前来投奔,每天膨胀的版图把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土地还没有丈量,边界还有待勘察,法律还没有公布。这种情况到了1990年代有了重大的改变。
活力的重要性仍是共识,语言的开放性也得到了坚持,但是帝国的法律颁布了,各省的边界确立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得到了清楚的阐释。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诗歌的特殊句法向散文的正常句法的回归。特殊的诗歌句法仍在被使用,但它必须经受文学效果的严格的检验,否则,诗人将首选正常的散文句法。在此,诗人们再次申明了自己的自由:诗歌并非只能采用几种特殊的诗歌句法,而有权调用包括散文在内的全部句法。其次,它体现为对语言的精确性的追求。我认为这是这一代诗人语言意识中最具普遍性的东西。当然,这里仍然不得不排除某些第三代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语言的精确性的追求已成为这一代诗人最基本的语言伦理或文学道德,并用它了结了上几代诗人普遍的道德强迫症。语言的精确性包含了几方面的综合要求:表达的简洁,语言的质地、敏感性、力度感的平衡,音节、语调的和谐,结构(句法和体式)的完整。这种对精确性的追求,要求诗人从效果出发,综合地考虑词语的形、声、义在诗歌表达中的特殊功能,不顾此而失彼。第三是肖开愚所说的语言的民主意识,它表现为一种把词汇当作材料使用的倾向。这一代诗人在拆除了诗歌语言和非诗歌语言的界碑的同时,开始学会平等地对待他们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他们懂得美和诗意只存在于词语之间的关系中,而不在词语本身。他们学会了朴素的表达,摒弃了华丽的词藻和那种言不及义的表达方法,使每一个词语的出现最大程度地服务于文学的效果。有趣的是,这种对待词语的民主态度,反而帮助他们驯服了语言这匹野马,使它在他们手下变得安静、耐心。这种意识也使得诗人和语言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关系脱颖而出。
我认为这是这一代诗人的语言意识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把语言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事物的意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臧棣的蝴蝶论表达得极为精彩。我们不妨引用一下:“语言和蝴蝶,有许多相似之处。至少把语言比作蝴蝶,会让我时常警醒语言是有自主生命的。蝴蝶在我眼里非常具有灵性。在野外捕捉蝴蝶,你就会发现蝴蝶具有一种幽灵般的能力,它能在你伸手触及它的刹那间,腾空翩翩飞起……”这种语言意识的一个结果便是这一代诗人开始学会尊重语言。对他们而言,语言的问题主要的不是一个如何驾驭它的问题,而是如何倾听和顺从的问题。这一代诗人由此建立了一种语言的发现观,即通过对语言的倾听、观察和揣摩,去发现事物之间被日常的经验和逻辑所遮蔽的关系,揭示事物潜藏的诗意。清平将之总结为语言与诗人互相发现、互相教育的关系。而在余怒那里,它表现为“不言说”“让语言自语”的戒条。哑石则把诗歌视为“语言、灵魂同一的呼吸中具有自主性的生长之物”。吕德安认为在与语言的关系中,诗人既是主宰也是奴隶,“像春天的屋顶,承受着雪,同时也感到自己的消融”。我认为这种语言观在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后果,使得最近20年成为新诗史上最为活跃的诗歌发现的时代。诗歌的题材、主题丰富了,诗意的范围大大开阔了,形式更加花样百出了,技艺愈加精密了,诗人的意识日趋活跃……
先锋或先锋性,是贯串并深刻影响了当代诗歌进程的一个重要诗学概念。对这个概念的不同阐述,是当代诗歌中种种冲突、对立和融合的根源。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它是一张人人想据为己有、可以立决胜负的王牌。1980年代诗歌的先锋性主要体现为一种盲目的、破坏性的力量,它的目标主要是涤荡以往的诗歌史加诸诗歌和诗人意识的种种限制,把一种原生性的生命力交还给诗歌。1990年代以后,诗人们的先锋意识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把诗歌的先锋性寄托于颠覆性、破坏性的革命原则上,而把它与一种理性的深谋远虑联系起来。它继承了1980年代诗歌所拓展的疆土,同时着手在这疆土上进行恢复和建设的工作。这个被继承下来的疆土主要是经验的开放性和实验倾向,同时利用秩序的力量驯服它们的破坏性。
在这一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直觉、感觉、想象、意识、日常经验以至历史事件,统统成为诗歌经验的来源,并在处理和转化上述材料的过程中显示出惊人的诗歌能力。一言以蔽之,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是基于经验的可能性,而不是经验的现实性。对诗歌经验的这种开放性态度,将当代诗歌引进了一个综合性和个人性的新境界。实验倾向曾经被概括为这一代诗人写作的一个本质性特征。这一代诗人以一种对待诗歌的实验主义态度取代了诗歌的本体论。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先验或预设的东西可以保证一首诗的成功。这种实验倾向把诗歌带入了灵魂的冒险行动中。对这一代诗人而言,实验不仅是激发诗歌活力的需要,而且也是不断丰富我们的诗歌的意识的需要。这代人确实是幸运的: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充分享受写作的快乐,把写作作为一个自在、自为的事情。这也是这一代诗人特别高产的原因之一。
但是,经验的开放性和实验倾向都是双刃剑,它们在拓展诗歌的疆域的同时,也在悄悄耗损诗歌的美学品质。到1980年代末期,大多数的诗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对秩序的恢复和建设给予了巨大的热情。强烈的实验倾向并没有在这一代诗人身上引发文学的虚无主义,而是赋予了他们一种建设者的自信。与臧棣的诗的定义应该从未来寻找这一观点相反,陈东东有一个关于诗歌的说法:“没有一个‘诗的理念’,没有所谓‘本质的诗’,诗又从何说起呢?……欠缺这样一个‘纯诗’的概念,无法写诗,也无从谈诗。”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从字面去理解臧棣和陈东东的说法,就不会得出他们的说法彼此矛盾的结论。事实上,两位诗人的说法是互为前提、互相补充的,它们相反而相成。照我理解,臧棣的定义是在强调诗歌对创新的要求,而陈东东则强调了这种创新与诗歌的理想秩序的关系。而臧棣也同样说过,诗歌的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不新”。结合我们这里所说的两个特点,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这一代诗人关于先锋的定义:从文学的历史所提供的关于诗歌和美的知识出发,通过灵魂的冒险,努力扩大我们关于诗歌和美的认识的边界。这个先锋性区别于第三代诗人的先锋性之处,在于它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
在新诗历史上,这一代诗人非常幸运地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位置上。从当代诗歌的进程来看,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萌芽于朦胧诗的人的自觉化和文学的自觉化的进程。放在整个新诗史上来考察,他们则是处在一个近百年新诗史的总结者的位置上。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日趋成熟、文学意识的丰富、历史对人的压抑机制的失效以及这一代人突出的诗歌才能,这一切都促使他们把新诗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与“继往”的特征相比,这一代诗人在“开来”方面的突出贡献更令人难忘。现代汉语诗歌的许多可能性是从这一代诗人开始的。他们开辟了新诗的诸多新领域。我相信他们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必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传统,对新诗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都使我对新诗的前途充满信心。我认为,随着20世纪的逝去,新诗的学徒期已正式宣告结束了,我们再用不着在西方现代诗歌的深厚传统面前妄自菲薄,因为我们自己正在参与一个伟大诗歌传统的建设。
注释:
③陈东东:《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陈东东访谈录》(未刊稿)。
标签:韩东论文; 臧棣论文; 朦胧诗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吕德安论文; 诗歌论文; 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