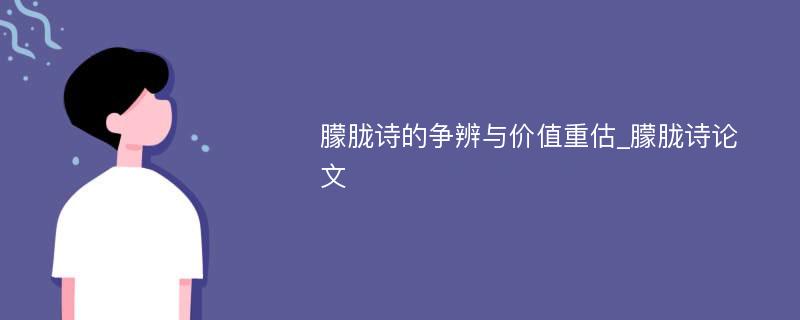
朦胧诗的争鸣与价值重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朦胧诗的出现引发过一场规模与影响空前的论争。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为代表的崛起派,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是标志着当代诗全面更新的起点,它使新诗艺术迈出了崛起的一步;丁力、程代熙、郑伯农等为代表的否定派,认为它是畸形的怪胎,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逆流,它将自生自灭。这场论争使朦胧诗概念以及一些模糊的理论命题日渐明确清晰,扩大了朦胧诗的知名度;但论战双方有时不够冷静。
朦胧诗不无曲高和寡倾向,但它冲击了传统审美习惯,结束了当代诗艺的停滞不前,并为当代诗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迪。它完成了时代内在历史的拼贴,在促进诗本质回归的同时,实现了对现代诗派、九叶诗派的超越;它重构了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美理想规范,形成了如烟似梦的朦胧风格;它以文学个人化的奇观,为当代诗坛输送了多种艺术模型。朦胧诗是新诗历史上一帧永远的风景。
朦胧诗这只“报春的乳燕”(李泽厚语)起飞维艰,命运多舛。它的簇新审美态势严重冲击了民族文化积淀的超稳定惰性,所以一经面世便被送了个不明不白不清不浑,内涵欠确且外延也模糊的戏称——“朦胧诗”,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大战;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论战产生的骚动与影响,远远超出了朦胧诗本身。时至今日,该是还朦胧诗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朦胧诗的价值应该得到高度确认。
一、诗外世界的对峙
朦胧诗论争的规模与影响都是空前的。几乎所有诗歌评论者不辨长幼男女都被卷入其中,不仅把诗坛一向清静的圣地搅动得沸沸扬扬,甚至也招引来整个文艺界乃至国外纷纷关注的目光。论争的阵容壁垒分明,一边是否定派,麾下立着丁力、程代熙、郑伯农、宋垒、臧克家、敏泽、周良沛等诸员大将;一边是崛起派,披挂上阵的有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徐敬亚、李黎、陈仲义、蒋夷牧等。两派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交战长达数年之久。
开始,双方只亮亮相,并未真正过招。谢冕这位功高盖世、历史不会忘记的朦胧诗理论领袖,凭着天生的热忱和睿敏捕捉到,在《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小草在歌唱》、《光的赞歌》等有巨大社会轰动效应的诗外,一种手法新颖的“古怪”探索诗正在不自觉地疯长,于是在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推出《在崛起的声浪面前》,欣喜宣告“一批新诗人正在崛起”,预示了其气势、力量与无法估量的前途,表现出一位诗评家的开放胸襟与智慧风采;然而摇旗呐喊的反映却是寂寞。稍后,章明先生在《诗刊》1980年第8期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拿九叶诗人杜运燮的《秋》和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开刀,批评这两首稍加体会便可入其堂奥的诗,代表了一种“晦涩怪僻”倾向,让人读了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气闷不过,便随手送给“永远无法以索解的‘谜’诗”一个雅号——“朦胧诗”(朦胧诗一词从此后约定俗成)。至此表面并未直接交手的平和宁静中,论战序幕实际已渐渐拉开,所以当谢冕的同窗孙绍振将其纲领性论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从1981年3月《诗刊》抛向社会时,就不啻于一颗定时炸弹,引爆了白热化的深入论争。这篇文章呼应了谢冕的观念,并使之深化了一步,认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以雄辩家的思维,论证新诗正在经历由非我的社会之我向自我的自觉之我回归,这种人的价值标准确立,是美学原则中心;同时还具体论证了新潮诗人的感知世界方式、理性思考光辉和艺术上的创新。坦率地讲,这篇文章多得哲学思考之妙,而对艺术本身涉猎不多;但它不驯服的姿态,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发表后仅《诗刊》一家就接连刊发程代熙、敏泽等人的五六篇文章,与之商榷,进入了两派之间真刀真枪的正规战,顷刻间朦胧诗成了文艺界的热门话题。而到1983年1月公木的高足徐敬亚,将在吉大读书时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论争走向了高潮。这篇三万余字洋洋洒洒才情横溢的论文,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朦胧诗的起因、艺术特征、美学价值及历史地位,因作者自身就是朦胧诗弄潮者,所以能深悟出艺术本体之妙,论证起来精粹新鲜,头头是道;虽过于投入,过于重视文采造成了某些偏颇失当,但仍不失整体合理性,从而与谢冕、孙绍振完成了三次崛起论全过程。可惜它有些生不逢辰,当时诗坛空气已远非两年前那般宽松自由;所以刚一露面,便招致数百篇商榷文章出笼。《诗刊》、《星星》、《文汇报》、《辽宁师大学报》都成为主要阵地,说是商榷,实为批判。在种种否定的声浪面前,徐敬亚不得不进行痛苦反思,于1984年3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对《崛起的诗群》错误倾向做了心悦诚服的检讨,标志着论争基本告一段落。当时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某种程度上已超出单纯学术艺术争鸣范畴,留下不少以政治批判代替艺术批评的教训;对一篇出自初出茅庐青年之手,总体倾向基本正确的文章,竟如此大动干戈,这是很不正常的。
否定论者与崛起论者对朦胧诗的评价更是针锋相对,大相径庭。否定论者认为它是畸形的怪胎,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是“沉渣的泛起”,是西方现代派与中国20—30年代现代派的翻版,它的命运也会与之一样沉落下去,自生自灭;是数典忘祖,是用“不健康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在非议社会主义政治,灰色孤寂,孤芳自赏和玩世不恭”[②],“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脱离了时代的精神”[③]。崛起论者则认为它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崛起,是标志着当代诗歌全面更新的起点,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开始,必将汹涌成一股澎湃的主潮;高度赞扬其是“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歌唱”,其“激流的主潮是希望与进取”,它的出现“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它是中国的,是现代的,更是新的,它不仅填平了抒人民之情与自我表现之间的鸿沟,而且体现了变革的先声[④]。观点的对立势若南北两极。对于这样针锋相对的论点,我们无意做走折衷道路的和稀泥者,只想说它们两派都不够冷静,时间审视距离的缺乏与诗歌论争以外一些因素的渗入,使它们二者在做出理论贡献同时,都下了不少不太客观公正的结论;但我们不必苛求与挑剔他们,而应该理解并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的一切都出自于对时代与艺术的真诚,因为他们都不是简单的捧杀与棒杀。事实上时间已经证明,朦胧诗的表现策略并无大差错,近乎爆破的情绪使他们不像台湾现代派诗人乃至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那样,把满腔的焦虑犹疑隐藏在复杂的比喻与结构里,而以急迫性的倾出方式较直接地喊出自己的心声,根本不存在完全读不懂的障碍;思想上虽致力于内心世界发掘,也不乏一定的忧郁与感伤,但它并没有彻底走向自我唯一存在的坟墓,而是常通过情感揭示表现对时代的关注,其基本主题是传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阵痛,既有对民族命运的反思,又有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更有对未来执著的瞩望,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大雁塔》、《纪念碑》、《太阳和他的反光》以及顾城的歌乐山组诗,都灌注着时代精神的动人音响。所以否定论者简单地视之为异端的古怪诗与沉渣泛起,恐怕批判得过重了,那是一种心灵的隔膜,更是艺术的隔膜,是阅读与诠释方法上的习惯厚茧使他们的判断出了毛病。那么崛起论者的问题出在哪呢?谢冕有时过于诗意化的表述使思想略显模糊,但基本精神仍把握了分寸,其它崛起派论者则常偏执得近乎极端。把自我引入诗内本无异议,但说“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表现世界,是为了表现自己”,“诗应该写潜意识的冲动”,则无疑混淆了自我与时代、人民的关系,易使人走进纯粹个人主义的蜗居;把我国渊远流长的古典诗歌统统视为“诘屈聱牙的古调子”,把建国后三十年的现实主义诗歌统统视为一直“沉溺在‘古典+民歌’的小生产歌咏者的汪洋大海之中”,显然也是虚无主义的片面性暴露,是缺少历史常识的表现;另外一味贬低现实主义,预测现代主义才是中国诗歌金光大道也没有足够的理论根据。尤为突出的是,他们那种背离传统中和之道的激进强劲态度也让人很不舒服,据说一些反对论者不反对朦胧诗而反对偏激的崛起派,这很能说明问题。
无论怎么说,朦胧诗论争的意义不可估量,它不像人们说的是没意思的混战。虽然论争双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最终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收场,虽然论争也留下了以政治裁判取代学术争鸣的沉痛教训;但它从朦胧诗现象到整个诗歌理论再到新诗发展方向的逐渐深化,使朦胧诗这原本十分含糊的概念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以往很少触及或模糊不清的理论课题,如传统与现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朦胧与晦涩、自我表现与抒人民之情的关系等问题逐渐清晰,诗歌观念也得到了积极反思与发展。尤其是这次艺术上的大面积平等对话,激活了诗坛的热烈民主气氛,扩大了朦胧诗的知名度,为新时期诗歌沿着健康正确的路线继续高远腾翔,准备了坚实有力的理论后盾。基于此,我们认为杨炼的一句话用在这恰到好处,“一切,不仅仅是启示”。
二、“历史将证明价值”
朦胧诗人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匆匆忙忙地被推上诗歌前沿的。缺乏自觉的自发性创作发生机制,使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地进了非伪诗的大门,将诗的辉煌旗帜高高升起;同时也决定了诗人与诗的不成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对于众说纷纭的朦胧诗,人们尽可以挑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都无法不承认,它以对日趋板结的审美习惯的猛烈冲击,结束了中国当代诗歌艺术的停滞不前,促成了荒芜诗歌园地尽早返青,它在诗坛引起的骚动与影响都是空前的。首先它以心灵日记方式(北岛多为沉思日记,舒婷多为情感日记,顾城多为感觉日记),完成了时代内在历史拼贴,不仅促成了诗歌情感哲学生命本质回归,而且实现了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超越后的螺旋式上升。他们用非现实主义手法传达现实性内涵,虽与象征、现代诗派构成了接力似的连续系列,但却非后者的沉渣泛起。同样从个体出发,后者回归内心是为逃避现实,否定现实与自身,其间浸染着飘逸自得风度,超脱而消极;朦胧诗则为更深刻积极地表现人与现实,脚踏实地探索真理,充满着向上明亮的热情与民族自强精神,如果说后者是飘浮在阴冷惨淡的愁云上,它则是坚实大地上负重身影的闪现。从怀疑感伤到沉思追求,朦胧诗彻底冲决了左倾思想栅栏,契合了时代心灵的发展进程,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一系列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反抗英雄、普渡众生的救世主似的形象塑造自不待言,即便是低音区的情思吟唱,充斥的也是理想的痛苦与英雄的孤独,仍在悲怆中凸现着向上的力度。它那种在唯我与无我间恰切抒情位置的寻找,恐怕是在读者中引起共振的心理基础。其次,朦胧诗以对传统艺术惰性的挑战,重构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美理想规范,形成了独特的朦胧风格,如轻纱遮水,似淡雾罩山。当新诗中断主体意识与艺术美感时节,朦胧诗置身在空白地带,带着积极创造精神,通过个人心理与直觉的再造,通过智慧空间对单向描摹抒情方式的取代,通过意象思辨性与语言创造性的强调,修复了断裂的朦胧美传统,放射着崭新美学气息,对于它的流行色——朦胧美,不少理论工作者与老诗人气愤不已大加鞑伐,这是不应该的,它的朦胧美不是对读者的戏弄,而体现着对人生意义与生活现实丰富意义的执著探索与尊重,何况未解冻时代选择它也是一种智慧。如《一代人》、《致橡树》、《双桅船》简直就是美的典范,它产生在文革文学中无法想象。再次,以文学个人化奇观铸造,为当代诗歌输送了多种艺术模型。朦胧诗人同样流淌在流派的河床里,但每朵浪花都有自己的绰约风姿。浸满自传性色彩的舒婷,骨子里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对理想的追求对追求中的心理矛盾,经她细腻灵性的梳理便转化成美丽的忧伤,深情优雅,清幽柔婉。顾城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构筑超现实的童话世界,他那敏锐的直觉力,能迅速达成明丽纯净物象与幻想心灵同构,玲珑剔透中闪烁着机智精巧;但在现实面前时时有虚幻脆弱之嫌。与深情的舒婷、机智的顾城相比,北岛更像冷峻的兄长,他缺少婉约与缠绵,善做冷静诡奇的哲学思辨与象征思维,沉雄傲岸,但也阴暗冷漠。江河与杨炼多得惠特曼、聂鲁达风韵,视境宏阔,在民族文化历史反思与掘进中,给人以豪健壮美之感;前者多以原型与个体同构,后者则致力于文化学者型智力空间的建构。芒克锐利,梁小赋精巧,李钢神奇诡秘,刚柔相济。每朵花都据有开放的权利。最后,朦胧诗昭示了自身蓬勃光大的可能性,不仅启发影响了第三代,而且也影响了同时代乃至上一个时代诗人的艺术操作。由于朦胧诗艺术上精湛的表演博得了众多喝彩之声,合理吸收它的内核就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追求;第三代后来的反叛丝毫改变不了如下事实,第三代尤其是其中的学院诗人,都是朦胧诗的后代,都是吮吸着朦胧诗的乳汁强壮起来的;并且它在雷抒雁、邵燕祥、刘祖慈、孙静轩、刘湛秋等中老诗人的创作中,也有广泛回应。
勿庸讳言,某些朦胧诗确有曲高和寡倾向。自发性使他们的创作常有种日记式的信手拈来之嫌,零乱而内倾,有时将自我凌驾于一切之上,狭窄世界的隔世感使它丧失了与群体沟通的可能;过度依仗于象征、暗示等间接性艺术手段,使主体意识渐渐为静止堆积罗列的意象群阉割,诗成了多义性乃至猜谜式的技巧实验,尤其是这种宜于表现心灵的艺术,一旦转向政治性内容时便显出捉襟见肘的迷蒙与无力;随着社会心理的日趋明朗,仍一味咀嚼自我伤痕,难免也会落伍于时代。种种消极因素既限制了朦胧诗的影响力,又羁伴着朦胧诗突破自我的驱动力,如此看来一些人对之嗤之以鼻也就并非毫无缘由了。不错,诗乃尖端的贵族文化艺术,有一定先锋性,但也必须把握住必要限度,因为诗歌选择读者,读者更在选择诗歌,一味求隐,令人望而生畏,艺术价值的实现无从谈起。像《三元色》一类的诗尽卖关子,搞愚弄人的恶作剧,连大诗人公刘也接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诗之悲哀。可喜的是从1984年开始,江河、杨炼的史诗构筑、梁小斌等人的断然反叛,都发出了朦胧诗突破的讯息。
一切先行者往往注定是落寞寡合的孤独者,朦胧诗从生长到成熟乃至分裂,始终有股浓厚的悲剧意味。当年“子孙会读懂”的凄清,刚刚转换为获得合法地位的欣慰,第三代挑战的声浪就无情地漫到了他们足下。但我仍然要说,朦胧诗永远不会成为隔日黄花,它已在现代诗史上留下辉煌的定格,并且完成了特殊的使命: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注释:
①臧克家:《关于“朦胧诗”》,见《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②程代熙:《评现代美学原则在崛起》,见《诗刊》1981年第4期。
③丁力:《古怪诗歌质疑》,见《诗刊》1981年第12期。
④参见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