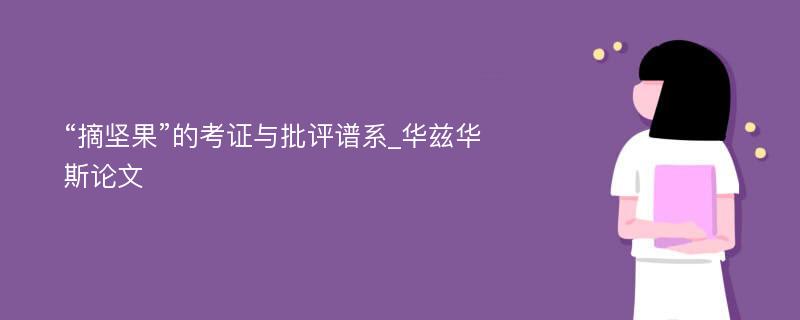
《采坚果》的版本考辨与批评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坚果论文,批评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中收录了华兹华斯一首奇怪的诗:《采坚果》。① 诗歌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描述了诗人童年时一次采坚果的经历。某个“美好的”一天,“我”艰难地穿过原本无路的层层“岩壁”、丛丛“草甸”以及枝蔓“缠绕的灌木”,来到一片人迹未至的幽雅的榛子林。一开始,“我”沉溺于这片美丽的“处女地”(A virgin scene!)所提供的“盛宴”——那浓密的“树荫”(bower)、淙淙的溪水、空谷的“幽兰”以及绿苔茸茸的“青石”——这一切都让“我”的心留恋沉醉,甚至与“飘渺的虚空”一起飘散。读到这里,传统的华兹华斯研究者可能会非常兴奋,因为这为“华兹华斯是自然派的诗人”的立论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例证。然而行文至此,华兹华斯笔锋突然一转,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事件:
……然后我站起身来,
把枝条拽向地面,裂帛声声,
糟蹋无情:那幽僻的榛荫(nook)
和绿苔茸茸的闺阁(bower),
都被蹂躏(deformed)和玷污了(sullied),从而顺从地
献出了它们的文静之身(quiet being)。
当践踏了这片树林之后,“我”一方面为自己“富赛国王”而兴奋,而另一方面,目睹那片“寂静的树林”和“闯入的天空”(intruding sky),“我”又“感到一阵痛楚”。然后,“我”突然向某个不知名的姑娘发出忠告:
所以,最亲爱的姑娘,请怀着温柔的心
穿行在这树荫中;请用温柔的手
轻抚——因为在这树林中有个精灵(a spirit)。
这之所以是一首奇怪的诗,不仅因为它是华兹华斯一生当中所写过的唯一一首具有明显性暗示的作品,更主要的是这首诗存在着太多欲言又止的含混——尤其是最后三行劝戒之言更是疑点重重:且不问那位被劝戒的“最亲爱的姑娘”到底是谁(是《露茜组诗》中的那个“孤星”或“幽兰”般神秘的露茜,还是作者的妹妹多罗茜?② 更为关键的是,作为全诗的收煞部分(coda),这三句在结构和语气方面出现得似乎太过突兀,以至于它们没有能够将全诗组织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
事实上,在该诗早期的研究中,后一个问题正像诗中那个神秘的“精灵”一样,使得大批颇有名气的华兹华斯专家显得笨拙而尴尬。如费里就认为这三句于全诗的结构完全是“多余的”(Superfluous)。他说:“这几句似乎偏离了(全诗的)主旨,或者仅仅是部分地与之相关,因而也就将其余部分过分简化了。”③ 帕金斯则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三行完全是“败笔”(a mistake)。④ 而当著名学者哈特曼在其同样著名的《1787-1814年间华兹华斯的诗歌》一书中论述到该诗时,对于这个问题则完全置之不理。⑤
那么,这首诗到底是作者自己精心创作的成功之作还是一时兴起的随感?如果是后者,他又为什么坚持把该诗收录进其成名之作的第二版《抒情歌谣集》之中?再进一步的问题是:在该诗中华兹华斯是否采用了某种春秋笔法?如果是,那些曲笔又隐含了哪些个人或历史的隐秘?总之,华兹华斯通过这首诗究竟想要表达怎样的思想呢?近年来,随着英美批评界对华兹华斯研究的日渐推进,上述问题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富有成效的深刻揭示。这些成果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华兹华斯的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本文从版本和批评两方面入手,梳理国外学界对该诗的研究,希望对国内华兹华斯的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版本考辨
列文森在《浪漫主义的碎片诗》中说,《抒情歌谣集》中所收录的《采坚果》以一个“半行句”(a hemistich)开头,这明显是一个删节标志(the mark of a truncation),它“暗示着某个先行存在的语境”,也即“某个业已遗失的完整版本”。⑥
列文森的判断是正确的,但那个“完整的版本”并未“遗失”,而且,还存在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因而使得《采坚果》这首诗牵涉到一段复杂的版本公案。这个问题其实在德·塞林科特(E.de Selincourt)1944年编辑《华兹华斯诗歌全集》时就注意到了。德·塞林科特不仅引用了《芬威克笔记》(“Fenwick Note”)中华兹华斯的原话——“这首诗原写于德国。本来是计划作为有关我自己生平的作品的一部分,但后来还是从中拿掉,因为觉得将它放在那里不合适”,而且他还提到多罗茜给科尔律治的一封信的手稿中也发现了《采坚果》的一种手稿本;此外,德·塞林科特还指出,两卷本的《序曲》中有些段落也明显来自《采坚果》;最后,更重要的是,德·塞林科特还附上了一个完整的全本(附录是后来编号为“鸽庐手稿16号”的那个本子)。⑦
继德·塞林科特之后,里德对《采坚果》的版本作了更为细致的考证。根据里德的考证,《采坚果》的不同版本分别出现于下列手稿中。它们是:Prel MS JJ,也即“鸽庐手稿19号”(“DC MS.19”);the Christabel Nb,也即“鸽庐手稿15号”(“DC MS.15”);Nb 18 A,也就是“鸽庐手稿16号”(“DC MS16”);DCP中一篇22.2×13.8cm零散页上面的一个片段,也即“鸽庐手稿24号”(“DC MS 24”)以及多罗茜写给柯尔律治的一封信(该信可能写于1798年12月14日,或21日或28日)中所附的那个短本(以下简称“多罗茜短本”)。⑧
这样,按照里德的观点,《采坚果》就至少有5种不同的版本,他们分别是:“鸽庐手稿19号”(以下简称“19号”)、“鸽庐手稿15号”(以下简称“15号”)、“鸽庐手稿16号”(以下简称“16号”)、“鸽庐手稿24号”(以下简称“24号”)以及“多罗茜短本”。(1800版《抒情歌谣集》采用的是“15号”的删节本;而德·塞林科特收录进《华兹华斯诗歌全集》中所采用的则是“16号”的后半部分;国内唯一的译本,即黄杲炘所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采用的也是“16号”本。)
近年来,有人又提出了与里德不同的观点。琼斯(Gregory Jones)认为,《采坚果》应该有六种版本,其中三种长本,三种短本。三个长本分别是“15号”、“16号”和“24号”。而三个短本中最早的一个出现在多罗茜1798年12月在德国时写给柯尔律治的那封信中(即“多罗茜短本”);另外两个就是“15号”和“16号”中的后半部分,分别见于1800年版的《抒情歌谣集》(“手稿15号”)和德·塞林科特的《华兹华斯诗歌全集》中(“手稿16号”)。批评家们常用的是德·塞林科特在《华兹华斯诗歌全集》中所采纳的版本,即从“手稿16号”中截出来的那个本子。⑨ 显然,与里德相比,琼斯只是将各种版本分为长本和短本两种,在版本考证问题上不仅没有提供新的材料,而且不知为什么居然忽略了“鸽庐手稿19号”那个本子——尽管琼斯这篇文章写于1996年,比里德的研究要晚将近30年!从琼斯引证里德的情况来看,他不应该不知道里德的考证。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琼斯并没有把“19号”当做《采坚果》的一个成型的本子,因为虽然“15号”中的第27-43行(" I would not strike a flower….A silent station in this beauteous world" )、44-46行(" And dearest maiden,thou upon whose lap/I rest my head,Oh! Do not deem that these/Are idle sympathies." )以及“16号”中的39-43行(" For,seeing little worthy or sublime….A silent station in this beauteous world." )都分别出现在“19号”中,但是,仔细读起来,这些内容仅仅是华兹华斯对其童年时代所作所为的感慨,不能构成《采坚果》的基本文本轮廓;而且,“19号”内容极其庞杂,那些诗行仅占全部内容中极少一部分,所以琼斯才没有考虑把“19号”中那些诗行看成《采坚果》的成型版本。
关于这几个版本的成稿时间顺序也有不同的观点。
德·塞林科特根据“16号”版本认定,《采坚果》最早的本子写成于1798年夏天——也即华兹华斯离开英国赴德国之前。⑩ 而里德却认为,在时间顺序上,最早被写成的应该是“19号”本,“15号”次之,“16号”再次之,“24号”(被掌握在华兹华斯的小姨子Sara Hutchinson手中)最晚成稿。但里德难以确定“多罗茜本”与其他手稿本之间的时间顺序。他只能够肯定“24号”是所有本子中最晚出现的(即晚于1798年冬天华兹华斯兄妹蛰居德国的时候)。里德还认为,“19号”本是所有版本的萌芽。而“19号”又是《序曲》的手稿本之一,看来《采坚果》这首诗应该是从《序曲》创作中衍生出来的。但不管怎样,里德认为,《采坚果》最早的成型本子应该是成于1798年秋天或初冬。(11) 里德推断,华兹华斯可能很早就在考虑把《采坚果》作为一首独立的诗从《序曲》中分离出来,因为华兹华斯自己曾经亲口说过,将该诗“放在那里不合适。”(12)
巴特勒(James Butler)和格林(Karen Green)两人的观点与里德基本一致,但他们更肯定地认为,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中的短本(即“手稿15号”的后半部分)是最早的本子,这个本子“应该创作于戈斯拉尔,时间在1798年10月6日至12月28之间;而其增加了前半部分的长本(即“15号”全本)则应该是成于1798年12月21日至1799年4月底华兹华斯离开德国前夕。”(13) 他们虽然也不敢完全肯定“15号”本与“多罗茜本”哪一个本子更早,但根据那封信日期落款来看,它应该是写于1798年12月21日至28日之间,这就是说,“‘鸽庐手稿15号’可能要更早一些”。(14)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和格林两人的考证比较明确地肯定了“手稿15号”中的前后两部分的成稿顺序,即,华兹华斯先写下了少年的故事(创作于戈斯拉尔,时间在1798年10月6日至12月28之间),而该故事的结尾三句完全是作者自己的信手写意;华兹华斯原本并没有考虑到要把这三句与全诗的结构有机地融为一体,甚至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要通过这三行来隐含某种深层的寓意;只是到了后来作者才补写了前半部分关于露茜的故事(大概成于1798年12月21日至1799年4月底华兹华斯离开德国前夕),以便给少年的故事加上一个诱因并使其结尾显得合乎情理。这也是为评论界所广泛接受的解释。评论界推测,出于某种原因,华兹华斯再后来又删除了前半部分(露茜的故事),只保留下来后半部分(少年的故事)出版,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出版于1800年的《抒情歌谣集》中的版本仍然存在那个扑朔迷离、没头没脑的结尾。(1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它所涉及到的不仅是版本问题,更主要的是牵涉到华兹华斯创作该诗的基本动机。在这个问题上,琼斯的考证有更新的发现。
琼斯一方面继承了里德以及巴特勒和格林的某些观点,另一方面则推进或修正了他们的某些看法。他也认为,“15号”、“16号”、“24号”以及“多罗茜本”四个本子都创作于1798-1799年冬华兹华斯兄妹蛰居德国戈斯拉尔的时候;而且认为“15号”是最早出现的长本或全本。对此,他提出了比前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认为,在“16号”和“24号”中,该诗的前后两部分(即少年的故事与露茜的故事)之间没有出现空白;而在“15号”中,前后两部分之间有相当大的空白空间,这显示这两部分不是从头至尾一气呵成的,而是分别写成于不同的时间。而且,“16号”和“24号”都是有标题的(“Nutting”),而“15号”和“多罗茜本”却没有标题,这显示出“16号”与“24号”都是后来修订的结果,而“15号”与“多罗茜本”则是作为即兴之作的原始文本。
更为关键的是,在“手稿15号”前后两部分的时间顺序上,琼斯力排众议,认为“15号”前半部分是先于后半部分成型的(虽然不一定行诸于文字)。他的证据来自于“15号”本的布局。尽管在手稿中两部分的顺序还是前后分明的,但前半部分结束于手稿64页左面,结尾句只占半行(" …Are idle sympathies" );后半部分(即后来出版于1800年《抒情歌谣集》中的本子)则开始于手稿65页的右面下方大概2/3的地方(也就是说65页右面上方整整2/3的页面空间是空白的),而且其开头句" It seems a day…" 也缩进了半行才开始(即列文森所说的" hemistich" ——“半行句”)。
这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虽然后半部分成稿(即行诸文字)可能要早于前半部分,但与此同时他又预留了足够多的空白页来补写前半部分。由于预留空白太多,结果等到将该诗前半部分补写完之后,却没有把这些空白空间完全填满,因而在我们所看到的“15号”手稿的成稿中,前后两部分之间出现了如此多的空白。也就是说,虽然后半部分可能早于前半部分行诸成文,但前半部分关于露茜的故事则可能是后半部分的诱发起因,因而以其他某种方式早于后半部分成型。
琼斯猜测,华兹华斯先目睹并感慨露茜对小树林的蹂躏,然后才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那次采坚果之旅。这里面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第一,华兹华斯可能在多罗茜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先写下了前半部分,如果“19号”早于“15号”的话,这种解释是有可能成立的。我们知道,“19号”中有好几段诗行后来都出现在15号的前半部分中,包括他把头枕在露茜大腿上这个尴尬的场景(" And dearest maiden,thou upon whose lap/I rest my head,Oh! Do not deem that these/Are idle sympathies" )。当然,也可能多罗茜知道此事,但她在信中对柯尔律治作了隐瞒。如果当时华兹华斯兄妹对该诗的前半部分所涉及到的性暗示的确极度敏感、因而不愿轻易示人的话,那么多罗茜刻意向柯尔律治隐瞒这一层是完全不奇怪的,因为后者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兄妹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第二种可能性是前半部作为腹稿先于后半部分在华兹华斯头脑中成型,因为华兹华斯往往有在动笔之前打腹稿的习惯,有时甚至大段大段的诗行也是首先在头脑中完成,而后才行诸文字的。(16)
如果这两种可能性成立的话,那么该诗的结尾就是对前半部分的自然呼应,而非与全诗结构相抵牾的、突如其来的“败笔”;而且,这还可以解释华兹华斯为何在出版短本时仍然要坚持用这三行看似没头没脑的箴言来收煞——因为它作为一种文本标识或印记,提示着该诗的写作诱因以及另一个版本的存在。
还应该注意的是,加有标题的“24号”那份手稿被掌握在华兹华斯的妻子玛丽·哈琴森手中,这表明这个本子是在华兹华斯1799年5月从德国戈斯拉尔回英国后写成的(华兹华斯1800年才向哈琴森求婚,他们于1802年结婚)。里德认为这个本子是成于1800年6月5日左右,即华兹华斯离开Gallow Hill去格拉斯米尔之时。(17) 这个情况说明从1799年冬天到1800年夏天(《抒情歌谣集》出版前夕),华兹华斯急于出版短本;对于第一个长本(也即“15号”中的那个本子),他还在进行两个版本(“16号”和“24号”)的修改,而这两个版本都保留了作为全诗诱因的露茜的故事。
在弄清版本问题之后,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800年版的《抒情歌谣集》中,华兹华斯删去了前半部分露茜的故事,而仅仅保留了在结构上不完整的后半部分?对此,人们可以提出多种合情合理的解释。比如由于《采坚果》中的露茜与《露茜组诗》中的露茜的原型都是多罗茜,因此,长版开篇中那些具有明显暴虐和色情的暗示对于兄妹双方来说都是很尴尬的。(18) 其次,长本中所描述的“他与露茜一起躺在树丛中,并且他的头还枕在她的大腿上”的情景如果出版出来的话,华兹华斯——或许是多罗茜,或许是两个人——不会没有顾虑。此外,华兹华斯自己可能也会吃惊于他何以会去津津乐道地渲染一种女性的性暴力——即使这种描述是隐晦的和譬喻性的。最后,当《采坚果》于1800年(被收录在《抒情歌谣集》)出版时,华兹华斯正在向玛丽·哈琴森求婚,而当时在多罗茜与玛丽之间似乎的确出现过一些相互的嫉妒和敌视——这种嫉妒甚至也的确搀杂着些情欲的成分。(19) 所以,以上种种因素都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华兹华斯最后选择出版的是被删节过的短本而非最初写成的长本。
然而,这种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立,但仔细推敲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即它过分拘泥于零散的史料,并搀杂了非常多的个人臆断。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尚不足以彻底还原1798年至1800年间华兹华斯最真实、最本质的思想状态。因此,我们就将对《采坚果》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一点粗略的梳理和剖析,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对华兹华斯的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更深入认识。
二、批评谱系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对《采坚果》所作的最早的评论来自海伦·达比西尔(Helen Darbishire)。她认为《采坚果》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精神交感(spiritual sympathy)”。(20) 显然,这种解释十分体面,但对于诗中的露茜以及少年对树林的蹂躏摧毁行为中所隐含的性暴力意味却没有任何说服力。
五年之后,哈特曼注意到了这一层意义。他说,如果要用一幅寓意画(emblem)来描述华兹华斯的思想成长,最恰当的莫过于《采坚果》一诗中所呈现的“被蹂躏的闺阁”(a mutilated bower)这个意象。他指出,蹂躏树荫的场景经常出现在罗曼司文学——如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疯狂的奥兰多》——之中。然而,在《采坚果》中,华兹华斯却给这种主题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浪漫主义诗人通过挪用并超越罗曼司关于“花神和古老潘神”的陈词滥调而成为真正具有“人心的诗人”(a poet of the human heart)。这样一来,诗中的“闺阁”与其说指的是某一个真正的树荫,毋宁说象征着罗曼司文学这个古老的文类。《采坚果》的重要性也在于此,它几乎是“英国诗歌转折的标志:它一方面回顾了罗曼司传统,另一方面又预示了这个传统的衰落”,即这首诗代表着浪漫主义文学“从主题到主角(the themes and agents)对斯宾塞和密尔顿模式的全面人文化(humanization)”。因此,在哈特曼看来,该诗的真正主题是浪漫主义与罗曼司文学的冲突:只有通过对罗曼司文学的摧毁,浪漫主义才能够触及到“人心”,才能够呈现出浪漫主义与新教精神和启蒙精神同构的人文性。为了将诗中寓言性的奸暴行为与所谓的“人心”联系起来,哈特曼否认诗中存在着任何真正的人的行为。他说,尽管《采坚果》中蹂躏“闺阁”般秀丽的榛子林的行为有一点点“关于性和猎手的欲望的暗示”,但那是“纯粹心理性的”。因此,少年对榛子林的摧残不仅与真正的性、性别、强暴等问题无关,而且是浪漫主义对自然人文化的体现,是浪漫主义的成人仪式:“《采坚果》的主题不是自然中的生命或对这种生命的神秘展示,而是少年的执拗任性如何在同情性想像(sympathetic imagination)中逐渐臻于成熟。……对于少年而言,树荫以忍受和温柔来承受他的暴力;对于(浪漫主义)诗人来说,自然的被摧毁则是其心灵成熟的关键。……通过对树荫的蹂躏(这是罗曼司文学的典型主题),少年融入了自然而不是与自然分离。他的情感被逐渐人文化,《隐士》中有关想像与自然结合的主题在此已经被预示出来了。”(21) 这样,哈特曼以一种比海伦·达比西尔更为体面和圆通的方式避开了《采坚果》中的性暴力这个令老一代批评家多少有些尴尬的问题。
10年之后,另外两个批评家运用心理分析的批评方法对《采坚果》进行了新的解读。他们反对哈特曼将该诗的性寓言转化为纯粹的诗学问题,但与哈特曼一样,他们也故意弱化或降低了该诗的暴虐行为。布里斯曼(Leslie Brisman)一开始承认诗中描述了少年“对榛子林的摧残”,但他马上又说,“那些具有明显性暗示的描述与其说叙述了少年对树荫的奸暴,不如说是对一个精致的文本的破坏”。(22) 库克(Michael Cooke)虽然也承认诗中涉及到了少年对树林的暴力行为,但他却认为这种暴力行为仅仅只是一种比喻,通过这种比喻,该诗“摆脱了创伤和不正常的依恋情感,因而使得全诗关于成长的主题得以继续展开。”(23) 库克甚至认为,少年在摧残树林之后所感到的痛苦之情表明华兹华斯所伤害的是他自己潜在的“阴性人格”(feminine aspect)——他现在才认识到其存在,并将其组织到自己的人格之中。库克的结论与布里斯曼相似:通过对树荫“些微的施暴”(a little rape),诗人“毫无创伤地”建构起了一种雄性超我(a male superego)。(24)
尽管与哈特曼小心翼翼地予以绕开不同,布里斯曼和库克注意到了该诗中的性与暴力的因素,但他们却又几乎完全采用了前者的立场。如果说哈特曼将该诗的寓言非人化,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它的人文性,布里斯曼和库克则是通过承认少年的奸暴行为来颂扬该诗的人文性。一如哈特曼的解读,强暴行为是少年生命以及树荫生命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使得施暴者与受害者双方都成长为自己应该有的角色。所以,任何创伤经历都是个人成长历程中的必要阶段,不管它是寓言性的、真实的还是心理性的。
继布里斯曼和库克之后,一些批评家对《采坚果》进行了新的解读。他们对该诗寓意的挖掘与前者是一样的,但评价却是否定性的。罗斯(Marion Ross)、阿里克(Jonathan Arac)和雅各布斯(Mary Jacobus)都认为,该诗典型地反映了男性是如何通过对女性进行社会-历史的征服来确保其男性自我意识的成长的;他们都认为,对具有女性性征的树荫(以及其代理人露茜)的征服是华兹华斯成人仪式的必要步骤。他们也都认为,《采坚果》认同并再现了当时有关两性差异的主流观点,也就是将女性视为男性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牺牲品或献祭物。
罗斯声称,在该诗中,“姑娘以及自然都不可能成为行使任何形式的身体侵犯(如性侵犯)的主体”,而恰恰是这种不可能性在诗中“被转化为(侵害与被侵害)双方达成心理和谐的前提”。(25)
这些批评家无一例外地都把诗中“闺房”般的树荫定位为女性:它或者象征着处女(1970年代以前的观点),或者象征母亲(70年代以后的观点);但不管怎样,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对那片女性树荫的暴行是小男孩成人的必要手段。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批评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被摧残的树荫而非最后那个被规劝的姑娘身上。小男孩的暴行或者被解释为对处子般贞洁的自然的摧残,或者是对自然母亲所施予的暴行。
进入90年代,《采坚果》的研究谱系中增加了新的理论因素。克劳福德从拉康理论出发来分析该诗。她注意到该诗赋予了树荫双重性别特征:秀丽的榛子林并非完全是阴性的,“高而挺拔”的树枝以及饱胀的坚果都表明这座林子也具有雄性性征。从此出发,克劳福德认为诗中的少年所摧毁的不单单是母亲的形象,而是父亲和母亲的双重形象,因此使得他能够把自己从父母/子女的垂直关系中解脱出来,建立起了成人-兄长/处女-妹妹的水平关系。但她的结论与上述研究者几乎还是一样的:妹妹的形象在该诗中被压抑了,其目的还是为了确立诗人自己的男性主体。(26)
克劳福德认为《采坚果》具有双性特征的观点启发了琼斯。在《对华兹华斯〈采坚果〉解审查》一文,琼斯从该诗的性征混乱和互文性两个问题入手,对《采坚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读。(27)
受克劳福德的启发,琼斯也认为,虽然闺阁般纯净的林荫在性暴力的侵犯下,最后“顺从地献出了其文静之身”,因而在性属上应该是女性,但榛子树“高而直,/悬着簇簇诱人的榛子”又表明这片林荫同时也具有男性性征。因此这片榛子林作为被性侵犯的对象,其侵犯者既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这是该诗性别混乱之体现。此外,琼斯还注意到全诗结尾处“闯入的天空”这个奇怪的意象所蕴涵的性别混乱。琼斯指出,“闯入的天空”首先是一个结构性因素,它将长本和短本两个故事统一了起来,即将华兹华斯从少年经历的回忆中唤醒过来,重新意识到露茜在眼前的存在:由于露茜的蹂躏,眼前也是一片“闯入的天空”。此时,两个相隔了数年之久的蹂躏行为最终在这个时间之点中被融合了起来。也就是说,“闯入的天空”这个意象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将全诗组织成为一个首尾呼应的统一整体——如果没有长本的存在,这个意象的结构功能是难以理解的。
然而,“闯入的天空”在修辞上却属于词的误用(catachresis):无形的天空何以能够像有形的阳具一样“闯入”或刺入某一片领域?琼斯认为,这恰恰是全诗之眼,是理解华兹华斯对于性、欲望等问题构想的钥匙:“闯入”的观念——刺入、侵犯、强奸——是一个修辞建构。只要你那样去想像,“非闯入性的”(unintrusive)天空(它本身高高在上、具有母性、沉静)也可以转化为像阳具那样具有侵略性的器物。直言之,性侵犯甚至性闯入(sexual intrusiveness)不必决定于是否拥有实在的男性性器。女性的性要求也可能是狂暴和具有侵犯性的——就如同天空也可以闯入树林一样。因此,“闯入的天空”是诗中的枢纽,它使得女性的“粗野交媾”(rude intercourse)成功地取代了男性的“强暴”观念。
琼斯还通过考证该诗的互文性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可能是受到哈特曼的启发,琼斯也认为《采坚果》一诗是对罗曼司这个古老文类的刻意挪用和改写(克劳福德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没有对此作进一步展开)。他注意到,在《采坚果》中,华兹华斯至少与密尔顿的《失乐园》、维吉尔的《埃涅伊特》、斯宾塞的《仙后》、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以及莎士比亚的《如愿》等前罗曼司名著构成复杂的互文纠结。限于篇幅,我们只简要介绍“鸽庐手稿16号”本子与莎士比亚的《如愿》之间的互文关系。
在“鸽庐手稿16号”这个本子中,华兹华斯把露茜与《如愿》(As You Like It)中的奥兰多联系起来:“Thou,Lucy,art a maiden‘inland bred’/And thou has‘know some nurture’…”。其中的直接引语“inland bred”和“know some nurture”都来自《如愿》的第2幕第7场。当老公爵(Duke Senior)和杰开斯(Jaques)坐在阿顿森林的树荫下用餐的时候,奥兰多持剑而上,要求他们把食物分一些给他和他的仆人亚当吃。老公爵便问道:“你是迫于患难才这样强横,还是天生的没有礼貌才这样的粗鲁呢?”奥兰多回答说:“你是第一下就猜着了:患难的锐尖夺去了我的礼貌;但我是内地生长的(I am inland bred),颇知一些礼教(And I know some nurture)。但是止住,我说:在我的事情没办完之前,谁敢动这水果,谁就是死。”(28) 但老公爵和杰开斯没有在意他的无理与恫吓,而是以宽厚和慷慨接待了他。这使得奥兰多不得不为自己的粗野抱歉和辩解:“我请你们饶恕我:我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野蛮的,所以我板起威吓的面孔。”(I thought that all things had been savage here,/And therefore put I on the countenance/Of stern commandment)这即是说,当置身于野蛮之地,奥兰多就准备以野蛮面孔示人;而如果置身于礼仪之邦,他就会因此而变得温良恭谦——如果不是置身于一个具体的场景之中,奥兰多也就几乎无法确定他的真正身份。
或许和奥兰多一样,露茜的野蛮行经也是源自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她当时处身于一个野蛮的场景之中。而华兹华斯本人则像老公爵一样告戒露茜说,这片林子并不蛮荒,而是“温柔的”,这样,露茜就应该“怀着温柔的心”,以“温柔的手”来“轻抚”她。但是将露茜等同于奥兰多的用意还不止这些。奥兰多不仅是男性,而且一开始还显然故意炫耀他的雄性暴力;这样一来,《采坚果》的读者一开始会自然地将树林的性属定位为女性,那么手持铁钩侵犯树荫的露茜也自然被等同为与奥兰多一样的男性强暴者(male rapist)。
因此,通过将露茜与奥兰多联系起来,华兹华斯不仅给露茜赋予了男性性征,而且还使我们联想起典型的莎士比亚式喜剧/罗曼司世界(Shakespearean comic/romantic world):其中的人物总是频繁地将自己伪装成其他的性别(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威尼斯商人》)。这样,《采坚果》的性别混乱就似乎不是不经意的结果,而是作者的精心设计。
在华兹华斯的作品中,没有其他任何一首诗像《采坚果》那样用引号直接引用莎士比亚。琼斯认为这种对文艺复兴时期诗学模式的直接借用使得华兹华斯能够言说那些18世纪诗学词汇所无法言说的话题,如性别混乱、狂暴的性幻想以及女性对独立性取向的渴望等问题。换言之,华兹华斯是以文学的方式或文学史角度来言说或探讨某些激进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18世纪末的英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通过刻意的用典,华兹华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关于性和性别的激进话语,而后者恰恰是被18世纪英国正统社会规范所排斥和压抑的。比如,通过将露茜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男性角色相联系,华兹华斯表明,露茜的性属,或者说性属本身在本质上仅仅是表演性的,即任何性属都可以像道具一样根据表演的需要而任意更换——就如同环球剧院中饰演女人的男演员一样。华兹华斯想要阐明的是,不管是在生理上或是社会意义上,性和性属都是含混和不稳定的。推而广之,任何既定的话语疆界都是非本质性的,因而都是可以被逾越、打破和解构的。
琼斯总结说,只有把《采坚果》的长本和短本结合起来阅读,我们才会发现华兹华斯创造这首诗的真实用意:一是幻象革命理想(a visionary manifesto),另一个则是个人化的恳请(personal plea)。这两个目的在长本和短本的结尾部分都是一样的。就前者而言,华兹华斯所要言说的对象是我们——读者:性与性别等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具有先在的本质,而是可以被想像、被构建、被塑造的。就第二个目的,即个人化的恳请而言,华兹华斯的言说对象仅仅是露茜一人。不管他有多么激进的思想,但对于露茜的激进(越轨行为)他却是恐惧的:在1798年的那个冬天,在戈斯拉尔,多罗茜几乎就是华兹华斯全部的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柱。当他意识到多罗茜所表现出来的独立的性取向时,华兹华斯是矛盾的:在理论层面上,他认可之,但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他又担心甚至恐惧因此而失去多罗茜。在全诗结尾的“用温柔的手”、“怀着温柔的心”的恳请(plea)表明,露茜的确具有某种让他恐惧的另类、反叛的欲望形式,因此他恳请她用“温柔”这个能够为18世纪英国社会所认可的女性美德将这种反叛欲望予以控制。华兹华斯的矛盾性便体现在这里。
因此,《采坚果》一方面是一首激进的政治性作品(a political poem),因为它倡导了一种颠覆性的性和欲望模式(这在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是非常革命性的,对于未来更是具有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采坚果》又是一篇个人生平记录(personal record),因而也就极大地限制了其政治理想的广度:将多罗茜的后半生与《采坚果》联系起来并以之来裁定《采坚果》可能会有些过分,但我们又不得不将它们联系起来:他关于露茜要“温柔”的忠告是否发生了作用?而1798年后多罗茜后半生的遭遇——她终生未嫁,在生活和情感上都依附于华兹华斯(这种依附从她的《日记》中可以清楚看到);感情和性方面极度的压抑;长年卧病在床;后20年精神失常——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就充分理解了《采坚果》版本的复杂性。一方面不停地修改各种长本,但却又选择出版删节过(删掉了露茜的“粗野交媾”场面)的短本,这个事实充分表明了1798年至1800间华兹华斯的个人生活与政治态度内在的矛盾性。
琼斯的论文发表于1996年。三年后,另一位批评家又对琼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29) 皮里茨(Janice Haney Peritz)在《性政治与〈采坚果〉》一文中指出,版本问题不是《采坚果》一诗的主要问题,原因很简单:1800年版的《抒情歌谣集》中的短本所描述的事件并未真实存在或发生过,它可能只是华兹华斯一时兴起的“胡诌”(a nonsense)或“幻想碎片”(a fragment of fantasy)而已,“那些长本和晚些时候成稿的本子仅仅是作者为了给那个信手写意之作——也即幻想碎片——添加一个使其看似真实的起因的尝试”,但那些尝试努力显然是“不成功的”,作者自己也可能不满意,因而才没有付梓面世。这样一来,所谓“删节”或“自我审查”问题就纯粹是琼斯等人子虚乌有的臆断。皮里茨认为,《采坚果》收煞处关于“温柔”的规劝之辞并非如琼斯所说是华兹华斯面对多罗茜日渐流露的性独立意识,从而担心自己终究会失去多罗茜的私心,因而便对此前自己所构想并认可的颠覆性话语的躲闪或规避;恰恰相反,由于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妇女权利一辩》等著作中对卢梭关于妇女美德论述的批判,“温柔”一词在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中负载着相当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代表着一种旨在使妇女在身体和德行等各方面都得到解放的“颠覆性的美德政治”(a subversive politics of virtue),而非卢梭在《爱弥尔》中所鼓吹的那种女性对于男性哈巴狗似的附庸和奴性。《采坚果》中的“温柔”就应该在这个背景之下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华兹华斯是如何在诗歌创作中实践了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激进的政治思想的。
此外,皮里茨还发现,《采坚果》的文本结构与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一段有关1789年10月6日早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尤其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受辱的描述非常相似。在柏克的描述中,“一伙残忍的暴徒和刺客”在杀死卫士之后,“闯进王后的卧室”几乎强奸了美丽的王后;接下来,王室成员从凡尔赛宫中被强行带到巴黎游街示众,“周围尽是可怕的呻吟和尖厉的叫声与激动的颤抖和下流的谩骂,以及以最下贱的女人撒泼的姿态像魔鬼发疯般地展现的种种难以言表的恶行”;最后,高贵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以一种穆肃的忍耐、以一种适合她的身份和门第”的态度忍受了那些以革命名义而实施的暴行。行文至此,柏克忍不住感慨道:“啊!是什么样的革命!我必须要有怎样的一颗心,才能不动感情地观照那场升起和那场没落!”(30) 皮里茨认为,《采坚果》的基本情节框架几乎是柏克故事的翻版,但在时间顺序上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他暗示,《采坚果》基本上是对柏克故事的刻意改写,通过这种改写,华兹华斯想要表明的是:“尽管革命行为具有暴力性,但这种暴力却并非不道德的。对榛子林无情的蹂躏(隐喻性地)开辟出了一片……‘更新想像力’的新天地,这个行为本身包含着(诗人)主体追求崇高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他能够获得一种美丽而坚韧的‘精神力量’”。(31) 如果说,琼斯对《采坚果》的政治-历史解读还因为所谓“自我审查”说而有所保留的话,皮里茨则从暴力革命(颠覆柏克)与美德政治(认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两方面对《采坚果》进行了完全肯定性解读,从而将华兹华斯从女性主义的责难中彻底解救了出来。至此,对华兹华斯以及《采坚果》的批评似乎又回到了海伦·达比西尔和哈特曼等人的肯定性评价,但这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肯定了。
综上所述,《采坚果》一诗不仅牵涉到一段复杂的版本公案,而且这段复杂的版本公案又引发出了一段甚至更为复杂的阐释公案。就目前的史料看,前者基本可以定论;而后者却似乎仍然没有终结,而且还可能会永远“延宕”下去。但不管怎样,如果说《采坚果》难以为我们确切地证实华兹华斯某个具体的诗学观或政治观的话,那么,其版本考辨史和批评史至少可以证伪一个论点:华兹华斯是美学上的自然派诗人(nature poet)和政治上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
注释:
①黄杲炘译为《采硬果》。见黄杲炘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90页。本文中《采坚果》的中文译文基本引自黄杲炘先生的译本,个别地方有改动。
②由于批评界已经约定俗成地用“华兹华斯”来指威廉·华兹华斯,用陶乐茜来指多罗茜·华兹华斯——这甚至还引起了某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不满,但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一称谓。
③David Ferry,The Limits of Mortality:An Essay on Wordsworth' s Major Poems,Middletown:Wesleyan UP, 1959,p.25.
④David Perkins,Wordsworth and the Poetry of Sincerity,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1964,P.184.
⑤Geoffrey Hartman,Wordsworth' s Poetry:1787-1814, Cambridge:Harvard UP,1964,pp.73-75.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伍德灵的书中Carl Woodring,Wordsworth: Riverside Studies in Literatur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8,pp.64-66。
⑥Marjorie Levinson,The Romantic Fragment Poem:a Critique of a Form,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6,p.60.
⑦⑩(12)E.de Selincourt,ed.,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vol.2,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44,pp.504-506; p.504; p.504.
⑧(11)(17)Mark L.Reed,Wordsworth: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Years,1770-179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331-332,pp.331-332,p.332.
⑨(16)(27)Gregory Jones," Uncensoring Wordsworth' s ' Nutting' " ,in 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35,Number 2,Summer 1996,p.215,p.216,pp.213-243.以下有关琼斯的观点均出自该文,不再一一注释。
(13)(14)(15)James Butler & Karen Green,ed.,Lyrical Ballads, and Other Poems,1797-1800 (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18,p.391,pp.391-92,p.551.
(18)在给其妻子的一封信中,当时也旅居在德国的柯尔律治曾经提到,那里的德国人都以为华兹华斯兄妹是一对情人:“他把他的妹妹带在身边是一步错棋(a wrong Step)——在德国,只有已婚的女人或穿着已婚服饰的女人才可以被介绍给客人。(在这里,)妹妹(Sister)这个词仅仅用来称呼情妇(Mistress)。”(14 January 1799)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V.I,rd.Earl Leslie Griggs,Oxford:Clarendon,1956,P.270。
(19)贝特森曾经指出,《萤火虫》“the Gloworm”是一首晚些时候写成的《露茜》诗,显然该诗最初也是写给多罗茜的,但掌握在Sarah Huchinson手中的手稿中,“露茜”被“玛丽”所替代。贝特森猜测,华兹华斯可能是想要安慰他那妒火中烧的妻子,因而才将原诗稍作改动,假装成那是献给玛丽的。但我们知道《萤火虫》中的露茜的确是多罗茜,因为在华兹华斯致柯尔律治的一封信中有该诗的另一个版本,在那个版本中,诗中的女人名为“爱玛”——而“爱玛”常常是华兹华斯诗中专指多罗茜的代名。而且,在该封信里华兹华斯还明确注明:“诗中所描述的是大约七年以前发生在多罗茜与我之间的事情”。参见 Reed,p.228。
(20)William Wordsworth,The Prelude,ed.E.de Selincourt,2[nd] revised Edn Helen Darbishire,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9,p.610.
(21)Geoffrey Hartman,Wordsworth' Poetry:1787-1814,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pp.73-74.
(22)Leslie Brisman,Romantic Origi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p.298-300.
(23)(24)Michael Cooke,Acts of Inclusion:Studies Bearing on an Elementary Theory of Romantic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149,pp.299-300.
(25)Marlon Ross," Naturalizing Gender:Women' s Place in Wordsworth' s Ideological Landscape," ELH 53.2,Summer 1986,p.394.
(26)Rachel Crawford," The Structure of the Sororal in Wordsworth' s ' Nutting' " ,Studies in Romanticism vol. 31,Number 2,Summer 1992.
(28)中文译文引自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下同。
(29)Janice Haney Peritz," Sexual Politics and the Subject of ' Nutting' :Question of Ideology,Rhetoric,and Fantasy" ,in 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38,Number 4(Winter 1999),pp.559-595.以下有关皮尔茨的观点均出自该文,如非必要,不再一一注释。
(30)参见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4-101页。皮里茨没有注意到,《采坚果》的各个长本都以“Ah! What a crash was that!”开头,这与柏克的“啊!是什么样的革命!”之句式非常相似。这是否可以进一步印证《采坚果》的确是对柏克的刻意挪用和改写呢?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皮尔茨完全否定长本的意义,因而他也就难以体察到这个重要的相似点。而且,柏克还用讽刺的口吻强调说,玛丽-安托瓦内特受辱的那天是个“美好的日子”——《采坚果》短本的开头句也几乎是一样的:“It seems a day,/one of those heavenly days which cannot die”。这也是皮尔茨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总的来看,皮尔茨的解读有点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方法的味道。这种方法本来应该使得皮尔茨在深度和广度上对《采坚果》的阐释取得激动人心的成果,但显然由于皮尔茨的史学修养不足,史料掌握不够(尤其是固执地否定版本史料的价值),从而使得他对《采坚果》的解释力度大打折扣。
(31)Janice Haney Peritz," Sexual Politics and the Subject of ' Nutting' :Question of Ideology,Rhetoric,and Fantasy" ,in 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38,Number 4 (Winter 1999),p.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