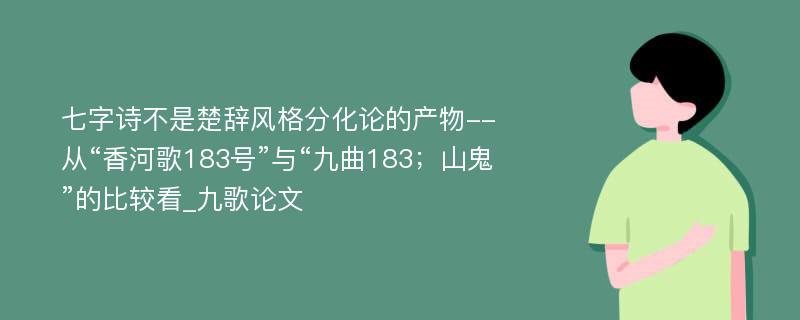
七言诗并非源于楚辞体之辨说——从《相和歌#183;今有人》与《九歌#183;山鬼》的比较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九歌论文,七言诗论文,山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8)03-0095-06
七言诗源于楚辞体,是现代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沈约《宋书·乐志》中在《相和》曲的名目下收录《今有人》一首诗歌,与《陌上桑》属于同曲,又署名《楚辞钞》。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它收录到第二十八卷《相和歌辞》三之中,属于相和曲,署名相同。这首诗歌从文辞上看完全是从《九歌·山鬼》改编而来(仅比原诗少了11句),因而古今学者多把它视为七言诗从楚辞中演化而来的最重要材料或者直接证据。现代学人中,余冠英先生注意到了二者在吟讽时节奏上的不同,认为二者“并非一类”,可惜并没有就此做详细论证。① 本人认为,由此入手,应该是探讨七言诗与楚辞文体特征的一个很好个案,故试就两诗略作比较,以期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先把两首诗原文引到下面:
《山鬼》 《今有人》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罗。 被服薜荔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 既含睇,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恋慕予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 乘赤豹,从文狸,
辛夷车兮结桂旗。 辛夷车驾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 被石兰,带杜衡,
折芳馨兮遗所思。 折芳拔荃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 处幽室,终不见,
路险难兮独后来。 天路险艰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 表独立,山之上,
云容容兮而在下。 云何容容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 杳冥冥,羌昼晦,
东风飘兮神灵雨。 东风飘摇神灵雨。
……
风飒飒兮木萧萧, 风瑟瑟,木搜搜,
思公子兮徒离忧。 思念公子徒以忧。
一、两诗间的因袭改写不等于文体的演化
从上面两首诗可以明显地看出,《今有人》的确是从《山鬼》改编而来的,文辞基本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我要提的问题是,根据这两首诗之间的改编关系,就能说明七言诗源于楚辞体吗?从逻辑学上看我以为是讲不通的。因为《今有人》与《山鬼》之间的文辞相同,说到底只是两首诗之间的改编或者因袭关系,并不代表楚辞体与七言诗这两种诗体之间的演化。考察现存的汉魏七言诗与楚辞体诗篇,像《今有人》与《山鬼》这样的情况,仅此一例,可见它是一种个别现象。当然,个别现象也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不能轻易否定。不过我们在考察楚辞体与七言诗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时,以下三点不能不特别受到关注。第一,《今有人》一诗见于沈约的《宋书·乐志》,属于相和歌,而相和歌这种艺术形式之盛行,是在东汉以后,而早在此之前的西汉已经有了不少七言诗句,特别是从一些民间谣谚、铜镜铭文乃至《急就章》等字书里的七言诗句来看,找不出脱胎于楚辞的明显痕迹。第二,作为楚辞体的重要体式之一的《九歌》体句式,在汉代的楚歌里继续存在,从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辞》一直到东汉后期少帝刘辩的《悲歌》、唐姬的《起舞歌》等,以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作为这种文体的基本定式传承下来。在这些诗篇里,每首诗的诗句可能在字数上略有变化,如有的是“○○○兮○○○”的形式,有的是“○○○○兮○○○”的形式,还有的是“○○○○兮○○○○”的形式,但是一句诗中间的这个“兮”一直没有改变,它们并没有演变为七言诗。由此可见,认为楚辞体可以演变为七言诗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受了《今有人》与《山鬼》这两首诗文辞基本相同这一假象的误导,而把这两首诗之间的文字偶然相同看成了两种诗体相类的力证。
其实,如果不是受这种现象的误导,我们试着把楚辞体中的“兮”字去掉或者略加整理,就会发现楚辞体并不是必然要变成七言诗,还完全可以形成三言、五言、六言等另外几种不同的样式,但是这些诗体是不是都是从楚辞体中演化而来的呢?显然不是。请看下例:
(1)《九歌》体句式:“若有人兮山之阿”,若把“兮”字去掉,可以变成“若有人,山之阿”两个三言诗句,这本是楚辞的变体在汉代最常见的现象,典型的例证是《史记·乐书》中记录的汉武帝时的《天马歌》是:“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而到了《汉书·礼乐志》中则变成了“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不过,这两个例子只能说明三言诗与楚辞体之间有转化的条件,并不能说明三言诗是从七言中转化而来的,因为三言诗的起源远比七言诗要早。《周易》中早就有三言诗存在,如《周易·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周易·旅卦·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
(2)《九歌》体句式:“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若把“兮”去掉,可以变成“帝子降北渚,目眇眇愁予”这样的五言句。但是表面上的字数相同并不能说明五言诗是从这种句式中转化而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个五言句虽然去掉了“兮”字,可是还保持着《九歌》体的二分节奏,其节奏形式是3+2式,而五言诗却是三分节奏,其节奏形式是2+1+2或者是2+2+1。所以,五言诗也不是从《九歌》体中流变出来,它同样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②
(3)《离骚》体句式:“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两句,若把“兮”字去掉,也可以变成“帝高阳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这样的六言句。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因为这样的六言诗句的音乐节奏特征并不明显,所以,作为楚辞体式的另一重要体式的《离骚》体句式,并没有发展成六言诗,却仍然是汉代的骚体赋中的基本句式;而作为这种句式的变体,即去掉“兮”字的形式,则大量存在于散体赋当中。如:
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
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
临朱汜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
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
——枚乘《七发》
轶陵阴之地室,过阳谷之秋城。
回天门而凤举,蹑黄帝之明庭。
冠高山而为居,乘昆仑而为宫。
按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闳中。
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
——刘歆《甘泉宫赋》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虽然楚辞体经过变化,从表面上看可以形成三言、五言或者六言。不过,从文体发展的渊源关系来看,三者当中,楚辞体与骚体赋和散体赋中的六言句的关系最为接近,是一种直接的演化关系,而三言与五言这两种诗体都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都不是从楚辞体中演化而来的。同样,七言诗与楚辞体也不是一种直接的演化关系。因为七言诗与楚辞体有着不同的诗体特征,这就是本文下面要谈的问题。
二、二分与三分:楚辞体与七言诗在音乐节奏上的巨大差异
中国早期的诗歌是可以歌唱的,歌词的形成本来就与音乐相关联。就文体特征而言,诗是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的加强形式。所以,要研究中国诗歌体式的发展演变问题,光从文字表面进行简单的比较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要把握节奏和韵律这一诗所以成之为诗的根本性特征。从这里出发,我们首先会发现,楚辞体与七言诗在节奏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从比较《山鬼》与《今有人》这两首诗开始。这两首诗表面看起来只是文字上略有变化,其实已经是两首不同的诗歌。从音乐分类角度讲,《山鬼》是楚歌,《今有人》是相和歌,两者属于两个不同音乐系统的歌曲;从声律节奏角度讲,《山鬼》是典型的二分节奏的诗歌,《今有人》则是二分节奏与三分节奏交错为用的诗歌,而七言诗则是三分节奏的诗歌。再从诗句的语言结构角度来看,受二分节奏的制约与影响,《山鬼》一诗每一句的语言以“兮”字为标志,前后各形成一个三字组的结构;而在三分节奏的制约与影响下,《今有人》中的七言句式则形成整齐的前面两个二字组与后面一个三字组的结构。二者的区别正从这两首诗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试比较:
被薜荔兮/带女罗。被服/薜荔/带女罗。
辛夷车兮/结桂旗。辛夷/车驾/结桂旗。
折芳馨兮/遗所思。折芳/拔荃/遗所思。
路险难兮/独后来。天路/险艰/独后来。
从上例比较中我们会发现两个重要现象:第一、在楚辞体的《山鬼》中,“兮”字承担着重要的音乐功能,由于有它的存在而使诗歌的二分节奏特点非常明显;而《今有人》中的七言句却明显地形成了三分节奏。在由二分节奏到三分节奏的转换中,把“兮”字去掉是关键的环节。因为只有去掉了这个“兮”字,才能打破楚辞体原诗的二分节奏,才有变成三分节奏的可能。如果不去掉这个“兮”字,即便是在原诗的基础上再增加字数,也没有变成三分节奏的可能,如楚辞《招魂》的末段:
路贯庐江兮/左长薄,
倚沼畦瀛兮/遥望博。
青骊结驷兮/齐千乘,
悬火延起兮/玄颜烝。
不包括“兮”字,每一句都可以看成是七言诗,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兮”字,它无论如何还是一个二分节奏的诗体,这说明《九歌》体的确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诗体,其特点就在每一个诗句中间这个“兮”字,这个“兮”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承担着多种虚词的功能,如“于”、“之”、“以”等等,③ 但是从语言结构上讲却完全可以去掉,并不影响诗句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兮”字的主要功能是起着强化诗歌音乐节奏的作用。正是因为它的存在而使这一诗体的音乐节奏加强,更便于歌唱,就是读起来也是摇曳生姿而又朗朗上口,同时又使得这一体式的二分节奏形式不可更易,使得“兮”字前后的两个词组各自具有不可分割性,与二分节奏紧密结合。所以,这类诗篇即便是去掉“兮”字,也仍然是非常鲜明的二分节奏的诗歌。例如,像《山鬼》这样的诗篇,如果仅仅把“兮”字去掉而不在诗句的组织形式上进行变换,它只会变成这样的三言诗:
若有人,山之阿;
被薜荔,带女罗。
既含睇,又宜笑;
子慕予,善窈窕。
在这样的三三诗句中,每一句都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结构,我们是不可能在原来的“兮”字的位置上加入任何一个实词的。第二、由于《九歌》体的二分节奏十分固定,由此而形成了前后两个词组鲜明的独立性,即便是把原诗中的“兮”去掉,它的二分节奏特征仍然不会改变。所以,要想把它变成三分节奏的七言诗,除了去掉“兮”字之外,还要通过词语的增加和句式的重组才能打破原诗的二分节奏。这个新增的词语,大多数情况都不会出现在原来“兮”字的位置上,而要更换位置。更换位置的原则就是要把原诗中前面那个三字结构变成两个二字结构,从而达到把原来的二分节奏结构变成三分节奏结构的目的,亦即由二分节奏的“○○○兮○○○”变成三分节奏的“○○/○○/○○○”。如原诗中“被薜荔兮带女罗”这样一个二分节奏诗句,改编后的新诗没有在原来的“兮”字的位置上加字,而是在原诗的第一个字之后加一“服”字,从而使其与原诗中的“被”字组合在一起,变成“被服/薜荔/带女罗”这样的一个新的三分节奏诗句。
由此可见,楚辞体与七言诗在文体方面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有两个方面。从音乐上来讲主要是二分节奏与三分节奏的差异;从语言结构上来讲,则是句首的一个“三字组”与两个“二字组”的差异。从《山鬼》到《今有人》的改编实践说明,从楚辞体中是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的。
三、楚辞体与七言诗的主要句式结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种诗体不同的句式结构。《九歌》体以“兮”字为标志而把一个诗句分成两个节奏单位,从而使其节奏具有固定性。仔细分析,《九歌》体这种中间带“兮”字的句式,按字数多少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每句在“兮”字的前后各有两个字,即“○○兮○○”的句式,组成了一个典型以二言为一节奏的二分节奏诗歌形式,如: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礼魂》)。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湘君》)。
第二种情况是每句在“兮”之前三个字,之后两个字,即“○○○兮○○”的句式,组成了一个以三言加两言的二分节奏形式,如: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湘君》)。
浴兰汤与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
第三种情况是每句在“兮”字前后各三个字,即“○○○兮○○○”的形式,组成了一个以三言为一节奏的二分节奏形式,如: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国殇》)。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
《九歌》共有255个单句,其中第一种句式只有30句,占总句数的11.8%;第二种句式有162句,占总句数的63.5%:第三种句式有60句,占总句数的23.5%。以上三种句式占《九歌》总句数的98.8%。这三种句式如果以数量多寡来算的话,那么第二种句式,即前三后二的“○○○兮○○”的句式就是最典型的句式,第一和第三种都是它的变体。此外《九歌》、《招魂》中还有前三后五、前四后二、前四后四等少数几种句型,也是同一类型的变体。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句式的关系,也就是正体和变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从文字形式上看,这几种句式虽然有字数多少的不同,但是它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都是把“兮”字置于一句之中,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前后结构;其次是从阅读与涵咏的角度来体会,我们同样会感觉到,不管这三种句式的字数有多少的不同,它们同样是二分节奏。请看下例:
吉日兮/辰良(《东皇太一》)
烂昭昭兮/未央(《云中君》)
若有人兮/山之阿(《山鬼》)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湘君》)
夫人自有兮/美子(《少司命》)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山鬼》)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菉苹齐叶兮/白芷生(《招魂》)
仔细体会,这些句子虽然有长有短,但是因为有“兮”字这个标志性的词语,我们都要按照二分节奏来读。这说明,节奏的固定在楚辞体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对《九歌》的句式结构和每句字数的多少给了基本的规范,同时又赋予这一诗体以一定的张力,在节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在字数的多少上有一定的调节。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句式无论有多大的张力,只要这种二分节奏没变,中间的“兮”字没有去掉,无论字数上有什么变化,它都不可能直接变成七言诗。
在楚辞体中,以《离骚》、《九章》为代表的一些诗篇在句式上与《九歌》表面上有所不同,它们的主要诗体形式是两句一组,在每一组的上句末尾有一“兮”字。这个“兮”字不再像《九歌》体那样起着强调每句诗的二分节奏的特点,可是这些诗篇照样是每句非常鲜明的二分节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离骚》体的句式中,每一句的中间几乎都有一个虚词起着强化二分节奏的作用。如: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离骚》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九章·惜诵》
这里的虚词在句中不仅具有语法作用,同时具有节奏分割的作用,通过这两种作用,《离骚》体句式也成为典型的二分节奏,亦即每句诗由两个相对独立的词组组合而成。
《离骚》的句子有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等不同,据廖序东统计,“上句不计‘兮’字,372句中,六言句278句,占总句数的四分之三,即每四句中就有三个六言句,七言句55句,次之。五言句又次之,28句。八言句10句,九言句1句。”在这些句子里,“虚字大多数是用在句子的倒数第三个字的位置,这是标准的位置。”④ 廖序东的这个统计非常有意思。他在这里所说的《离骚》体以六言句为主,虚字在倒数第三字的位置上,其实也就说明:在《离骚》体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句子的句首都是“三字组”。所不同的是,《九歌》体的句首三字组后面是“兮”,其典型句式是“○○○兮○○”,而《离骚》体的句首“三字组”后面则是其他的虚词,其典型句式是“○○○▲○○”。在这里,由于《九歌》体中间用的是“兮”,所以它的音乐节奏性非常明显;而《离骚》体中用的是其他虚词,不便于歌唱,因而有明显的散体化趋势。我一直怀疑《离骚》可能只是用于吟诵的诗体,就因为它把《九歌》体中的“兮”字变成了其他不便于歌唱的虚词。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作赋以讽”,是“贤人失志之赋”,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也就是为什么《离骚》体句式在汉代继续在骚体赋和散体赋中存在的原因之一。
七言诗的句式结构其实很简单,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战国后期到汉代的七言诗中,几乎所有的七言诗句都是三分节奏的。而且这种三分节奏的基本形式是前面两个二字组与后面一个三字组。如:
愚暗/愚暗/堕贤良。
如瞽/无相/何伥伥。
荀子《成相》
马饮/漳邺/及清河。
云中/定襄/与朔方。
代郡/上谷/右北平。
辽东/演西/上平冈。
《急就篇》第三十四章
汉有/善铜/出丹阳,
和以/银锡/清且明,
左龙/右虎/主四彭,
朱爵/玄武/顺阴阳,
八子/九孙/治中央。
西汉镜铭
日月/星辰/和四时。
骖驾/驷马/从梁来。
郡国/士马/羽林材。
总领/天下/诚难治。
《柏梁台联句》
空桑/琴瑟/结信成,
四兴/递代/八风生。
殷殷/钟石/羽钥鸣。
《郊祀歌十九章·天门》
天长/地久/岁不留,
俟河/之清/祗怀忧。
张衡《四玄赋系诗》
把七言诗的句式与楚辞体句式相比较,除了三分节奏与二分节奏不同之外,二者的词语组合方式上的不同也就非常明晰了。如我们上文所言,楚辞体的典型句式有两种,一种是《九歌》体的典型句式“○○○兮○○”;一是《离骚》体的典型句式“○○○▲○○”,都与七言诗相差很远。其实,在谈到楚辞体与七言诗之关系时,学者们所看重的,也不是楚辞体中的这种典型句式,而是看中其中的变体句式,特别是《九歌》、《招魂》中的“○○○兮○○○”乃至“○○○○兮○○○”句式,往往认为七言诗是从这些楚辞中的变体句式中变化而来。其实这可能是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因为变体句式虽然有所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楚辞体句式以“兮”字为标志的二分节奏特征。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汉代存在的大量的楚歌,从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辞》一直到东汉末年的汉少帝刘辩的《悲歌》、唐姬的《起舞歌》等,几乎都是《九歌》体典型句式的变体,但是它们在汉代都被人们称之为“歌”,都与当时流行的七言诗没有关系。这同样说明七言诗不会是从楚辞体自然转化而来。
以上,本文从《山鬼》与《今有人》的比较入手,分析了楚辞体与七言诗的关系。旨在说明,二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诗体,差别很大。从表面的文字形式上看,楚辞体有接近七言的句式,在汉代还有楚辞体句式与七言句式混用的情况,有个别诗句把“兮”字去掉甚至可以看成是典型的七言句式。这说明楚辞体在七言诗形成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其他文体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小说与戏曲、诗与词、词与曲之间都有影响关系。但是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诗体特征上的差异非常之大。所以,七言诗不可能是从楚辞中脱胎演变而来。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关于七言诗起源以及其与楚辞体的关系问题比较复杂,本文所写,只是就七言源于楚辞这一说法而进行的一点辨析,不当之处,尚请各位方家指正。
收稿日期:2007-11-01
注释:
① 参见余冠英《七言诗起源新论》,《汉魏六朝诗论丛》,中华书局1962年2月上海新1版第132页。
② 关于五言诗的节奏,有的人认为是二分节奏,其节奏形式是2+3。而本人认为是三分节奏。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在这里讨论。读者可以参看拙作《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法结构与语言功能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不过,即便是把它看成是二分节奏,因为其基本形式是2+3,与《九歌》体改成的3+2式也有极大的不同,照样可以说明五言诗不是从楚辞体转化而来这一观点。
③ 参见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④ 参见廖序东《楚辞语法研究》,语言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