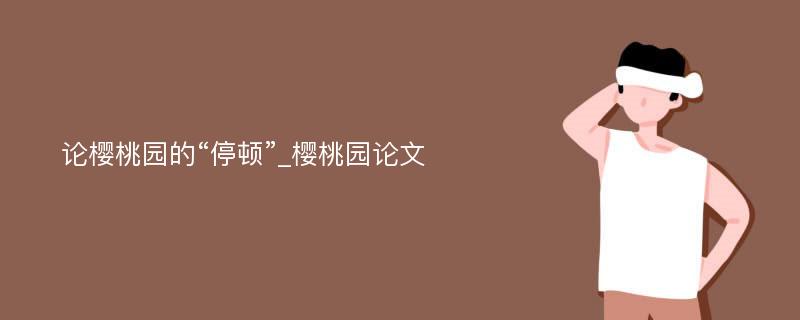
论《樱桃园》中的“停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停顿论文,樱桃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停顿”,作为戏剧内部的、心理的动作,作为对生活节奏敏锐、准确的标示,一直没有受到剧作家和理论家的足够的注意、研究和运用。
古希腊戏剧对生活的反映往往注重超越现实的想象,浪漫气氛浓烈,不可能达到现代人所谓的戏剧化,而只是戏剧的雏形。当时的生产力不发达,文化水平低下,生活节奏缓慢,人们的时空概念淡薄,很少注意一定的时空所蕴含着的深刻内容。虽然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戏剧反映生活的独特性质,但在当时的戏剧实践中,戏剧与生活的距离还是很大的。这就决定了当时不可能产生性格和人物心理的起伏跌宕的发展过程以及准确、细微的时空表现;不可能注意到生活中每一片刻的重要性。歌队合唱的形式也往往不具备展示人物内心的作用,而仅仅表示前后场的顺接或烘托气氛。索福克勒斯所作的努力是惊人的,他不仅成功地运用了戏剧中的“悬念”、“陡转”、“惊异”等手法,而且努力使戏剧在更高的意义上接近生活:“我所创造的人物,是写人们应该具有的那种样子”。[①]但他受时代的限制,没能摆脱理想化、浪漫化的倾向,也没能在戏剧中精当地记录生活的节奏。
戏剧发展到了文艺复兴及其稍后的时代,情况趋于两极:莎士比亚更加注意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却不强调表面的戏剧化;而高乃依等法国古典主义作家,过于看重“三一律”,使戏剧走向公式化甚至僵化,人为地达到所谓戏剧化。即使是莎士比亚,他对时空的敏感也不是用“停顿”这种说法,而是大量采用“独白”。最著名的如哈姆莱特的独白。第一次在戏剧理论上提出“停顿”这个概念的是18世纪中叶的狄德罗,他深刻阐述了“独白”与“停顿”的关系:“独白对剧情来说是一个停顿的时刻,而对人物来说则是一个混乱的时刻。即使剧本开场时的独白也是如此。如果说话的人心平气和,这就违反了真实,因为人们只在困恼的时候才会自言自语。如果独白太长,这就会伤害剧情的自然性,使它停顿得过久。”[②](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狄德罗所说的“停顿”还是狭义的,几乎等同于戏剧节奏或者时间上的“停止”。真正发现“停顿”的内涵和戏剧功用并进而加以丰富和运用的,是19世纪末俄国的戏剧革新家契诃夫。
狄德罗概括过舞台提示、表演说明的必要性:“当演员的动作姿态构成一个画面;当它使台词更有力或更清晰;使对白得以联系;使人物的性格突出,或当它非常微妙,难以猜度;……在以上各种场合,就必须把表演说明写下来。”[③]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契诃夫之前剧作家的广泛注意。与契诃夫同时代的易卜生结构主义倾向较重,他开始注意到压缩生活的一般节奏,并在剧中常用“过一会儿”来标出时空的间隔,不过这并没有和剧情充分融合,作为反映生活节奏的主要内容。
契诃夫天才地发现了生活节奏对提高戏剧真实性的作用;而真正理解了契诃夫这种发现的意义的,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两位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丹钦柯是把“契诃夫式停顿”的运用作为舞台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他认为这一点“是和契诃夫戏剧的本质相近的”[④]。他说:“停顿在艺术剧院的艺术成就上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愈接近生活,愈可以免除旧型剧场所特有的那种滑溜无阻的‘文学性的’流畅……要用属于生活本身的那种最深沉的停顿;要用停顿来表现一种刚刚经过的纷扰的结束,来表现一个正在来临的情绪的爆发,或者来暗示一种具有紧张力量的静默。”[⑤]这是对“停顿”内涵非常重要的开掘。
我国导演艺术家焦菊隐早在40年代就注意到契诃夫这一重要发现。后来,他又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停顿’是‘契诃夫的节奏’的最主要的律动……‘停顿’是现实生活本身的节奏,越能接近生活的,便越能理解:现实生活中最深沉有力的东西,便是‘停顿’。它既表现刚刚经验过的一种内心纷扰的完结,同时又表现一种正要降临的情绪的爆发,或者某种内心的期待。它又表现内心活动的最澎湃、最热烈、最紧张的刹那。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内在律动,都是要用停顿来表现的——这是一种最响亮的无声台词。所以,契诃夫的‘停顿’,不是沉默,不是空白,不是死了的心情,相反地,是内心生活中最复杂、最紧张的状态所必然产生的现象。”[⑥]焦菊隐甚至认为,如果把契诃夫剧本里像“停顿”这样的舞台说明删掉几个,“他的人物便会死去几个。”[⑦]我国一些戏剧理论著作中把“停顿”归于“戏剧动作”的范畴[⑧],并且注意到,“停顿是否具有戏剧性,正是取决于人物在这一瞬间心理活动的内容。”[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关于契诃夫的篇章还没有结束,人们还没有象应有的那样读完它,还没有深入领会它的实质,而是过早地把书阖上了。”[⑩]比如,对于《樱桃园》中三十三个“停顿”的出色运用,就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研究过。
不难发现,在剧的第三幕只有一个“停顿”,可它却成了这幕戏的戏眼和结构的重心。人物性格正是在“停顿”的前后鲜明地显示了出来。这个“停顿”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刹那。作者似乎想让女主人公朗涅夫斯卡娅真实地感到一点她从未严肃思考过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停顿”前作了四次情绪上的积累(她三次提到陆伯兴去拍卖为什么还没回来;当听说已经拍卖了樱桃园时,她又让人去打听买主是谁),好象她十分关心拍卖樱桃园的事,但她并没有意识到拍卖樱桃园是对她生活的一次彻底否定。她作的四次情绪积累几乎都是虚的,似乎刚刚摆脱了一点过去的生活,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却又不知不觉地滑向了庸俗。她好象是发自肺腑地说:“我爱这所房子;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也一齐卖了吧!”[(11)]可她马上又疼爱地嗔怪那位在巴黎吸着她最后一滴血的情人给她每天来电报,她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这种爱情:“我爱他,我爱他……这就象是我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石头,把我坠到水底下去了,可我还是爱我这块石头。没有这块石头我就活不了。”[(12)]在这前后的语言变化中,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从表面的悲壮、崇高滑向实质的庸俗、腐朽的。但她只能这样滑下去,她的生活基础本来就是鄙俗、腐朽的,虽然她想让自己扮演成一个悲剧人物,可她根本没有扮演悲剧角色的勇气,她根本不知道悲剧角色应体验什么情感。那么,当陆伯兴说出樱桃园是他买的之后产生这个“停顿”时,她是否体验到悲剧角色的情感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她之所以听了陆伯兴的话后心里一阵难受,以至于要不是扶住一把圈椅就会倒下去,倒不是因为她意识到过去生活的完结而感到绝望,而是由于买这片园子的是过去这里的老仆人的儿子,并且是竭力劝她卖园子的人。她并不关心,也不可能对园子留恋,她偶尔说几句对园子有感情的话,也不过表明自己还是一个有情感的“人”。至于谁买这个园子她更不在乎,她所关心的只是能早日完结这件老是妨碍她正常生活情绪的事情。可她万万想不到买园子的人曾经是爱过她的人。她只是感到一种惊讶,不能适应这新的环境和人物关系变化所造成的压抑气氛。她并没有由此对陆伯兴产生敌视和仇恨,她还不具有这么严肃、强烈的情感。哭了一阵后,她又愉快地给他和自己的养女瓦里雅做媒了(第四幕)。
这个“停顿”也为陆伯兴双重性格的展现作了准备。此时的陆伯兴不作任何说明,观众也能认清他的面目。可他却迫不及待地不愿停留在这个难堪的“停顿”中,他想把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拉出这由“停顿”所造成的死寂的、严酷的审视气氛,想为自己作一番辩解:“我请你们等一等,不要忙,我的头有点晕,我说不出话来……”[(13)]但他又始终压抑不住自己成功的快乐,“(笑)我们去拍卖场的时候……”[(14)]正因为他企图跳出这个可怕的“停顿”,他的全部性格才充分展现出来。一方面他带着对女主人公真挚的、人道主义的爱;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凶狠本性,当利益来到手边时就无情地伤害了自己曾爱过的人。冲破了“停顿”气氛的压迫,他感到自在了,完完全全成为他自己了,一面指挥着乐队庆贺自己成了园子的主人,一面又被女主人的眼泪所打动,流出眼泪来。如果他陷在“停顿”中,只能让人感到他兽性、野蛮的一面,而不能感到他人性、人道的一面。“停顿”的时空给他造成了充分展示自己性格的迫切感和可能性。
“停顿”不仅在“樱桃园”中成为结构的重心,也改变了剧中规定情景的生活节奏,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第二幕老仆人费尔斯非常自得地说:“……(笑)到解放农奴的时候,我已经升到听差头目了,那种自由,我没有愿意要,所以我 照旧还是侍候着老主人们。”这句话之后,出现了一个“停顿”。然后他又接着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伙都快活得不得了。可是为什么快活呢?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15)]这中间的“停顿”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老仆人是用满腔的热情让过去陈腐生活的回忆停留在现实生活的时空中,占有了一席现实生活宝贵的位置。扩充开来的旧生活的回忆,使人仿佛感到一股死尸的臭气突然隔绝了现实生活的正常气流(虽然樱桃园本身已经够陈腐的了),使人感到沉闷、阴暗、晦气。这个“停顿”是苍白的、无力的,但它却使现实生活的节奏中断了,出现了历史的回溯,在人们心中产生一种失落重心的感觉,“停顿”得越长,这种可怕的下坠感就越明显。虽然樱桃园里的人们是以过去时代的化石性人物生存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妨碍他们对刚刚逝去的农奴制时代的生活怀有很大的新鲜感,怀有一种对过去豪华的自足与对目前生活每况愈下的伤感。因此,他们不可能感到这个“停顿”所带来的空气的窒息,反而觉得飘来一股昔日苍白生活的香气。正是这种对过去有毒气息的不断吮吸,使他们永远不能再回到现实生活中,而成了未被埋葬掉的活尸。
契诃夫准确地抓住生活本来的节奏,使“停顿”所包含的重要意义的外延扩张,而又省略压缩了人们可以理解的不重要的思维过程,使剧作具有一种罗马人常说的“神秘的简炼”的特色,深化了剧作的思想,为人物展示丰富的内心活动提供了时空。戏的第四幕,在朗涅夫斯卡娅企图撮合陆伯兴与瓦里雅的婚姻而终于不成这一节戏里,作者一口气使用了七个“停顿”。女主人公就要离开樱桃园了,可她并没有感到内心的痛苦,“是啊,我的心思平静多了。”[(16)]她还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老仆人费尔斯的病;一是她的养女瓦里雅如何安排。在感叹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啊……”后,出现了一个“停顿”,然后她转向陆伯兴,“我老是希望着……希望能看见她嫁给你……”中间这个“停顿”不仅仅只起转折的作用,它还是一种思想角度的转移。在“啊……”后的省略号里,她重又勾起过去曾想到过的这一桩婚姻,她由对瓦里雅的爱怜到寄希望于养女和陆伯兴爱情、婚姻的实现这一情绪变化过程是在“停顿”的时空中完成的。她的这种情感转换是不深刻的、浅薄的,是随意唤起的一种意念。这与她对生活几乎是天真、愚昧和可笑的无知是一致的。因此,这个“停顿”的时间是短促的,没有力度的,几乎是不能察觉地喘了一口气。而当陆伯兴有意想回避这件事、用香槟酒岔开时,她却“精神抖擞”地布置了一个“约会”的环境,让大家全躲开,叫来了瓦里雅:“瓦里雅,把事情放下,到这来。来呀!”这时台上只剩下一个陆伯兴,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表,“嗯”了一声,紧接着出现第二个“停顿”。这时门外传来强压下去的笑声和咕噜噜的耳语声,最后,瓦里雅上来了。这第二个“停顿 ”,陆伯兴是想借以调整由于突然的事件所造成的内心失衡状态,但他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紧张,这毕竟不是恋爱,他不会爱瓦里雅,因为她不是他的事业的支持者,而是他将要破坏的旧的园地的维护者,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这里,他借助看表来表明自己所关注的是火车开车的时间,而不是注意她的到来。他想使这个“停顿”成为一种轻松自然的等待,可门外神秘的笑声和耳语声却又充斥了这个“停顿”。他企图排除“停顿”的时空中渗入的内容,一种自然的对外力的反作用又使他的内心紧张起来,一下子扩展了“停顿”的时空和紧张情绪的密度。正是在“停顿”处于极端饱和的状态下,瓦里雅上场了。
但一切都出人意外。她的行动从表面上看不像是冲着陆伯兴来的,倒好像是为上火车顺理成章地来检点行李,嘴里喃喃地说:“奇怪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啦……”这一行动的意外转换,一时也使陆伯兴的思维出现了真空,积蓄的紧张情绪不知投向什么目标了,有点莫名其妙地问瓦里雅:“你找什么?”她仍像是在延续着自己的行动线索:“是我自己打的行李,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这之后,出现了第三个“停顿”。乍看上去,这个“停顿”似乎不可理解,可正是在这个“停顿”里埋藏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向着陆伯兴热烈呼唤的心。我们可以从这个“停顿”中发现瓦里雅掩饰的外部动作与真实的内心意向的全部秘密。她是想借这个“停顿”给陆伯兴造成一个求婚的时空。但她并不愿表现出她是有意来听这种福音的,而是“偶然”在做着什么时,“偶然”听到了一个爱她的人向她求婚的声音。这比红着脸被女主人叫来听一个人的求婚要自然得多。可对于这种掩饰,她是准备并且希望被陆伯兴在这个“停顿”中揭穿的。但陆伯兴却以与她完全不同的缓慢、冷淡、随便的节奏使这个“停顿”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仿佛只能理解她的表面行动,仍然照她的行动线索往前延伸一步:“是在雅什涅沃吧?离这里大概有七十里的样子。”至此,他也感到必须按自己的行动线索走了,不然就被动了,必须“停顿”下来。
这第四个“停顿”是真正戏剧冲突性的“停顿”。双方都处在矛盾的中心,只是一方企图摆脱这矛盾的漩涡,而另一方则要把自己埋葬在这个“停顿”中。她真正感到了爱的波动,可这是没有对象的虚幻的反射;而他则真正开始寻求摆脱这一落陷的方式。“停顿”顿时成为双方情绪紧张压缩的符号,舞台节奏则趋于极端的外缓内紧状态。这种情绪的紧张所引起的内心矛盾的压缩都向外扩散着自己的影响和力,可力的方向却相反。一个渴求,一个却是摆脱。这就使“停顿”不是浓缩了情感,而是被矛盾的情感撕裂了。而这一切全部发生在情感的深处,表面仍是平静的。陆伯兴淡淡地似乎是毫无思索地说了一句:“这么说,这所房子里的生活就算是结束了……”可这句话里却包含了他在“停顿”中所找到的“爱完结了”的全部暗示,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爱的希望。这句话与上一句话毫无内在联系,中间被一个冷酷的“停顿”划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暗示瓦里雅感到了。可是她不愿表示自己曾经渴求过什么,虚荣心使她没有勇气那样做。她想继续她外部的虚饰的行动线索,查找着行李,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所暗示的是什么,仍接着一出场时的话说:“到底弄到哪儿去了呢?也许是我把它放在大箱子里去了?……”但这种虚饰的行动是和内心真实的情感相违背的,她不能再忍受这既来自内心又来自外部的痛苦的折磨,她几乎是绝望地接上陆伯兴的话:“是的,这里的生活,现在就算是结束了……不会再有了……”是否体会到她这话里的绝望、痛苦的情感,对于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所注意的是不给她创造这种爱的机会,尽量减弱这种爱的气氛。可她内心情感的线索仍没有断,仍被痛苦折磨着。当他谈到自己将坐离去、把家事交给叶比霍多夫时,她惊醒般地“噢”了一声。往下,他又生硬地大谈天气:“去年这个时候,已经下雪了。这你也许还记得。可是现在呢?你看,天气又晴朗,到处又都是太阳。只是稍许冷了一点……已经降到零下三度了。”她却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我没有寒暑表。”这产生了第五个“停顿”。可这个“停顿”几乎是一个空白。她甚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说出“我没有寒暑表”这句话,这不是她的心声。她说出口才明白这是与自己的心境毫无联系的,没有意义的。但她立刻又发觉这毫无意义的话也并非全无意义,它毕竟还与她当时的心理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这就使“停顿”中的空白得到了充实。她给这无意义的话中加进了意义深蕴的内容。“停顿”给了她充实这种意义的时间。在这一“停顿”后说出的话不是无意义,而是意味深长,饱含着全部的希望和暗示:“而且寒暑表也破了……”在这句双关语的后面又出现了第六个“停顿”。这个“停顿”不是对第四个“停顿”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强度上的加大。如果说第四个“停顿”并没有全部显现出陆伯兴“爱完结了”,对她没有任何希望的暗示,那么这第六个“停顿”反射地、乞求地显现出她的探询:“爱真的完结了?”她希望通过反射找到最后可能存在的爱的余烬。此时,双方的心思彼此都能察觉得出,排斥与期待的情绪上的分裂使二人都感到这个“停顿”的空间过于狭小。陆伯兴意欲冲出这个时空,但瓦里雅却没有力量再冲出这最后含有希望的时空了,她宁愿固守这个狭小的天地,自己忍受这种停滞的折磨。她害怕这个“停顿”的打破给她带来不幸。可她控制不住这个时空,倒不是陆伯兴要毫无人性地、残酷地冲出这个时空,而是另一个世界的呼唤打乱了他们内心高度紧张、表面却极端平静的氛围——院子里传来叫陆伯兴的声音。他好象早就盼望这一声叫了,仿佛要使自己相信已脱离了“停顿”似地大应一声:“我就来!”急急忙忙走了。瓦里雅终于感到一切都破灭了。她坐在地板上,把头伏在衣服包裹上轻声地啜泣。这时门开了,朗涅夫斯卡娅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轻声问瓦里雅:“怎么?”第七个“停顿”在这里出现了。而在“停顿”之后却是这么一句话:“那,就走吧!”[(17)]这前后两句话是不连贯的。“停顿”省略压缩了由第一句话到第二句话的逻辑联系的全过程,女主人公完成了由猜测到明白、由明白到失望、最后转向连贯全幕的总的行动线——到火车站去的思维曲线。这个“停顿”实际上是运动着的,它贯穿于人的思维线路。这正是生活中最普遍的一种思维节奏,它使生活紧凑、简捷,但决不紊乱。
通过“停顿”来揭示人物性格,放大人物内心活动,沟通与观众的联系,为观众提供思考的时空,这也是“契诃夫式停顿”的重要内容。第二幕一开始,家庭教师夏洛蒂内心独白似地叙说了自己如何不幸后,有一个“停顿”,然后又说:“我真恨不得找谁把这个心思说一说呀,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谈谈的……我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啊。”[(18)]这后面的话实际就是她在“停顿”中思索的全部内容。这是“停顿”内涵的外化。她没有父母,叙说自己的身世没人理解和同情,她只能在心中自我叙述。她听不到外界任何共鸣,只能静听内心的回声。假如有人听她的叙说,同情她,那么这个“停顿”所包含的“孤独的、荒唐的、不为人所需要的寄食者”[(19)]的自我戏谑、苦笑的情绪就不存在了,而是被一种深沉、痛苦,但又有某种欣慰的情感所代替了,“停顿”之后将会听到人们的叹息声或宽慰话。可这里的“停顿”内容又是她把要说的话再想一遍,然后再说一遍。如果不说出来,而把这种内心的朦胧、麻木和虚幻留在意识底层,这个“停顿”固然也是丰富的、有深度的,但观众对这个人物的前源后世都不了解,那就不能感受到这个“停顿”的份量了。
仍是第二幕。管家叶比霍多夫对自己带着某种嬉弄的、荒诞不经的态度谈着命运。说早上起来胸口上趴着一只大得出奇的蜘蛛;又无聊地谈到喝一口克瓦斯,就准发现里边有点什么恶心的东西,比如蟑螂什么的。[(20)]说到这里,有一个“停顿”。但这个“停顿”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对他都毫无意义,只能是一个“空白”的时空。他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负载着痛苦、忧郁,只关心自己,谈任何事情都从自我出发,只生活在自己的心中,带着“反观内省”的心理、哲学议论的癖好、琐细无聊的不幸和哈姆莱特精神,厌恶尘世,没有什么能吸引他们去奋斗一番。他们只在自己的内心小天地中生活,即使偶尔作某种表达,也是奇特的“个性化”的,别人无法理解。当他们不探出头来关心人世时,人们也就遗忘了他们。他们的话不产生任何共鸣,没有情感的流动,也不关心别人是否注意他们的一切。但这里的“停顿”所表示的空白,并非是作家的疏忽,而是使这个“停顿”具有了双重意义。对管家来说,这个“停顿”是空白的、不属于他的、毫无意义的;而对于观众来说,这个“停顿”为他们提供了认识人物性格的时空,即由19世纪末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忧郁、苦闷基调所派生出来的人物性格。这个“停顿”的内容被观众充实了。“停顿”在这里只提供给观众,而不属于舞台人物的节奏。舞台上的人物重新获得自己的节奏是在这处“停顿”之后的另一个“停顿”中。管家从内心深处微微探出头来,淡漠地问杜尼亚莎:“你读过勃库尔的书吗?”“停顿”出现了。管家在搬弄他自己根本不懂、不过想说明自己有学问的勃库尔的书后,感到人们都没注意他的存在,于是说了一句能引起人们注意的话,表示自己尚存在于世:“杜尼亚莎,我可以麻烦你一下吗?只说两句话!”[(21)]上面这个“停顿”是充实的,他想和人们结成一种联系,暗合着只有当他关心人生的时候人们才会注意他的存在的逻辑过程。他积极地使这个“停顿”有了内容,这就结束了前一个“停顿”——在他只算一个毫无意义的“空白”的情境。
“停顿”所表现出的“契诃夫的幻想”和永恒美也是令人振奋和神往的。契诃夫是“依靠恰恰明朗的幻想和对未来的信念而生活的”[(22)]。他是首先感觉到必须清算旧生活、砍掉表面美丽而实质腐朽的樱桃园继而重新建起俄罗斯大花园的那一批人中的一个。他有无数的幻想,这种热烈的、美好的幻想实际上是一种对美好生活必然到来的预感,这在那昏暗、窒息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俄罗斯,像一道闪电一样,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必须把这种幻想“浮雕般地凸出”在舞台上[(23)]。第二幕中当特罗费莫夫热烈地呼唤着新生活时,安尼雅拍着手说:“你的话说得多么美呀!”出现一个“停顿”。然后接着说:“今天这儿叫人觉得多么舒服呀!”这个“停顿”中充满了幻想,安尼雅真正像浮雕一样站在那里,如同站在一个新世纪的起点上,那种热烈的、明快的、向往的情调和作者同期写的小说《新娘》完全一致。你能说这种幻想不是一种永恒?这“停顿”的刹那不是象征着永恒?“这一切都属于永恒的领域,不能不怀着激动之情来对待它。”[(24)]这个“停顿”的瞬间给人带来永恒的快感,它所包含的全部实在、美好的意义,甚至不是这个剧本的时空所能容纳、负载的。未来的美是一种接近永恒的全新画面。人类所寻求的最终极的美都实现在永恒中。它的无限延伸,给仍生活在腐败花园中的人们带来无比的快乐和热烈的向往。但这里只有安尼雅能最深切地感受到,她的存在使全剧中唯一的永恒美的星辰降落在一瞬间的“停顿”中,给全剧的抒情气氛又增抹一笔浓重的色彩。而樱桃园中的另外一群人正是一批不用自己的劳动去接近永恒的人,他们离开接近永恒的人群太远了,永恒只给了他们瞬间存在的意义,加速了他们的消亡。由他们造成的“停顿”这一瞬间都失去了永恒的意义。他们没有任何行动能在这永恒的、广阔的背景上出现。只有用劳动不断寻求生活意义的人,才会使永恒的一瞬加长、延缓、扩大生命的存在时空,在永恒的背景上使瞬间更接近永恒。这正是契诃夫戏剧中用抒情笔调给我们展现的未来一瞬间永恒的、崭新的画面;只有在安尼雅的行动中才能看到这一瞬间全部深刻意义的端倪。
“停顿”的意义各不相同,但都是生活节奏的最基本符号。“停顿”中充满了悲伤和欢乐,绝望和期待;它有时达到喜剧的效果,有时达到悲剧的效果。契诃夫试图准确地记录这种符号,他精确、深入地确定了每个“停顿”前后的语言环境,创造了使每个“停顿”实际存在的特定时空气氛,使“停顿”的内涵丰富多样。这是创造性地、大胆地对生活节奏准确记录的典范,充分表明了作者对细微、深刻的生活节奏的敏感和透视力。
“契诃夫式停顿”与《樱桃园》的抒情风格紧紧融合在一起。抒情风格使《樱桃园》能够在一部现实主义剧作中融进大量的象征、隐喻成分。这部戏剧的总体构思就是一种象征、隐喻。“樱桃园”所象征的正是旧时代乐园的衰败;隐喻着一个旧时代最后的一次叹息。“契诃夫式停顿”把揭示象征、隐喻内涵的时空标示出来。全剧每一句台词所潜藏的象征、隐喻内涵是通过生活本来的真实节奏暗暗向人们揭示的;而不断出现的“停顿”就象省略号一样,给人们一个回味的机会,使剧中的情感潜流形成一个个意味深长的蓄池,不让这种潜流过分激荡而一泻无余,只给人留下冲洗过的印象。
舞台上一片寂静。忽然间,仿佛从天边传来一种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然后忧郁、缥缈地消逝了。台上的每个人都注意到这声音。朗涅夫斯卡娅发抖地说:“这声音可有点怕人!”[(25)](第二幕)之后出现了一个“停顿”。这个“停顿”给了象征、隐喻的潜流一个丰富的时空。女主人公并没有意识到这断弦声和自己说的这句话预示了什么。她只生活在很浅显的生活表面,还不能理解自己活着究竟为什么,她也不可能悟出任何征兆,不可能预感到什么。但这个“停顿”却把作者所要告诉人们的象征、隐喻内含凸现了出来,引起了观众的深深思索。观众明白了不知道怎样严肃生活的女主公所不能理解的这句话的另一层含意。它本身体现了对旧时代逝去的畏怯,旧时代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所有这些不知严肃生活的人的心。他们没有对于时代变迁的敏感,他们并不重视自己对这个社会应负多大责任。他们在无意中给自己、给已逝去的社会敲响了丧钟,可他们自己却听不见。他们并没有感到旧时代的逝去对他们的生活追求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毁灭,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追求。他们自己给自己拖着挽联,却并没有感到它的沉重。死亡在他们心中没有产生悲剧的感觉。这正是他们不是悲剧的悲剧所在。女主人公这句话具有双重含意。表面上好象是她带有某种真实的感受,而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话;本质上作者把深刻、隐蔽的象征、隐喻潜藏在每一个字的后面,借助一个“停顿”,让观众隐隐回味到这一点。这个“停顿”对女主人公来说虽是空泛的、毫无意义的,但却给老仆人费尔斯一个深刻思索、回忆的机会:“在那次大灾难发生以前,也正是这个样子;猫头鹰也叫了,铜茶炉也不住地咕噜咕噜响。”这时嘎耶夫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在什么大灾难以前啊?”之后又是一个“停顿”。这个“停顿”是由老仆人造成的,可它的深刻性却只反映在安尼雅身上,而对女主人公来说则是多余的、不舒服的沉闷。她不理解为什么安尼雅会在这深刻的“停顿”中哭了;她也不理解一个时代的完结与她个人有什么联系。这个“停顿”使她后面毫无情绪变化的行动更引人注目。她让大家回去,只是因为“天快黑了”;她拥抱安尼雅,却呆滞地发问:“你怎么啦,我的孩子?”[(26)]去掉这个“停顿”,女主人公的麻木、毫无意义的存在就难以表现。
“停顿”在《樱桃园》中的突出运用是与契诃夫所坚持的戏剧美学原则相一致的。契诃夫指责过去的“戏剧的形式是装腔作势、吵闹不休、厚颜无礼、使人厌倦的情妇。”[(27)]他认为:“在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倒不是因为作家需要这样写,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本来就是这样。”[(28)]按照契诃夫的理解,戏剧矛盾和冲突不应表现在它的外部,而应是“全部含意和全部戏都在人的内部。”[(29)]依照这一美学原则,“停顿”作为生活中最深沉有力的节奏,必然应成为戏剧的最基本的节奏。这种节奏对于戏剧冲突的内心世界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时空,使戏剧有了一种庄严、宏伟的气氛和简炼、震憾人心的风格,改变了人为加快生活节奏给戏剧带来的虚假,使戏剧更接近于契诃夫所理解的最普通人的生活。
“停顿”与契诃夫戏剧美学原则的一致,除了表现为“非戏剧化”外,还表现于契诃夫对戏剧人物的选择。他不像屠格涅夫那样,仍站在贵族的立场上,选择贵族中间的优秀分子来证明他的主题:如果奶油不好,那还谈什么牛奶呢?契诃夫选择的人物是一些不凶恶的、对现实“毫无害处”的、滑稽而且好心肠的、不愿意也不会使人遭到痛苦的人物,这是契诃夫选择戏剧人物的美学准绳。这些入选的人物过着腐朽、堕落、毫无目的和生气、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的行动节奏缓慢,但猛然间又会急促起来,毫无规律性,但又以缓慢、趋于停滞为其主旋律。这正是契诃夫明确点明三十三个“停顿”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停顿”并非全是由朗涅夫斯卡娅和嘎耶夫之类的人物造成的。但由于他们处在行动的中心,必然波及周围人物的行动节奏,在不同人物身后留下的节奏就具有各自的内容和时空。但总的趋向又是一致的,即都是樱桃园这个总环境里的生活节奏的变奏,只是在程度上的扩大或缩小,人物行动的总节奏的趋势是缓慢的、逐渐趋向停滞的、毫无意义的。
“停顿”成为契诃夫戏剧的重要内容,它贯穿在他的全部戏剧创作中,这与契诃夫不断对新的戏剧形式的探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契诃夫在《海鸥》第一幕里,通过特里勃列夫之口说:“现代戏剧什么也不是,不过尽是些传统的因袭罢啦。幕升上去了,在人造的灯光底下,一间三面围墙的屋子里,于是就有这班伟大的天才们,献身于神圣艺术的脚色们跑了出来,表演着人们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爱、怎么走路、怎么穿衣服;他们从那些平凡庸俗的句子和场面中,努力想抽出一些平凡庸俗的教训来,一些易于理解而又便于日常应用的琐屑的道理;无论怎么千变万化,总之是不离其宗……”[(30)]但契诃夫又并不是这样琐屑地描写生活,即使在他的《醋栗》那样的小说中,你也能从中感到作者深刻的思想倾向,感到他带着强烈的讽喻、指责或含着痛惜的眼泪。这是对尚存的旧时代活尸的掩埋。不是欣赏旧时代的陈腐,哀怨它的丧失,而仿佛是准确、深刻地选择在新时代尚存的旧时代的故事,带着强烈的情感叙述它,使观众感到这种旧时代的存在是可悲的、令人窒息的,是需要改变的。这种在观众心理上唤起的热烈愿望正是作者所表达的抒情的效果。不断的“停顿”,使这种效果有了深刻的节奏。该逝去的时代的节奏越来越混乱、微弱,而已经存在的新时代的节奏越来越齐整、强烈。契诃夫之前的剧作家谁也没有意识到记录这种生活节奏有多么重要,而契诃夫却充分展示出这节奏符号中时代变迁的最深刻内涵。任何时代都有自己最微 妙的节奏,作家的深刻、伟大,正在于能敏感、准确地捕捉这崭新的节奏。
注释:
① 《外国剧作选》(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②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68页。
③ 狄德罗《论戏剧艺术》,载《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第145页。
④ ⑤ 丹钦柯《文艺·戏剧·生活》,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⑥ 《契诃夫戏剧选》译后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423页。
⑦ 见《戏剧艺术》1980年第3期,第134页。
⑧ 顾仲彝《编剧理论与技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⑨ 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⑩ (22) (23) (2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史敏徒译,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第327、372、373、261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5) (26) 《外国戏剧选》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6、347、355、355、329、364、367—370、320、321、321、333、333—334页。
(19) 叶尔米洛夫《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张守慎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60页。
(27) (29) 见《电影艺术》1981年第5期,第59、59页。
(28) 《俄国文学史》下卷,布罗茨基主编,塞昌宁诺夫、赖亭、斯特拉舍夫合著,蒋路、刘辽逸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1191页。
(30) 契诃夫《海鸥》,见《契诃夫戏剧集》,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