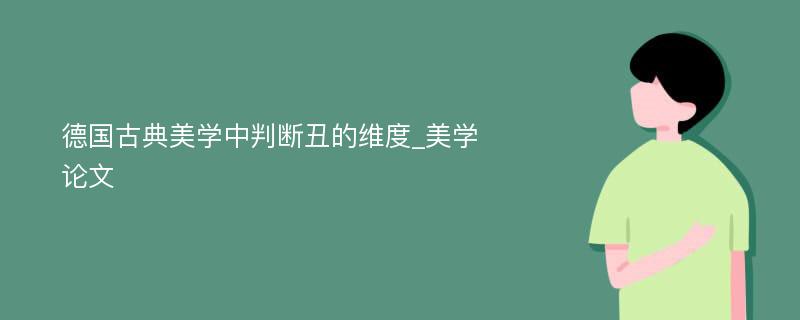
德国古典美学的审丑之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美学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5-0019-11 1750年,鲍姆加登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美学》,由此开创了一门学科。按照鲍姆加登的定义,“美学”是“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①。作为“感性认识”,它包含“美”和“丑”两个方面,“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据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②。“丑”由此在美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鲍姆加登在此名下研究的只是“由自然和人工作品引发的美和崇高的情感以及对诸如此类情感的判断原则”③。至于“丑”则付之阙如。然而,这块领域却受到了后来者极大的关注。在随后德国古典美学宏大的“审美”叙事中,“审丑”理论不断发展,并于罗森克兰兹《丑的美学》达到顶峰。只不过,这一进程至今仍鲜有学者关注。 一、门德尔松:“混合的情感” 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审丑问题主要体现为“艺术丑的问题”,而门德尔松则是第一位深入研究艺术丑并建立了系统理论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特意提到了门德尔松:“艺术应该引起怎样的情感?害怕还是怜悯?但这些感情又怎么能是宜人的呢?对不幸的处理又怎么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情感?这些问题在摩西·门德尔松的时代特别流行,在他的作品中能找到许多相关的讨论。”④ 1755年,门德尔松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论情感》(On Sentiments),采用书信对话体,深入探讨了艺术丑的问题。门德尔松首先由鲍姆加登的“完善”出发,将完善分为两种:一是感性的完善,也就是美,这是基于杂多的统一基础上的“轻松的享受”,“杂多特征的同一、统一是美的对象物的特性。它们必须展现出某种秩序或者说完善,能够诉诸感觉,而且做得毫不费力。如果我们想感知一种美,那么我们的灵魂希望是一种轻松的享受。”⑤二是智力的完善,是基于“灵魂的积极的力量”直觉到的“真正完善的知识”,“一种愉悦——源自智力努力获取的相互支撑的表象而非你的不足”。⑥在门德尔松看来,智力完善的愉悦要远高于感性完善的愉悦,前者是“地上的维纳斯”,后者是“天上的维纳斯”。鲍姆加登对“感性的完善”作了深入的阐述,而对“智力的完善”虽有涉及但并没有展开,却正好成了门德尔松艺术丑理论的出发点。那么,这“天上的维纳斯”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美? 门德尔松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悬崖突出在河上,摇摇欲坠,边沿石块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掉进万丈深渊,让人不敢直视,然而,迅速定下心神之后,我们重新直视这个可怕的对象物,可怕的景象已令人愉悦。“这种特殊的满意从何而来?”⑦其二,在一幅绘画中,一艘船在同波浪作了长时间的搏斗后正在下沉,满怀热情的水手仍在用尽最后的力气挽救它。白色的浪花劈头盖脸,他们互相激励,不屈不挠。但一切都是枉然!风暴掀起滔天巨浪,带来了死亡。目睹同伴的死亡,他们脸色惨白,不起作用的船舵从无力的手中落下。这种景象是悲惨的,但这幅画却令人觉得美,而且危险越是被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观众越会认可这幅画,“它已经不再是美丽的自然,不,它是恐怖的、可怕的自然。你发现可以欣赏它?难道不应该说,面对回忆中的惨像,人类非但不会沮丧,反而热衷于此类不幸的事件?”⑧在这两个例子中,对象物都带给人愉悦,但显然不是“轻松的享受”,而需要智力的完善。 门德尔松进而追问:这种愉悦何以可能?换句话说,自然中引起反感的事物,在模仿中何以会产生快感?显然,这是个古老的美学问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曾给出了两个经典的理由:一是源自人类求知的本性,因为模仿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最基本的形式;二是出于对画家高超技艺的欣赏。⑨门德尔松对第一点不置可否,但对第二点显然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艺术技巧远没有那么大的功用,“无可争议的是”,门德尔松写道,“描绘一艘全力行驶的船同描绘一艘即将沉没的船,需要同样多的技巧”。因此,艺术技巧无法解释这幅沉船画作的独特魅力。门德尔松自己的答案是“同情”,“在那些命运多舛的事件中,令我们愉悦的源泉唯有同情(sympathy)”⑩。何谓“同情”?这是一种“混合了愉悦和不快的情感”,以其“积极的特征”区别于其他感情形式,“是一种对混合着不幸概念的对象的爱”,更是人的本性,“这就是我们情感的本性。一点痛苦,混合到甜蜜的快乐中,会增加愉悦,使甜蜜加倍。当然,只有在混合在一起的两种情感不会直接对立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才会发生”(11)。同情本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最习以为常的感情之一,门德尔松却从中发掘出了独特的内涵:首先,它是愉悦和不快的混合;其次,它表现为积极的爱的情感;第三,两种对立情感的适度混合增加了愉悦。正是同情使得人们对一幅描绘悲惨沉船事件的绘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由“同情”门德尔松最终发展出了内涵更为丰富的美学范畴“混合情感”(mixed sentiments)。 在《论情感》发表6年后,门德尔松意犹未尽,写下《论情感书简增补或随想》(Rhapsody or Addition to the Letters on Sentiments,1761),深入讨论了“混合情感”,他写道:“悲伤的场景怎么可能又是令人非常愉悦的对象?……客观的不完善唤起的绝非是纯粹的不满,而是一种混合的情感。从客体及(表象)同其关系来看,由于直觉到客体的缺陷,我们所感受到的的确是不满和反感。但是从心灵投射的角度来看,灵魂的认知和欲求力量参与其中,也即是说它的现实性得到了提升,而这必定导致愉悦和满意。”(12)由此可见“混合情感”属于“智力的完善”。“混合情感”至少有以下五个特征:(1)效果因人而异,粗鲁的人较之有教养的人就更容易获得愉悦,“粗鲁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同情别人,所以能够从同类的受难和惨状中获得愉悦”(13)。(2)客体和表象反映不同情感,“不完善、邪恶和缺陷总是唤起一种混合的情感,它由对客体的不满意和对客体的表象的满意组成”(14)。(3)主客体之间距离是关键,主体、客体和表象构成了事实上的三角关系,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表象的效果,“如果客体同我们关系密切,如果我们视其为自身的一部分或者干脆等同于我们自身,表象的愉悦性特征就会完全消失,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立刻就变成了同我们之间的不愉快的关系,因为这里主客体的界限消失并合而为一了。于是,表象不再让人愉悦,而只是令人痛苦”(15)。(4)艺术品是摹品,可以有效地保持距离,带来愉悦感,“让柔弱的心灵对最可怕的事件产生愉悦的另一种方法是艺术的模仿,即在舞台上、画布上以及运用大理石的模仿,因为内心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模仿品,意识到我们看到的并非真正的实物,就会缓减对客体的恶心感,而且正如艺术品所实现的,它从主体方面提升了表象”(16)。(5)混合情感比单纯的情感更吸引人,“混合情感具有特殊的品性,它当然不像纯粹的愉悦那样柔和,而是会更深入心灵,产生更持久的影响。单纯的愉悦很快就会令人餍足,终至令人生厌。我们的欲求总是会超过我们的享乐,如果得不到完全的满足,心灵就会渴求改变。相反,不快的感觉混合着愉悦能够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防止我们过早产生腻味情绪”(17)。 门德尔松进而把他的“混合的情感”理论应用于崇高研究。在门德尔松看来,当人们面对一个巨大的对象物时,会努力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但又不可能完全理解,这时就会唤起混合情感,它包括满意及其对立面,一开始会引起恐惧战栗的感觉,而如果继续沉思它,就会产生一种快乐的眩晕感。《论情感》开篇提到的河上的危岩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情感就是由满意及其对立面混合而成。对象物的巨大让我们满意,但是无法完全理解又在满意中加入了某种程度的苦痛,从而令这种感情更具诱惑力。”(18)同样,不可度量的大海、广袤无边的草原、不可胜数的繁星、时间的永恒、每一个不可穷尽的高度和深度、伟大的天才、令我们敬畏却又无法达到的崇高的品行,等等都能产生这种混合情感。门德尔松把这种“完善的力量”正式“命名为崇高”,“有空间的巨大……就有力量的或非延展的巨大,同前者具有相似的效果……完善的力量被命名为‘崇高’,总的来看,人们可以说:就其完善的程度而言,每样巨大的或表现为巨大的事物都可称之为崇高”(19)。崇高显然不是美,因为它不可能是感性的完善,“如果对象物不能在同一时间里被全部感知到,那么它就不再是感性的美的事物,而成为在空间上庞大的存在。它唤起的情感就具有混合的特性”(20)。巨大的对象物如何达到智力的完善?如何实现统一和谐?门德尔松提出了“想象”,“由崇高产生的情感是合成体……巨大唤起一种甜蜜的战栗,并迅速传遍我们的每一根神经,同时杂多阻止了所有的餍足,让想象插上了翅膀,不断深入,势不可挡。所有这些情感都在灵魂中合在一起,互相涌流,汇成单一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敬畏(awe)”(21)。 门德尔松的“混合情感论”和同一时期英国美学家埃德蒙·博克在论述崇高时提出的“痛苦和快乐相伴说”颇多相似之处,但远比后者系统、深刻,影响也更大。康德的崇高理论明显受到门德尔松的影响,而门德尔松的“亲密朋友”莱辛更是在其著名的《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中直接引证门德尔松的艺术丑理论来解决核心问题。 二、莱辛:“拉奥孔的痛苦” 18世纪中后期,德国学术界就著名的古希腊雕像《拉奥孔》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论争,温克尔曼、莱辛、施莱格尔等都对该雕像独特的表情“拉奥孔的痛苦”给予了经典的阐释。在这场争论中艺术丑问题得到了集中的关注,审丑理论也有了极大的丰富。 关于拉奥孔雕像(22)的讨论始于“德国古典主义之父”温克尔曼。1755年,温克尔曼发表长文《论古希腊雕刻和绘画的模仿》(On the Imitation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 of the Greeks),他以拉奥孔雕像为典范,对古希腊艺术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古希腊作品终极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姿态、表情上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海面波涛汹涌,海底静止不动,希腊人所造的形体正与此相似,不论情感怎样激荡,内在的伟大心灵始终平静。”又说,“在最剧烈的苦痛中,在拉奥孔的脸上——当然不只限于此——伟大的心灵闪耀着全部的光彩。剧痛刺进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连我们几乎都能感觉得到,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不是脸部,或其他最富于表现的部分——只有腹部因极端的疼痛出现了收缩。然而,我得说,不论是在脸上还是在姿态上,都没有激烈的反应。他并没有像维吉尔的拉奥孔那样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毋宁说他张嘴发出了一声焦躁、沉重的呻吟”(23)。在温克尔曼看来,拉奥孔雕像充分体现了古典作品的特征:一方面,拉奥孔的痛苦通过一些简单的形体特征(如略微扭曲的鼻子、暗淡的眼神等)被生动地表现出来,震撼人心,甚至令人为之痛苦哭泣;另一方面,身体的苦痛并没有淹没对拉奥孔心灵的表现,相反,在对巨大苦痛的忍受中,拉奥孔伟大的心灵像太阳一样,散发出“平静的美”,其光芒漫溢过激情,其表情“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自然力量”。“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遂成为评价古典艺术最为经典的名言。然而,如何理解“拉奥孔的痛苦”?这种表情显然同古典雕塑的艺术原则有些冲突,温克尔曼似乎视之为伟大心灵的反衬,但缺少说服力,艺术批评家莱辛就有不同的看法。 1766年,莱辛出版了“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的纪念坊”(朱光潜语)式的著作《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这部作品可以说完全针对温克尔曼关于拉奥孔的观点而作。莱辛赞同温克尔曼对雕像中拉奥孔表情的描述,即拉奥孔没有哀嚎。但拉奥孔为什么没有哀嚎?温克尔曼认为是出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古典美理念。莱辛则持不同意见。从莱辛关于《拉奥孔》的遗稿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真正的理由是美的规律”(24),它决定了古希腊雕刻家不可以在雕塑中表现丑,“雕刻家要在既定的身体苦痛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最高度的美。身体苦痛的情况之下的激烈的形体扭曲和最高度的美是不相容的。所以他不得不把身体苦痛冲淡,把哀嚎化为轻微的叹息。这并非因为哀号就显出心灵不高贵,而是因为哀号会使面孔扭曲,令人恶心”(25)。但为什么拉奥孔在维吉尔的诗歌中可以哀嚎?莱辛由此出发,用大量的篇幅“论画与诗的界限”,结论是诗是时间的艺术,画是空间的艺术,“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26)。由于在时间的承续中丑感被冲淡了,所以诗可以表现丑的东西,“在诗里形体的丑由于把在空间中并列的部分转化为在时间中承续的部分,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它不愉快的效果,因此仿佛也就失其为丑了,所以它可以和其他形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去产生一种新的特殊的效果。在绘画里情形却不如此,丑的一切力量会同时发挥出来,它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比在自然里弱多少”(27)。莱辛进而指出,艺术的领域在现代得到了扩大,所以丑自然应该被纳入进来,他引用“人们”的观点写道:“艺术在近代占领了远较宽广的领域。人们说,艺术模仿要扩充到全部可以眼见的自然界,其中美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真实与表情应该是艺术的首要的法律……如果通过真实与表情,能把自然中最丑的东西转化为一种艺术美,那就够了。”(28)这样,莱辛就把丑引入了艺术领域,这至少对温克尔曼这样的古典美学家来说还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如何理解《荷马史诗》中唯一丑的形象特尔什提斯?莱辛运用门德尔松的“混合情感论”首先指出,特尔什提斯是嫌厌的对象,是“极端的丑”,“这种丑看起来不顺眼,违反我们对秩序与和谐的爱好,所以不管我们看到这种丑时它所属的对象是否实在,它都会引起厌恶”(29)。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丑被利用来生成某种“混合的情感”,以提供娱乐,而且丑还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莱辛写道:“荷马使特尔什提斯显得丑,为的是使他显得可笑。但是他之所以可笑,也不单是因为丑;因为丑是不完美,要显得可笑,就须有完美和不完美来对比或反衬……但是尽管特尔什提斯不能单因为丑就显得可笑,他要显得可笑,却也不能不显得丑。他的丑以及这种丑和他的性格的协调,这两个因素和他的妄自尊大之间的矛盾,他的恶意的闲言蜚语只给自己丢脸而却无害——这一切必须结合在一起,才会使他显得可笑。”(30)特尔什提斯形体虽然是极端的丑,但综合其他要素所表现出来的整体形象却是可笑的,能提供娱乐,带来快感。这样,莱辛就不仅解决了丑如何进入诗歌的问题,还深入分析了“滑稽”这个喜剧范畴——丑被界定为必要的因素。莱辛进而区分了“无害的丑”和“有害的丑”。像特尔什提斯这样只是靠耍嘴皮并不能造成真正伤害的就是无害的丑,而像能够抓破腮帮的长指甲那样的丑则是有害的丑,前者是可笑的,后者是恐怖的,两者都可以进入艺术,“通过模仿,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吸引力和快感”,只是都不宜过度,“无害的丑不能长久地停留在可笑上面,不愉快的情感就会逐渐占上风,原来第一眼看去是滑稽可笑的东西,后来就只惹人嫌厌了。有害的丑也是如此,可恐怖性逐渐消失,剩下来的就只有丑陋,不可改变地留在那里”(31)。莱辛关于“嫌恶”“滑稽”以及“有害的丑和无害的丑”的区分,都极具启发性,《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堪称审丑理论的经典著作。 莱辛的理论却引起了当时年轻的文学批评家、“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领袖赫尔德尔的激烈反驳。1769年,赫尔德尔发表长文《批评论丛,或关于美的艺术和科学的反思》(Critical Forests,or Reflection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循着莱辛的路数”对《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中的观点逐一反驳。赫尔德尔首先指出,莱辛把诗定义为“时间的艺术”,视“先后承续”为其主要特征,是毫无道理的。在他看来,诗歌固然表现出了连续性,但首先,这只是声音上的连续性,它既不是天然的,对诗歌的效果也不是主要的;其次,连续性是所有语言的特征,并非诗歌所特有,“对定义或区别诗歌的本质几乎没有什么帮助”(32)。之后,赫尔德尔重点讨论了特尔什提斯的例子。赫尔德尔同意莱辛的看法,即特尔什提斯是形体丑的极致,但激烈反对莱辛的“滑稽可笑说”,“特尔什提斯的主要特征不是滑稽而是丑陋,他不是一个可笑的同伴而是一个邪恶的、乱喊乱叫的家伙,是集结在特洛伊之前所有人中灵魂最阴暗的人”(33)。赫尔德尔认为,荷马的确有意把特尔什提斯的丑表现无害,但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缓和他的绝对的丑和绝对的卑劣,而不是其他的目的”(34)。赫尔德尔同样反对莱辛把可笑同丑陋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并非所有可笑的事物都是丑的。在完善和不完善之间大量无害的事物中,还有可称之为‘丑陋的美’的事物……同理,并非所有恐怖的东西都必然是丑的。”至于恐怖和丑陋,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35)。几乎在所有观点上,赫尔德尔的看法都和莱辛针锋相对。不过,客观地说,他关于特尔什提斯的丑陋、可笑与滑稽、嫌恶与恐怖等的解释显然还不足以否定莱辛的看法。但不可否认,他以“或然性”对诸多艺术丑概念之间关系的解释、特别是“丑陋的美”的提法都拓展了艺术丑问题的论域。 三、施莱格尔:“留在灵魂中的刺” 对于德国文学批评家施莱格尔来说,艺术丑问题的提出有个大的背景,那就是横跨17、18世纪遍及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古今之争”。德国诗歌领域的“古今之争”集中体现于两部几乎同期完成的长篇诗论:席勒的《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On the Nai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1795-1796)和F.施莱格尔的《古希腊诗歌研究》(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1797)。 席勒在《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创造性地把诗歌分成了天真的和感伤的两类。按照席勒的说法,“天真”是诗歌的最高境界。自然是纯真的,“每个真正的天才必然是天真的”,天真的诗就是天才按照自然法则自然而然创作出来的诗歌,“它不按照已知的原则,而是按照突发的念头和感觉行事;可是它突发的念头是神的启示(凡健康的自然之所为均为神授),它的感觉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万古不易的法则”(36)。而感伤的诗则刚好相反,是不可挽回地失去自然后眷恋之情的表达,“我们眷念自然的感情如此近似我们悲叹逝去的童年和天真岁月的感情”(37)。“随着自然作为经验、作为(行动的、感受的)主体逐渐开始从人类生活中消失,我们也目睹它在诗人世界里作为观念和主题缓缓升起。”(38)按照席勒的观点,“古代的和现代的”分别对应着“天真的和伤感的”。显然,这种划分带有古今之争的鲜明烙印,且倾向性明显,“在德国,古今之争体现在席勒《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之中。当席勒把古典奉为典范时,他的讨论建立在古典和现代截然二分的基础上。现代被一系列独特的条件所限制,它不再能够简单地模仿自然,因为已经进入了自我反省的哲学新时代”(39)。尽管席勒坚持认为两类诗之间根本就不应该比较,但客观上的比较却贯穿了整部著作,而且现代诗明显被置于低一层次的位置。从美学上来说,现代诗的效果是“讽刺的”或“哀伤的”,虽说仍然是美的艺术,但同“天真的”古代诗歌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倾向在施莱格尔那儿更加明显,而现代诗歌也堕落成了赤裸裸的“丑陋”。 施莱格尔是公认的现代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但同时他也是古典主义的狂热爱好者,“人们总是很惊奇地发现,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人们普遍认为,作为欧洲浪漫主义最早的践行者,他不仅处在最前沿,而且还是最积极地建构浪漫主义美学的人——是古典主义的狂热爱好者”(40)。施莱格尔深受温克尔曼影响。温克尔曼通过对古代雕塑、绘画的研究,不仅确立了艺术史研究的诸多标准,还帮助规范了18世纪人们对古希腊艺术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也发展出以古典美为典范的审美理论。施莱格尔敏锐地发现温克尔曼美学思想可用至于古希腊诗歌研究,遂立志要做“古希腊诗歌的温克尔曼”,《古希腊诗歌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动机下完成的。强烈的古典主义倾向决定了施莱格尔对现代诗歌轻视的态度,而且较之席勒,年轻的施莱格尔远为激烈。 《古希腊诗歌研究》开篇就对现代诗歌极尽讽刺之能事:“毫无疑问,现代诗歌要么还没有达到自身努力奋斗的目标,要么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它的发展没有具体的方向,历史缺少持续性,整体也不够统一……哪怕是最出色的现代诗歌——气势很大,值得尊敬——虽时常把心灵统一起来,但也只不过为了把它置于更痛苦的时尚形式之中。它们在灵魂中丢了根刺,带走的远比给予的多。”(41)同席勒一样,施莱格尔认为现代理性或曰哲学化显然败坏了诗歌的趣味,使现代诗歌远离了真正的美,甚至哪怕最出色的现代诗歌都是以所谓的“真理”“道德”而不是“美”为目标。而一旦失去“美”的至高原则,“丑”就公然进入了诗歌,“差不多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每一种原则悄然成了预设的条件或被暗示出来,作为艺术最高的目标和基本的法则,作为他们作品价值的终极尺度。也就是说,每一个原则,除了美的原则。情况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不仅最杰出的诗歌都在公开表现丑,而且还成了现代诗歌的指导原则”(42)。更有甚者,现代诗歌已经以其“不自然”、“哲学化”形成了“一整个特征鲜明的主要流派”,但它甚至并不比科学、历史更近于优美艺术,而且科学、历史以求真区别于优美艺术的求美,现代诗歌则完全走到了优美艺术的对立面——求丑,“丑往往不可或缺,而美则甚至只是被用来作为实现其具体的、哲学的目的的手段”(43)。留在灵魂中的那根“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那就是“丑”。 然而,施莱格尔虽说在抨击现代诗歌时不遗余力,但有时似乎又对现代诗歌情有独钟。这位诗人气质浓郁的文学批评家从来都不以逻辑严谨见长,其理论文章因而难免观点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运用歌德的特征化理论,批评现代诗歌“混乱”“没有法度”,充斥着“怀疑主义”“缺少特征似乎是现代诗歌的唯一特征”(44)。同时又运用康德的美学思想,斥责浪漫主义诗歌完全为“指导性的概念”所驱动,其狂野想象缺少自然基础,已经走错了方向,“它受制于概念的规则,就像这些幻象所应该有的那样脆弱和模糊,知性成了审美发展的规范原则”(45)。另一方面,施莱格尔似乎又认为,能表现出这种“混乱”也是难得的才能,“人们最终必须承认,对混乱的表现,就其所有丰富性、就其出于无限活力的绝望个性而言,同对完全和谐中的盛大和活力的表现相比较,需要同等的(如果不是更大的话)创造力和艺术智慧”(46)。而且,该如何评价莎士比亚?席勒把莎士比亚同荷马相提并论,施莱格尔不遑多让,奉莎士比亚的作品为现代诗歌的巅峰之作,称其最深刻全面地体现了现代诗歌精神。然而,按照古典美学的标准显然无法解释莎士比亚的巨大魅力——这是所有古典主义批评家们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席勒把莎士比亚作为现代诗人的例外而归为天真的诗人,但这显然没有说服力,同他自己古今对立的理论也颇多矛盾。施莱格尔自然也绕不过去,而且似乎完全随着喜好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我们似乎完全失去了恰当的视角。任何视其诗歌为美的艺术的人,最终将只会发现更深刻的矛盾——他越具有辨别力,对诗人的认识就越深”。施莱格尔写道,“自然产生美和丑,它们相互混杂,且同样丰富,莎士比亚也是如此。就整体而言,他的戏剧没有一部是美的;在整体安排上,美从未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在自然中一样,哪怕是最独特的美的要素也难免附着的丑,它们都只是另一个目的的方法。它们都服务于特征化或哲学兴趣”(47)。同席勒一样,施莱格尔显然认为只有“自然”二字才能解释莎士比亚的天合之作。但不同的是,施莱格尔没有把莎士比亚往古代诗人上靠,没有用古典美的理念来解释其作品,而是直接用“丑”名之,且以“自然”的名义。只是,这儿的“丑”表达的不再是否定,而是热情的肯定。就这样,“施莱格尔明确建议,把丑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且倾向于把它完全排除在美的范围之外,但是却发现丑不可避免地闯了进来”(48)。 这必然的倒转与其说是施莱格尔理论上的矛盾,不如说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施莱格尔对现代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全面深入的否定或“丑化”,反转成了系统、深刻的现代诗歌美学。施莱格尔的创造性在于把“丑”纳入评价体系,而且丑无须特征化自身就可以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因素。施莱格尔的这种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现代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对古典美学不啻反戈一击。施莱格尔曾狂热地把古典美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一旦反过来看,肯定就变成了否定,不食人间烟火的古典美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席勒就清醒地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他在写给歌德的一封信中不点名地批评施莱格尔说:“近来的美学作者,在他们把美的概念独立出来并使之纯净化的努力中,近乎抽空了美的概念,使之变成了空洞的声音。”(49)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艺术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按照鲍桑葵的说法,施莱格尔的《古希腊诗歌研究》“第一次把丑作为解释美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50)。施莱格尔的艺术丑理论奠定了浪漫主义美学的基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鲍桑葵自己也正是在施莱格尔及其继承者建立的研究基础上才发展出了新的艺术丑理论。 四、罗森克兰兹:“丑的美学” 鲍姆加登的《美学》出版后整整100年,德国哲学家罗森克兰兹出版了《丑的美学》。按照罗森克兰兹自己的说法,他用了15年之久才写出了这部著作。《丑的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纳为:艺术丑何以可能?是典型的、黑格尔意义上的“艺术哲学”(51),只不过研究的不是美而是丑。 《丑的美学》题记是歌德《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中俄瑞斯忒斯对伊菲革涅亚说的一句名言:“听从我的建议,/不要过于爱恋太阳或星辰,/来,随我下降到黑暗王国!”(52)这也是歌德的《浮士德》中主角浮士德的座右铭。《浮士德》对丑的形象、特别是魔鬼摩菲斯特思以及大量女巫的经典表现把艺术丑提升到了新高度。罗森克兰兹更是用许多以表现丑著称的伟大艺术家开篇:“心灵的伟大探索者已经深入到邪恶可怕的渊薮,并再现了他们在暗夜里直面到的令人敬畏的形式。伟大的诗人如但丁进而描画了这些形式的外形,奥坎那、米开朗琪罗、鲁本斯和彼得·康纳琉斯这样的画家已经给予它们以感性的呈现,而像路德维格·斯鲍尔这样的音乐家则让我们听到了可怕的毁灭之音——邪恶尖声嚎叫出它被撕裂的灵魂的冲突。”(53)从歌德到斯鲍尔,这些杰出的艺术家及其伟大的作品足以说明,丑同艺术甚至是伟大的艺术完全可以共存。 然而,罗森克兰兹作为一个哲学家,像门德尔松一样,深知艺术和丑之间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在列举了艺术丑的诸多伟大现象后,罗森克兰兹清醒地指出:“既然丑是美的对立面,那么丑的美学听起来就像木铁(一样不可能)。”(54)在分析“美的丑”时,罗森克兰兹客观地指出,艺术真正的动机“是心灵对纯粹的、没有混杂的美的渴求”,紧接着直面问题:“如果创造美是艺术的任务,那么当我们注意到艺术也能产生丑时,岂不是最大的矛盾?”(55)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罗森克兰兹先反驳了两种流行的观点:(1)艺术的确能产生丑,但是以美的方式;(2)美需要利用丑让自身显得更美。(56)对于第一种看法,罗森克兰兹认为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增加了第二个矛盾,而且更大,因为丑的事物不可能变成美的事物。罗森克兰兹重点反驳了第二种观点,在他看来,美是绝对的、自足的,根本不需要什么反衬,“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美的事物完全内在于自身,无须任何外在的支撑,也无须对立面来彰显。丑不会让它变得更美”。相反,“诸如此类的反衬只会造成干扰”(57)。罗森克兰兹是黑格尔最得意的学生,是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他的反驳具有鲜明的黑格尔色彩,而他解决艺术和丑之间矛盾的方法也是黑格尔式的。 罗森克兰兹自己的观点可分成两个部分,首先,艺术不可能避开丑。在他看来,艺术丑是客观的存在,“可以在理念的本质中找到答案”。理念的本质就是“允许外形的存在”,这决定了作为“理念感性显现”形式的艺术需要感性要素(尽管感性要素同善和真的自由相对立),从而为“否定”提供了可能性,换句话说,为丑(美的否定)进入艺术打开了大门,“如果艺术希望表达的不只是理念的单一的经验,它就不可能避免丑陋”。罗森克兰兹写道,“纯粹理念呈现于我们的是最重要的美的时刻,是积极的,但是自然和心灵难道不应该以其全部戏剧性的深度得以再现吗?如此,自然的丑陋、邪恶和魔鬼般的事物就不可或缺”(58)。罗森克兰兹由此确立了“艺术丑”的合法性。但这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丑因此和美是否同等重要?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在黑格尔派的“精神现象学”中美是绝对的存在,而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正是罗森克兰兹的看法:“美,像善一样,是绝对的;丑,像恶一样,是相对的。”(59)实际上,这个论断在一开始就被罗森克兰兹明确地提了出来,并把它确立为“丑的美学”最基本的原则,它也决定了罗森克兰兹对艺术和丑之间矛盾的进一步解释。 其次,丑必须服从于美。丑可以进入艺术,但必须为美所收服,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同艺术所追求的目标相矛盾,问题是美如何征服丑?罗森克兰兹一开始似乎认为,在艺术同一体中,美、丑关系密切,而基于美的绝对地位,丑会自我消解其同美的对立,与美同归整一。在这过程中,美作为一种力量自我呈现出来,一再收服丑的反抗,丑最终也会实现自我超越。罗森克兰兹把这个过程称为“美化”(Beautification),“在这过程中,在这美化的过程中,无数的快乐被唤起,引发了我们的欢笑。在这样的运动中,丑把自身从它混杂的、自我指涉的本性中解脱出来。它承认自身的无力,并成为滑稽的东西”(60)。在稍后分析“美的丑”时,罗森克兰兹对美化的过程作了更详细的解释。在罗森克兰兹看来,艺术不会直接再现丑,因为这同“美化丑”的概念相矛盾。相反,艺术首先必须“理想化”(idealize)丑,“艺术必须理想化丑,即必须按照美的一般法则处理它,这将违背丑存在的本性,艺术不是好像要隐藏、伪装、篡改丑,以华丽的东西装点它,而是按照其审美意义的参数赋予它以形式和真正的完整性”。理想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净化(purification)的过程,“这种净化去除了不确定的、偶然的、缺乏特征的东西,是一种理想化的活动,它并不包括为丑增加一种异己的美,而是直截了当地清理掉那些把丑标记为美之对立面的要素”(61)。经过“理想化”、“净化”处理,丑虽仍然是丑,但已经没有了否定的因素,而通过对丑内在否定要素的否定,丑生成了滑稽,并得以同美实现整体意义上的同一。 对艺术丑问题的深入分析极大地丰富了罗森克兰兹丑的概念。综合罗森克兰兹对丑的定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本体上来说,美是绝对的,丑是相对的;美是肯定的,丑则是美的否定,依赖美而存在,“丑的概念只有在同另一个概念相联系时才能被把握。这另一个概念就是美,美构成了肯定的前提,丑只有在美的范围内才能如其所是。如果没有美,当然就不会有任何丑,因为后者只是作为前者的否定而存在。美是神样的、原初的理念,而丑作为它的否定只是第二位的存在”(62)。当然,美、丑很难分开。其次,丑从外延上可分成三个类别:自然丑、精神丑和艺术丑。自然的绝对目标是“生命”,自然丑源自生命冲动同纯粹形式之间的背离,“自然永远处在生成变化之中——这对所有的自然物来说都是基本的,在生成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度和不合比例的现象,从而扰乱了自然自身所追求的纯粹形式,于是就有了丑”(63)。精神的绝对目标是“真和善”,精神丑在于内在恶及其外化,“意志的真和善会促进人格尊严,并自内而外在感性外表上体现出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就此而言,黎西滕伯格的说法是对的,即所有的德行都美化人,所有的恶行都丑化人”(64)。艺术的绝对目标是纯粹的美,也即理念单纯的感性显现,艺术丑则源自感性的复杂性及其同精神的必然对立,“出于生成总体理念外形这个理由,艺术难免制造丑陋。把理念局限于单纯的美的事物,这种理解是肤浅的”(65)。第三,丑在内涵上被归纳为三种形式:无形式(formlessness)、不正确(incorrectness)和畸变(deformation)。无形式就是“对形式普遍统一性的否定”,但无形式并不一定就是丑——所有形式的纯粹缺失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只有当一些内容本该有形式却没有,或者有形式但其形态却同内含的概念不相称,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形式才是丑的”(66)。不正确是相对于正确而言,而正确通常“意味着准确无误地再现自然形式的必然表象”,但错误总在所难免,因而,“如果一个形式违背了自然的规则,矛盾冲突必然会生成丑陋。就算自然本身,若脱离常规,漠视了它的法则,也不再是美的”(67)。畸变源于内在的动机,并造成了外在的“不和谐与不自然”,“无形式和不正确是丑的两种主要形式。但是仍然有那么一种形式,它实实在在地包含了成为这前两种形式的动机,这就是内在的畸变,它会爆发为外在的不和谐与不自然,因为它自身就是晦暗杂乱的”(68)。罗森克兰兹按照丑的三种形式把《丑的美学》分成三个部分,再分门别类详细论述,形而上面面俱到,形而下无所不及,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系统的审丑的理论。罗森克兰兹在西方现代审丑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他之后,德国美学大家卡里尔、夏斯勒、哈特曼等都给予丑以足够的重视,这显然都离不开罗森克兰兹的影响,夏斯勒甚至把他的鸿篇巨制《美学批评史》题献给了罗森克兰兹,而受罗森克兰兹影响最大的显然还是同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鲍桑葵。 ①鲍姆加登:《美学》,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②鲍姆加登:《美学》,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③Paul Guyer,Kant,The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tr.&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editor's introduction," xiv. ④G.W.F.Hegel,Aesthetics:Lectures on Fine Art,Vol I.trans.,T.M.Knox,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31-32. ⑤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1. ⑥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4. ⑦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6. ⑧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 36-37. ⑨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7页。 ⑩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73. (11)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74. (12)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6. (13)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5. (14)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4. (15)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4. (16)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8. (17)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43. (18)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45. (19)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 194-195. (20)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93. (21)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95. (22)拉奥孔的故事属于古希腊英雄传说,拉奥孔原本是特洛伊海神波塞冬神庙祭司,在特洛伊战争中因主张烧毁希腊人留下的木马而被女神雅典娜派来的两条巨蛇缠死。这个故事因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在其《埃涅阿斯纪》中的生动描写而广为人知。而关于拉奥孔雕像的描述主要源于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所著《自然史》(Book XXXVI.4.37-40)中的几句话:“提图斯皇帝宫殿里的拉奥孔雕像比任何绘画和雕塑都要优秀。杰出的艺术家哈吉桑德罗斯、波利德洛斯和艾森纳德洛斯都是罗德岛人,按照他们一致同意的计划,用一块完整的石头创造出了拉奥孔、他的儿子们以及不可思议地紧密缠绕着的蛇。”(Pliny,Natural History,Vol.X.trans.D.E.Eichholz.M.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eb Classical Library,1962,pp.31-33.)这座神奇的雕像自古罗马之后便湮没无闻,直到1506年才重见天日,被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收藏于梵蒂冈的伯尔维多宫。但由于种种原因,温克尔曼事实上从未见过这座雕像。 (23)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Reflections on th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of the Greeks,tr.Henry Fuseli,London:Translator,1765,p.30. (24)莱辛:《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69页。 (25)莱辛:《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6页。 (26)莱辛:《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27)莱辛:《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37页。 (28)莱辛:《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页。 (29)莱辛:《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35页。 (30)莱辛:《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30-131页。 (31)莱辛:《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37页。 (32)Johann Gottfried Herder,"Critical Forests,or Reflection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Selected Writings on Aesthetics,tr.& ed.Gregory Moore,Oxford:Pre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144. (33)Johann Gottfried Herder,"Critical Forests,or Reflection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Selected Writings on Aesthetics,tr.& ed.Gregory Moore,Oxford:Pre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161. (34)Johann Gottfried Herder,"Critical Forests,or Reflection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Selected Writings on Aesthetics,tr.& ed.Gregory Moore,Oxford:Pre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164. (35)Johann Gottfried Herder,"Critical Forests,or Reflection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Selected Writings on Aesthetics,tr.& ed.Gregory Moore,Oxford:Pre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p.168-169. (36)席勒:《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载张玉书编选:《席勒文集》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37)席勒:《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载张玉书编选:《席勒文集》VI,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38)席勒:《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载张玉书编选:《席勒文集》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39)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5. (40)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1. (41)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17. (42)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18. (43)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31. (44)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20. (45)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26. (46)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18. (47)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d ed.,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34. (48)Barnard Bosanquet,"The Aesthetic Theory of Ugl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1,No.3,1889-1890,p.394. (49)Barnard Bosanquet,"The Aesthetic Theory of Ugl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1,No.3,1889-1890,p.38. (50)Barnard Bosanquet,"The Aesthetic Theory of Ugl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1,No.3,1889-1890,p.37. (51)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明确指出:“美学……的领域是艺术。”参见G.W.F.Hegel,Aesthetics:Lectures on Fine Art,Vol I.trans T.M.Knox,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 (52)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31. (53)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31. (54)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32.“木铁”一词源自古希腊,意指把两种不相干的东西(有机的木和无机的铁)结合在一起,用以表达对立面之间的不可能性,在德语中是众所周知的逆喻。 (55)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47.这个问题在《丑的美学》中频繁出现,如第48页:“艺术的目的只能是美,又怎么能创造出丑陋?”第50页:“艺术果真再现丑,这似乎同美化丑的概念相对立。”第258页:“艺术作为美的事物原初形态,应该能以丑作为对象,这似乎是矛盾的。”等等。可以说贯穿了全书,作为核心问题被反复甚至重复论证,由此足见罗森克兰兹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56)第一个观点显然来自康德,他在《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中说:“美的艺术的优点恰好表现在,它美丽地描写那些在自然界将会是丑的或讨厌的事物。”(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而第二个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门德尔松广为流传的论断:“这就是我们情感的本性。一点痛苦,混合到甜蜜的快乐中,会增加愉悦,使甜蜜加倍。”参见Moses Mendelssohn,Philosophical Writings,Daniel O.Dahlstrom tr.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74. (57)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47. (58)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48. (59)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33. (60)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33. (61)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50. (62)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33. (63)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37. (64)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42. (65)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48. (66)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56. (67)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57. (68)Karl Rosenkranz,Aesthetics of Ugliness,tr.Andrei Pop and Mechtild Widrich,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5,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