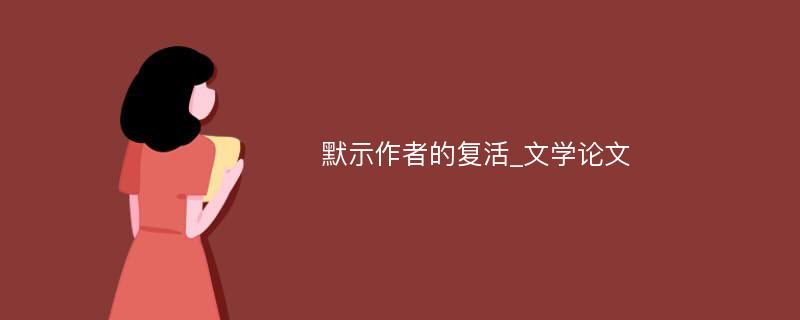
隐含作者的复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5-0030-11
读者一定不会感到奇怪,《小说修辞学》① 的作者面对批评家纷纷宣称“作者的死亡”,会觉得毛骨悚然(其实,涉及的只是隐含的作者②;无人宣称那有血有肉的作者根本不存在)。怎么竟会相信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我们如何阅读作品无关?诚然,批评家可以说作者在文本之外所表达的意图,可能会与作品所最终实现的意图大相径庭。然而,难道这种差异不恰恰生动地说明了必须区分隐含作者和[有血有肉的]作者吗?
这篇论文本可致力于批驳各种各样暗杀作者的荒唐企图,然后再举出一些使作者复活的最出色的论著。有的论著非常精彩,譬如出自詹姆斯·费伦和彼得·拉宾诺维兹之手的,我简直想照抄下来。但本文将做另一件事:就我们为何需要努力维护“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无论如何对之加以界定),而再次进行一次说教。
当我首次论述隐含作者时,至少有三种动因,它们都与我对20世纪50年代批评界的状况感到忧虑相关。
1、对当时普遍追求小说的所谓“客观性”而感到苦恼。很多批评家提出,小说家若要站得住,就必须“展示”(showing)而不是“讲述”(telling)故事,以便让读者作出所有的判断。小说家若要令人称道,就必须摒除一切公开表达作者观点的文字。作者的评论不仅常常枯燥乏味,而且总是违背真正的“诗意”性质。
早在巴特、福柯以及其他人毫不含糊地试图“暗杀”作者之前,批评家已经宣称,真正令人赞赏的小说只是艺术性地展示故事,清除了表达作者观点的所有文字。令人称道的小说必须客观表达,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不是仅仅被遮掩,而是完全被清除。③
这种立场经常导致贬低约瑟夫·菲尔丁④、简·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这样的天才作家的超凡叙事技艺,当然遭到贬低的还有很多伟大的欧洲和俄国小说家。这种立场还经常导致对作品的明显误读。很多“以视点为重”的批评家完全忽略公开表达的作者修辞所起的十分重要的审美创造作用。倘若不是篇幅有限,我会引出“乔治·艾略特”(这是女性天才玛丽安·埃文斯创造出来的男性隐含作者)发表的长段作者评论。她的/他的积极有力的“介入”不仅对我阅读其作品提供了帮助,而且还令我赞赏,甚至爱上了隐含作者本人。假如我与玛丽安·埃文斯相识,我会爱上她吗?这要看我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到这位有血有肉的人。但她创造的以多种形式的自觉“介入”为特点的隐含作者真是妙不可言。
2、对学生的误读感到烦恼。虽然我在大学里教的学生丝毫不反感那些自我意识很强的伟大的叙述者的讲述(他们没有读到对这种讲述的抨击),但是他们却经常不了解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隐含作者与有血有肉的作者之间的差异。很多学生从未学会如何将不同程度的不可靠的叙述声音与有意创造出这种声音的隐含作者区分开来,尤其在阅读所谓客观的现代小说时是如此。
现在想起来,当时经常出现的最令人忧虑的误读,涉及的是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学生在阅读时完全与霍尔登·考尔菲尔德相认同,而看不到塞林格字里行间对这位主人公的严重错误和弱点的反讽。学生以为作者笔下霍尔登的话语基本上都是正确可靠的。批评界对这种广泛存在的误读不予关注,这让我倍感烦恼。
3、为批评家忽略修辞伦理效果(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的价值而感到“道德上的”苦恼。我对伦理的这种强调招来了很多攻击。当时批评家坚持断言,小说也应该像诗歌那样“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不表达[意义]”;小说也跟诗歌一样“不作用于社会”。尽管跟诗歌相比,对小说持这种“唯美主义”论断的批评家相对较少,但不少批评家接受了奥斯卡·王尔德那样的论断:“根本不存在符合道德或违反道德的书。书只有写得好坏之分。仅此而已。”⑤ 时至今日,虽然还有不少批评家拒绝考虑伦理问题,但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承认存在小说伦理。J·M·库切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评论均公开宣称库切赢之无愧,尽管其作品中有不少令人感到压抑的片断,但是其作品帮助我们改进了在这个充满不幸的世界上,回应各种残忍和苦难的方式。与1950年代强调“纯粹”、“诗意”的批评家不同,当今大多数批评家都承认(有的仅仅是默认)伟大的小说可使我们在伦理上受益——除非我们加以误读。⑥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接受了不久被称为“读者反应”的运动,断言阐释完全在于读者一方:“至于亨利·詹姆斯的人物在做什么,我的解读远比詹姆斯的意图重要,那我又有什么可以跟他学的呢?什么也没有。”⑦
除了这三种动因,还有第四种动因。我进一步考虑了真实作者对隐含作者的创造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也无处无时不存在建设性和破坏性的角色扮演。无论在生活的哪一方面,只要我们说话或写东西,我们就会隐含我们的某种自我形象,而在其他场合我们则会以不尽相同的其他各种面貌出现。有时,这种隐含的形象会优于我们通常自然放松的面目,但有时隐含的形象又令人遗憾,比不上我们在其它场合的面目。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区分有益的和有害的面具。在文学批评中尤其如此。
数十年前,索尔·贝娄精彩而生动地证明了作者戴面具的重要性。我问他:“你近来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哦,我每天花四个小时修改一部小说,它将被命名为‘赫尔索格’。”“为何要这么做,每天花四个小时修改一部小说?”“哦,我只是在抹去我不喜欢的我的自我中的那些部分。”
我们说话时,几乎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模仿贝娄,尤其是在有时间加以修改时,我们抹去我们不喜欢或至少不合时宜的自我的痕迹。假如我们不加修饰,不假思索地倾倒出“真诚的”情感和想法,生活难道不会变得难以忍受吗?假如餐馆老板让服务员在真的想微笑的时候才微笑,你会想去这样的餐馆吗?假如你的行政领导不允许你以更为愉快、更有知识的面貌在课堂上出现,而要求你以走向教室的那种平常状态来教课,你还想继续教下去吗?假如叶芝的诗仅仅是对他充满烦扰的生活的原始记录,你还会想读他的诗吗?假如每一个人都发誓要每时每刻都“诚心诚意”,我们的生活就整个会变得非常糟糕。
更为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对好的和坏的面具不加区分,我们就更有可能会落入坏面具的破坏性的圈套,譬如政客们欺诈性的修辞花招(rhetrickery⑧)。此外,我们还难以欣赏我们在伦理上对精彩面具的依赖:我们的配偶所创造的最好的隐含作者,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记者等所创造的最佳形象,如此等等。是的,你不妨列出你最喜爱的戴上有益面具的人。就我而言,正如本文将要说明的,我最欣赏的是知道如何抹去自己不喜欢的自我的作者。
一个简单的伦理事实是:我们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别人(尤其是作者)创造的较好的隐含形象当作自己的生活榜样。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经常共处的人(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有益或有害的影响,会大于文学作品中的隐含作者。但即便就亲友而言,他们影响我们的方式也时常是抹去他们不喜欢的自我。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亲友最早使人接触文学活动——让生活从幼年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隐含作者。
这种投射的,也经常是完全虚假的自我可谓无处不在,这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问题呢?这些面具总是在某种程度上遮掩着更为复杂,且较为低劣的自我。有的人会将这样的假面具仅仅看成虚伪的表现,那么,我们应该对之加以颂扬吗?这样的假面具提供了比作者的日常生活更好的生活榜样,那会使我们获益吗?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彻底谴责这种面具,仿佛它是施瓦辛格⑨ 式的虚伪行为呢?
要回答这些大得吓人的问题,恐怕得写一本书。我现在退至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落:贝娄所提到的那种文学面具。我相信我们都会感激贝娄抹去他不喜欢的自我。在我与他交往的这么多年里,我看到了贝娄不讨人喜欢的一些其他版本,假如这些“贝娄版本”被允许支配他的小说,恐怕会把这些小说完全毁掉。此外,研究了他的手稿的人(我本人没有)发现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他从数千页手稿中挑出了几百页,这几百页的隐含作者为他所喜欢,也为我所喜爱。
诚然,我们只能对作者的性格加以尝试性的判断。但是,只有愤世嫉俗的人才会声称不存在真正的道德上的差异:“既然都是欺诈,何苦操这份心?”当严肃认真的作家把作品交给我们时,有血有肉的作者创造出来的隐含作者,会有意无意地渴望我们以评论的眼光进入其位置。这些隐含作者通常都大大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作者。
既然我以前关于隐含作者的探讨聚焦于小说,在此我将转向诗歌。我的基本观点是:不仅隐含作者是我们颇有价值的榜样,而且我们对于较为纯净的隐含作者和令人蔑视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区分,实际上可以增强我们对表达前者的文学作品的赞赏。(就我所知,这一观点尚无人予以生动的说明。)
阅读诗歌时,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跟小说隐含作者不同的情况呢?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很少见到诗人反讽性地有意创造出有缺陷、不可靠的叙述者。诗人只是偶尔创造出像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费恩或《去日留痕》⑩ 中石黑一雄笔下的老管家那种一直靠不住的叙述声音。更确切地说,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与隐含作者完全一致的彻底净化了的叙述者,而有血有肉的诗人希望我们分享这种隐含的立场:“我——诗人——直接用我的真实声音跟你说话。”然而,如果我们查阅从古到今任何一位伟大诗人的自传和传记,就会发现作品中诗人的自我装扮相当优雅,对生活中的悲欢十分敏感,引起我们由衷的羡慕,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诗人却常常与之相违。我们不妨重新阐述叶芝的相关文字:我们通过自我斗争来创造诗歌,这有别于我们跟他人斗争时的修辞。(当然,我会扩展“修辞”一词,使之涵盖内在争论。)
的确,有的诗人,譬如勃朗宁,有意创造了诗中不可靠的叙述声音。(11) 近来,还有很多像西尔维亚·普拉斯那样的诗人,在作品中出色地揭示和再现了他们自毁性的缺陷和痛苦——似乎毫不掩饰,极其真诚。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创作诗歌时所实现的自我,也要大大强于在用早餐时咒骂配偶的自我。
有的读者在传记中读到有血有肉的作者的生活有多么糟糕时,感到非常烦恼。当一位传记作家在描述一位备受尊崇的诗人时,若揭示出其各种短处,很多读者会感到其作品被玷污了。当我们得知T·S·艾略特竭力从作品中清除了他认为会使作品“过于个人化”的自身情感因素时,难道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崇拜他的诗作吗?艾略特认为诗歌“并非用于倾泻情感,而是为了逃脱情感;诗歌不是为了表达个性,而是为了逃脱个性。当然,只有那些具有个性且充满情感的人才会明白为何会想逃脱”(12)。一方面逃脱某种情感和个性,另一方面又创造另一种情感和个性,像艾略特这样戴假面具难道不令人蔑视吗?假如他决定“毫无保留地倾泻一切”,难道他不会变成更加伟大的诗人吗?
毫不奇怪,有的读者会做出肯定的回答,还会攻击艾略特和其他诗人生产出不够“诚实”的诗歌。现在几乎出现了整个这么一个行业,专门“暴露”诗人如何压制了其有问题的自我,常常暗示假如诗人更为诚实的话,他们笔下的诗就会更加精彩。但你不应该感到奇怪,我对那一问题的回答是“不会!”。倘若我们崇拜的那些诗人没有戴上面具,那么他们的大多数作品都会糟糕得多。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激诗人做那样的清除吗?(13) 既然他们有这样的清除能力,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而赞赏他们吗?
我在此仅举出两个实例,其一是罗伯特·弗罗斯特,有的传记作家几乎带有恶意地“暴露”了这位诗人的生活私事。在他下面这首诗《一段聊天的时间》中,我们看到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又是谁呢?
当一个朋友从路上叫我
并意味深长地放慢马步,
我那片坡地还没有锄完,
所以我没停下来张望,
而是原地大声问:“什么事?”
不,虽然没有聊天的时间,
我还是把锄头插进沃土,
五英尺长的锄头锄口朝上,
然后我慢慢走向那道石墙,
为了一次友好的聊天。(14)
( When a friend calls to me from the road
And slows his horse to a meaning walk,
I don' t stand still and look around
On all the hills I haven' t hoed,
And shout from where I am," What is it? "
No,not as there is a time to talk,
I thrust my hoe in the mellow ground,
Blade-end up and five feet tall,
And plod:I go up to the stone wall
For a friendly visit.(15))
首先,这位说话的叙述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是一位令我由衷赞赏和乐意接受的人:一位责任心强又很勤奋的农民,尽管他需要尽快锄完山坡上的地,但出于对友情的格外珍重,还是停下了手中重要的农活,去跟朋友聊天。这位农民热爱肥沃的田地,但在朋友造访时,不惜暂离田地。对他而言,在乡村跟朋友好好聊聊,这更有价值。
但谁又是背后那位创造了这位叙述者的隐含作者呢?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如同一人:隐含作者显然没有对叙述者加以反讽。但隐含作者并非仅仅是友好的农民。尽管他也具有叙述者的美德,但他更为复杂。他忠诚于诗歌形式,数小时甚至好几天都努力写作,以求创作出符合自己的规则的有效的押韵。这样,就没人可以说押韵只是由同韵决定的:road与hoed押韵;walk与talk押韵;around与ground押韵;tall与wall押韵;还有,相隔六行之远的" What is it" 和" friendly visit" 押韵。他还努力创作出理想的格律和行长,这样他就可以用最后惟一的短行" For a friendly visit" ,给我们带来一种意外。对我来说,这样的工作比锄地要辛苦得多(两种我都干过)。能遇上这么一个人也确实不错:他虽然热爱农活,却更为重视友好交谈,但他最为重视的是写出一首完美的诗歌;就我们所知,他多年没碰锄头了。其结果:虽然这不是弗罗斯特最伟大的一首诗,但隐含作者正在朝着伟大的地位迈进。这是比可靠叙述者要丰富得多的神秘人物,尽管两者之间不存在惊人的对照:毕竟一位忠实的农民也可以是诗人,而且农民和诗人都可以乐于跟邻居聊天。
与此同时,谁又是那位有血有肉的弗罗斯特呢?或许你也会像有的人那样,拒绝提出这一问题,因为答案可能会减弱读诗带来的快感。上面那两位弗罗斯特与传记中描绘的弗罗斯特之间存在令人震惊的对照。(16) 一部最有影响的率先对他进行负面揭露的传记称他为“可怕的人,心眼很小,报复心强,是位糟透了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怪物,一个残忍成性的人……一个装扮为乡村农民类型的人,但实际上一直是富有的城市人”(17)。近来的传记作家没有把他描写得那么坏,有的尽管承认弗罗斯特有可怕的弱点,但对他的描绘要正面得多。(18) 然而,没有任何传记揭示出一个足够好的弗罗斯特,让我乐意成为他的近邻或亲戚,或午餐伴侣。我只愿意跟这样的人成为近邻或兄弟:出现在上引那首诗或更好的诗歌中的弗罗斯特,或我读大学时给我们演讲的那位出色的故作姿态的弗罗斯特。
这样的对照究竟是减弱了我对弗罗斯特诗歌的赞赏,还是如我所说,实际上多少提高了这些诗歌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在西尔维亚·普拉斯那里,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一组相互对照的自我。就我研究了生平的为数不多的诗人来说,普拉斯是最有可能获得这么一种奖项的:“有着最多的相互矛盾的隐含作者的有血有肉的人。”至于自己笔下的什么诗歌真正符合她想要展现的那一自我,她一直犹豫不决,她的日记、她的先生和传记作家都揭示出这一点。她不信任自己多种声音中的任何一种,尽管她觉得这些声音创造出来的诗歌和小说还是不错的。当她解释为何在历经修改之后,选择了《楼梯之魔》作为其第一部诗集的标题时,说道:“……这一标题涵盖了我的书,‘解释’了诗歌对绝望的表达,绝望就像希望那样具有欺骗性。”(19)
普拉斯不仅要在绝望之声和希望之声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还要在愤怒之声、身体暴力之声、复仇之声、性欢悦和失望之声之间进行选择,这令她痛苦不安。特德·休斯(Ted Hughes)解释说:普拉斯快要自杀的时候,最终选择了《阿丽尔》(Ariel)这一标题,这时她“删除了一些1962年以来写的较为自我放肆的诗歌,本来可能还要多删一两首,但她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了”(20)。普拉斯的母亲对于诗中描绘的女儿的形象感到苦恼,珍妮特·马尔科姆对此正确地解释道:
普拉斯似乎从未想到《阿丽尔》和《钟型坛》中的“我”就是她想要再现和被人记住的“我”——她似乎从未想到她为了发表而这样写作是因为她希望读者这样来看她,她展示给母亲的形象并不是她希望展示给读者大众的那种形象。(21)
我还要更进一步说:“她母亲所了解的那一自我,并不是她真正希望具有的自我。”(22)
普拉斯故去后,休斯决定出版她的诗集时,除去了诗中部分自相矛盾之处。他在前言中这样解释道:“几位顾问感到,这些[后期]诗歌中互相冲突的强烈情感也许难以被读者大众接受……这种担忧显示出一定的洞察力。”(23) 普拉斯的日记(我仅读了一部分)记下了很多故事,其中不少好像是真实记录,但有的显然进行了加工润色,以便将来发表,这些日记清除了她不喜欢的自我。然而,在大部分故事里,可以发现她在努力寻求和投射某种更为优秀的“自我”,尤其是那个懂得如何当好一个经常痛苦的女人,而不仅仅是女人的“自我”。
在诗作中,普拉斯经常揭示自己在竭尽全力,诚实地描绘某种真实的、被损害了的自我。但令人感到幸运的是,当她坐下来写作关于这些自我的诗歌时,这些自我往往逃遁不见了。普拉斯曾因丈夫特德·休斯跟其他女性调情而勃然大怒,将“他在1961年冬写下的一切撕成了碎片,还撕毁了他的莎士比亚的作品”(24)。难道我们要为普拉斯没有写一首关于这一时刻的诗而感到遗憾吗?
甚至在涉及她临近的自杀的后期诗作中,思考着死亡的隐含作者依然很有创造力。下面是从她的《边缘》(这可能是她的最后一首诗)中引出的结尾部分:
这个女人已臻于完美。
她死去的
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
希腊命运女神的幻像
流动于她宽外袍的淌卷里,
她赤裸的
双脚似乎在说:
我们已走了老远,一切都结束了。
每一个死去的孩子盘卷着,一条白色的毒蛇,
在每一个小小的
如今已空了的奶罐子。
她已将
他们掷回自己的体内像玫瑰
的花瓣关闭当花园
凝结而芳香自
夜华甜美、深沉的喉间流出。
月亮没有什么值得哀伤,
自她尸骨的头巾凝视。
她习于这类事情。
她的丧服拖曳且沙沙作响。(25)
( The woman is perfected.
Her dead
Body wears the smile of accomplishment.
The illusion of a Greek necessity
Flows in the scrolls of her toga,
Her bare
Feet seem to be saying:
What we have come so far,it is over.
Each dead child coiled,a white serpent,
One at each little
Pitcher of milk,now empty.
She has folded
Them back into her body as petals
Of a rose close when the garden
Stiffens and odors bleed
From the sweet,deep throats of the nigh flower.
The moon has nothing to be sad about,
Staring from her hood of bone.
She is used to this sort of thing.
Her blacks crakle and drag.) (26)
在大声朗读了几遍之后,我不仅对这首诗十分赞赏,而且还爱上了字里行间隐含的作者:这位作者要大大优于我在她的日记和不甚精心的诗作中遇到的作者。这位作者确实是在考虑自杀,在思忖自杀,甚至做出计划。但在那一时刻,她在创造一首美丽的诗歌,描述思忖自杀的感觉。她在思考一件可怕的事:自杀对她来说犹如比喻性地杀害自己的孩子,跟孩子一起度过的时光会随之消失,那可爱的情景会消逝,多少会变成——不,不是变成悲伤:月亮上(超越人类情感的世界)没有任何令人悲伤之处。
最后,普拉斯选择投射的那个创造者(无论她自己5分钟之前或昨天到底有何感受),试图借用诗歌的力量,把即将来临的死亡摆到涉及一般死亡的普遍真理的位置上。在探索那一真理的同时,她也在追求诗歌的优美,追求卓尔不群的诗歌结构。面临死亡的普拉斯创造出这么一个自我:在想着自杀的同时,能写出完美的诗歌。你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已经大声朗读了这首诗,就这些人而言,我的下面这番话可能会枯燥乏味。请注意她是如何用韵的:" in the scrolls of her toga" ,接下来还有" rose" ," close" ," odors" ," throats" ," bone" 。她似乎在叹息:啊,啊,啊,死亡,你带来的痛苦在哪里?
然而,那一连串“o”变成了恼人的元音押韵,以及刺耳的、爆发的头韵或半头韵:
Each dead child coiled,a white serpent...
最后出现了韵律与头韵的集合体:
blacks crackle and drag.
普拉斯的丧服究竟要把她和她的读者拖到哪儿去呢?(27) 拖到强有力的与死亡的对抗中去!
据说普拉斯是行将离世的时候写下《边缘》和其它一些最为精彩的诗歌的。她清晨五点就醒了,公寓里冷冰冰的,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心理上因为丈夫的婚外恋而伤心愤怒,因要照顾两个孩子而负担太重,渴望得到朋友经济上的帮助。当她每天清晨一连几小时写诗的时候,她一定感到最终发现了她想表达的真正的自我。她就是那样做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有创造力的自我依然是个面具——每天早晨孩子一醒来,那个面具就扯掉了。在普拉斯的一生中,她对于自己的面具一直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令她烦恼不安,其面具包括完全被动、尽职尽责的爱家妇女,有时又几乎像一个妓女,有时犹如……谁知道呢?
那么,在读这么一首诗时,我们这些读者扮演的不尽相同的自我又是怎样的呢?只有当我们承认诗人的面具使我们获益匪浅,对我们自己的各种面具有重要影响时,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诗人所戴面具的价值。(也许会有点太戏剧化,我把自己的面具称为各种各样的“布思”,而你作为读者则可以换上你自己的名字。)
首先是“布思甲”,这是完全投入的读者,他试图忠实、准确地理解全诗,力争站在隐含作者的立场上来接受诗中的每词每字,希望成为隐含作者期待的隐含读者。
布思甲试图做到柯尔律治所说的“完全悬置怀疑”(即相信故事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允许杂念的干扰,不思考本文所探讨的这种复杂的批评问题。他只是试图进入诗中世界,与隐含作者达到一致,甚至希望在自己面临死亡时,能像普拉斯那样,写下富有创造力的描述文字。
在这种和谐的阅读过程中,布思甲有意无意地加入了所有诗歌爱好者的行列,尤其是那些喜欢阅读探讨死亡的诗歌的读者。他们不同于那些憎恨自由诗的老派读者,不同于那些厌恶不“愉悦”、不欢快的诗歌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同于那些一味追求“客观”,嫌恶明显押韵的读者。隐含的读者,即彼得·拉比诺维兹所说的“作者的读者”(28),一定读了不少其它现代诗歌,否则就无法成功地阅读这首诗。此外,他们还喜爱亚历山大·蒲柏笔下那种令人惊叹的丰富韵律,蒲柏的戒律是:“声音必须与意思相呼应。”这些读者仔细考察《边缘》的细节,十分欣赏其自由诗体的那种微妙的抒情效果(上文仅对此做了部分分析)。
与此同时,布思甲还有另一个版本,权且称其为“布思甲a”,他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都清楚诗人写完这首诗后不久就自杀了(因此他不同于那些不知情的仔细阅读作品的诗歌爱好者)。隐含的“普拉斯”一定觉得这样的读者(我就是如此)会特别被这一点所打动:她在生命即将终结的绝望时刻,还能创作出如此精彩的作品。可以想见,假如我们不知道她自杀了,我们对这首诗的反应会何等不同。
我一方面真诚地戴上那些不尽相同的面具,力求进入“作者的读者”的位置;另一方面,我也必须向大家说明还有好几个另外的布思。最为尴尬的是作为介入型批评家的“布思乙”,他为了写这篇论文而利用那首诗。他曾写下一本书,来探讨好的和坏的面具,有时甚至称之为“上升的或下降的虚伪”。以此为动力,他将自己的批评兴趣强加到了作品之上,显然这对于普拉斯的任何自我来说,都是不无冒犯的,至少也是不相干的。布思乙对布思甲有所损伤,使后者难以完全进入作者的读者的位置。布思乙残忍地站在隐含作者——那个创作的、痛苦的“我”——的上面,或者说,“下面”?当然布思乙也想说自己就是戴上有益假面的实例:除了这句话,他一心一意地完全投入文学批评,诚实地探求伪装或遮蔽行为的真理,探讨这种行为和这首诗的关系。
与此同时,“布思丙”,即那位有血有肉的人,休息一会,去趟洗手间,看了一两页日报,考虑了一下如何修改探讨普拉斯这首诗的文中这一节,以求使之较为完美。他在计算机旁坐得太久了,腰酸背痛,令他苦恼:“管他呢,不做了,随便对付了算了!”实际上他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过一会,他的朋友会来跟他一起练习弦乐四重奏,他现在就应该练习贝多芬四重奏编号59之3中的大提琴部分,他们今天上午要拉这支曲子。因此,他心绪已乱,无法专心分析这首诗,或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他今天早上偶然读到了激烈抨击他的一本书的书评。
第二天,终身致力于道德说教的“布思丁”又回头来改那篇论文,他为成功演奏了贝多芬的曲子而感到高兴,但他发现自己并未关注那首诗,而是在考虑自杀。普拉斯一定期待着不少读者自己考虑过或尝试过自杀,但这位布思却从来没有过。跟一位去年自杀未遂的读者相比,这位布思的感受一定迥然相异。实际上,他有这么一种不确定的信念:自杀是不道德的,每个人都应竭力抵制这一行为。因此,他有一种不相干的、破坏审美的愿望,想对有血有肉的普拉斯进行说教,批评她抬高自杀的价值,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但与此同时,他应该清楚这篇论文的整个主旨——不应抛弃隐含作者,因为隐含作者可以帮助我们改进自己——进入了“布思丁”的领地。
当其他的布思反复阅读这首诗,反复修改写下的阅读结果时,作为批评家的“布思乙”始终以地道的学者或批评家的面貌出现,致力于客观探求这一真理:诗人的面具如何使我们获益匪浅。他略带不安地与其他隐含或实际的读者保持距离,一心挂念着要写出一篇好的论文。至于各种各样的琐碎小事,他认为与普拉斯如何创作这首诗无关,普拉斯也会这么想。“布思乙”心里清楚,这样做有可能会损伤这首诗:把自己的过度理解(overstanding)强加于这首诗,导致贬抑对它的诗意的理解。只有普拉斯的诗歌才能使他摆脱那种不公平的介入。而此时此刻,他正在写作中竭力隐含一个完全诚实的作者。
无论从何种道德或理智角度出发,读者都难免会对揭示出来的普拉斯的某些面具产生反感。我自己(即布思丙)禁不住这样想:假如她多少抵制了文化环境、家庭、朋友、英语教师和书本强加于她的“现代主义的个人主义”,假如她设法减少了对于那一真实自我充满痛苦的寻求,她本来可以避免自杀。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说的(尽管特德·休斯加以了否认),她很有天赋,本可成为伟大的小说家。说到底,我们所能做的,是感谢我们的命运——她终于找到了那个解放她的面具,写下了最后那些诗歌。哎呀,那一面具未能救她一命,她还是拧开了烤炉的煤气开关。布思丙想这么说(但或许他是错的):假如她最终坚持拼搏,继续生活下去了的话,我们的情况都会要好得多。她本来可以说:“我在赞美自杀之时,仅仅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专心写作一首美丽的诗歌。”
在本文即将结束之时,必须强调一点:本文一点也不认为戴上诗人自我的面具是一种欺骗。并不像有的传记作家所表明或其他人的文字所暗示的,作为创造物的隐含作者其实并不会导致我们将其创造者谴责为糟糕的骗子。弗罗斯特和普拉斯的隐含作者不仅与他们缺陷甚多的日常版本一样真实,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更加真实,当然也更令人欣赏,更有影响力。这些诗人在除去了他们不喜欢的自我之后,创造出来的版本既改善了他们的世界,也提升了我们的世界。想想吧,倘若没有创造出这种较为优秀的自我版本,我们的生活该会多么枯燥乏味。
与此同时,以往暗杀隐含作者的人异口同声地喊道:“为何要为这些不相干的或虚假的区分操心费力?为何不聚焦于文本,用看来正确的某种方法来阐释它?忘掉有血有肉的作者,消灭隐含作者,阐释诗歌本身吧!”另外一群学者虽然赞同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但会指责我玷污了弗罗斯特和普拉斯,因为我详细论述了他们的缺陷。为何要提及作者生活中那些令人厌恶的事情呢?欣赏他们的作品就够了。
我只能重复本文一直在暗示的那一简单回答:当我得知弗罗斯特、普拉斯和其他善于戴面具的人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细节时,我对其作品反而更加欣赏了。这些带有这般缺陷、遭受如此痛苦的人怎么能写出如此美妙动人的作品呢?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能成功,是因为他们不仅追求看上去更好,而且真的变得更好,超越他们感到遗憾的日常自我的某些部分。他们创造出一个更为实在、更为真实的自我的版本,超越了因行为卑劣而使他人烦恼的那些自我。当他们坐下来润色作品时,会除去自己不喜欢的自我中的某些部分,或者会一方面生动地描述较为阴暗的自我(普拉斯就经常这样做),一方面通过对诗歌、小说或戏剧的润色,用较为优秀的隐含作者来战胜其他的自我:“我其实是这样的,我能够展现这些价值,写出如此精彩的文字。”
还有那么一小群人,现在也插进来,对我回避了隐含作者和实际文本之间的不同而表示恼怒:怎么能那样讨论问题,似乎文本所隐含的那个实在的人跟文本完全是一回事?喔,那是因为在我看来,在布思甲所进行的那种阅读的整个过程中,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差异。只有当布思乙那样的读者开始考虑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的时候,才会创造出隐含作者的不同版本,而这些版本是作者创作文本时跟本没有想到的。当然,我现在阅读文本时重新建构的隐含作者,不会同于我在40年或20年前阅读同一文本时重新建构的隐含作者。但我要说的是:我现在阅读时,相信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当年作者所进行的选择,这些选择反过来隐含作出选择的人。诚然,在某种意义上,文本总是“在那里”,脱离了其创造者,经历了无数次阅读和误读。但是,在创作文本时,以及在我重新建构文本时(除非我把自己的过度理解强加于文本),文本和其创造者曾经是一致的。(当今对文本的误读泛滥成灾,令人震惊:读者事先就“知道”会在文中找到什么,然后自然就找到了,根本不管隐含作者希望他们找到什么,对此我就不举出实例了。)
其他一些人可能会为我对伦理效果的着迷而感到烦恼。对此,我只能略为无礼地回答:难道你们这不是呼应那些提高误读地位、暗杀作者的人吗?那些误读者仅仅关注理论和结构问题,实际上没有按照作者的意图来体验文本。由于没有通过人物与作者建立情感联系,他们就可以不考虑伦理效果。但是,有的读者能够先把抽象批评问题放置一边,全身心地体验诗歌,在完全投入、完全成功、完全净化的状态下非常兴奋地与作者融为一体——只有这样完全上钩的读者,才会发现与作者的融洽交流如何能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个被创造出来的自我创作了作品,当我们与这一自我融为一体,按其意图重新建构作品时,我们会越来越像作为创造者的隐含作者。当我们得知作品后面存在较为低劣的自我时,我们不仅会比以前更为欣赏作品,而且还能看到创造更好的自我的可以模仿的榜样。
诚然,也许以后我们会认定我们跟隐含作者的某些融合是有害的,甚或是灾难性的,但必须持续不断地研究这种融合的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遇到大量的建设性或破坏性的隐含作者——不仅在文学范畴,而且在政治、新闻、学术、教学等各种范畴中。
(原文为Wayne C.Booth," Resurrection of the Implied Author.Why Bother," 发表于James Phelan and Peter Rabinowitz(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Oxford:Blackwell,2005,75-88。本文的英文摘要由布思的学生和好友James Phean提供。)
注释:
①W.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second edition,1983.
②见W.C.Booth,The Company We Keep:An Ethics of Fiction,Berkeley,C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尤其是索引里" Author,implied" 下面的条目。
③在“作者之死”运动之前,有无数论著批判了作者的介入( authorial intrusions) ,其代表作有P.Lubbock,The Craft of Fiction,London:J.Cape,1921; F.M.Ford,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Studies in Technique,London:Duckworth,1932; C.Gordon and A.Tate,The House of Fiction,New York:Scribner,1950.
④应为亨利·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八十多岁的布思先生将Henry Fielding和Joseph Conrad记混了。——译注
⑤引自《道林·格雷的肖像》的序言。Richard Ellmann在Oscar Wilde( New York:Alfred Knopf,1988) 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述了王尔德并非一位极端唯美主义者,而是一直在追求道德或伦理效果(但对这些效果有独特的界定)。
⑥A.B.Yohoshua在The Terrible Power of a Minor Guilt ( trans.Ora Cummings.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8]2000) 中,就叙事如何无法避免伦理问题进行了一流的探讨。
⑦在这一令人感到震惊的提高读者、贬抑作者的运动中,不少批评家走极端,包括像Stanley Fish那样的才华横溢的学者(譬如,S.Fish,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我不想在此探讨这些论述的荒唐之处,部分原因是现在我更愿意认为其中有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关于如何在读者反应和充分尊重作者意图之间达到适当平衡这一问题,最精彩的探讨是Louise Rosenblatt,Literature as Exploration( 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iciation,[1965]1995) 。
⑧这是布思将" rhetoric" 和" trickery" 相结合而生造出来的一个词。
⑨指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1947—),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曾是世界级健身冠军,后又成为(动作片)电影明星,然后步入政界。——译注
⑩有几种不同译法,包括《告别有情天》、《长日将尽》等。——译注
(11)请参看勃郎宁精彩的反讽作品" My Last Duchess" 和" Mr.Sludge,the Medium" 。
(12)T.S.Eliot,"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in Selected Essays:1917-1932,New York:Harcourt Brace,[1917]1932,p.10.
(13)譬如,在尚未完稿的Modernism and the Ethics of Impersonality一书中,Tim Dean提出:假如艾略特在《荒原》中表达了其同性恋的自我,那么这首诗就不会如此伟大。
(14)引自《弗罗斯特集》(上),曹明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6-167页。
(15)R.Frost,Mountain Interval,New York:Henry Holt,[1916]1939,p.156.
(16)对此,一个很好的总结是D.Donoghue," Lives of a Poe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6 ( 18) ,1999,pp.55-57.
(17)L.Thompson,Robert Frost,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66,p.27.因为这样的谴责引起了一阵骚动,Thompson后来写的不少对弗罗斯特的描述措辞要相对温和,但依然揭示出弗罗斯特的“傲慢”如何让周围的人遭受痛苦。
(18)请参看J.Parini,Robert Frost:A Life,New York:Henry Holt,1999。有那么几部传记看来不够诚实,把弗罗斯特几乎描绘成了一位圣人:几乎是那十分精彩的复杂诚实的诗歌作品所隐含的那位弗罗斯特。
(19)S.Plath,Sylvia Plath:The Collected Poems,ed.with introduction T.Hughes,London:Faber and Faber,1981,p.13.
(20)Plath,Sylvia Plath:The Collected Poems,p.15.
(21)J.Malcolm,The Silent Woman:Sylvia Plath and Ted Hughes,New York:Alfred Knopf,1994,p.15.
(22)Malcolm,The Silent Woman,p.18.
(23)Plath,Sylvia Plath:The Collected Poems,p.15.
(24)Malcolm,The Silent Woman,p.18.
(25)张芳龄和陈黎译,见http://dcc.ndhu.edu.tw/trans/chenli/Plath.htm,译文原为繁体字。本译者对有的字加以了改动。
(26)Plath,Sylvia Plath:The Collected Poems,pp.272-273.
(27)我不知道她为何选择了复数的" blacks" 一词,我猜想这是为了押韵,当然也是为了暗示黑暗。
(28)P.J.Rabinowitz,Before Reading: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