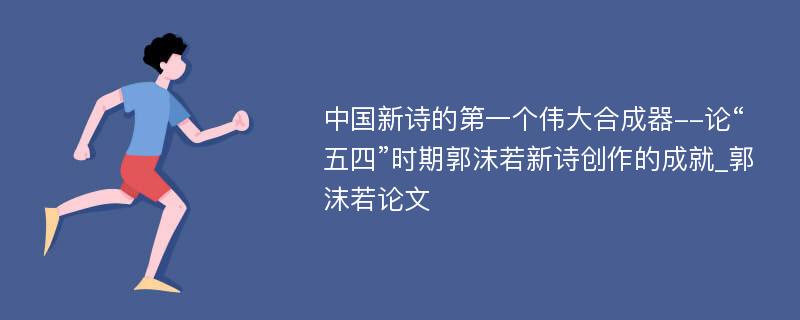
中国新诗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论郭沫若五四时期新诗创作的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郭沫若论文,第一个论文,中国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对新诗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把中国新诗从“摹仿自然”阶段推向“表现自我”阶段,并借助泛神论加强了新诗“表现自我”和反封建力度;使“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成为新诗艺术的精魂和生命线及郭诗超出同代诗人成就的所在;郭诗的活跃丰富、大胆奇特的想象,提高了新诗的素质,其浪漫主义的主色调和象征的精义,扩大了诗歌的精神内涵,进而创造了“女神体”的新诗体式。
作者龙泉明,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邮编:430072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成就不仅支撑了整个创造社诗人群,而且照亮了整个五四新诗坛。他不仅“代表五四以后最早也是特出的浪漫主义诗潮”,而且也是中国新诗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在五四时期,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中国新诗坛、参与诗歌创作的。他的《女神》一问世,就急遽地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胡适的时代”,开一代诗风,引领着新诗走上新的里程。五四诗歌革命,只有到了《女神》“异军突起”,才充分显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威力,新诗阵地才有了主将。《女神》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崭新的浪漫主义审美意识,恢宏的诗歌创造才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郭沫若的《女神》及其后几部诗集真正地实现了五四时代所要求于新诗的情感的大解放和诗体的大解放,创立了自由体诗的格局。它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美学原则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达到五四时期中国新诗主潮的顶峰,为中国新诗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一、郭沫若力倡“主情主义”,强调内心情感、情绪的表现,从而把中国新诗从“摹仿自然”阶段,推向“表现自我”阶段。从此,一种新的诗歌美学观开始建立起来。
以胡适等人的白话诗为开端的中国新诗所努力的目标,主要是打破旧诗的镣铐,创造一种白话的无拘无束的新诗,至于这种新诗内在的质素到底应是什么,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胡适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它属于“摹仿”——一种过时的陈旧的理论之范畴。然而对于五四初期的中国诗坛来说,它却是崭新的东西。在这种诗歌观念的影响下,五四初期的白话诗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带着“摹写自然”的倾向,很多诗都是对自然景观和社会现象的描摹,缺乏诗人的自发性和创造力。对于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来说,它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意绪的流溢。如果说胡适等人的初期白话诗仅仅还停留在“摹仿自然”的阶段,那么郭沫若的诗歌则进入了“表现自我”的阶段,它是对前者的超越[①]。
郭沫若明确提出“情绪说”或“自我表现说”。他认为,诗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现”,因此“情绪”高于一切,“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②]。他在1920年1月18日写给宗白华的信中激情地宣称:“我想我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hain(曲调),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旋律),生的颤动,生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郭沫若的这种理论导源于卢梭、歌德,更与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十分接近。早在1798年华兹华斯就给诗下过这样的定义:“所有的好诗,都是从强烈的感情中自然而然的溢出的。”[③]在一定的程度上,郭沫若发展了华兹华斯的偏颇之处。尽管如此,对五四新诗理论及创作来说,它显然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和反叛。在这种诗歌观的指导下,郭沫若创造了和“摹写自然”迥然不同的“表现情绪”的诗歌。他这种诗与早期白话诗相比,不但有了诗才,更有了“诗魂”,即首首都是他的血,他的泪,他的自叙传,他的忏悔录。虽然,郭沫若和五四时期的新诗尝试者们一样,喜欢用自然作为自己诗歌的原料。然而,郭沫若笔下的自然已经在自然景观中流溢着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是诗人情绪中的自然,或者说是诗人在自然中的情绪。因此,在郭沫若的自然为题材的诗中,就有了更多的“自我表现”成分,有了较为分明的主体形象。这样,郭沫若的诗歌观及其创作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中国新诗由“以物观物”向“以心观物”的转移。中国新诗到郭沫若才真正塑造了主体形象,才真正具有审美意识的主体性,中国新诗才真正跃进到现代化的行列。郭沫若的这种特点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女神》中。
二、郭沫若借助泛神论,“展开了一个辽阔而丰富的新的世界”,开拓了新诗宽广的领域,加强了新诗“自我表现”和反封建的力度。
朱自清曾经指出,在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新诗中“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一样是泛神论,一样是“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④]泛神论以反对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为其特征,它与“静的忍耐的文明”的产物——佛学是对立的。在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过渡的重要标志,就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垄断诗坛,与此同时,还有儒学和佛学影响的明显削弱和泛神论思想的崛起。严重束缚人的个性和欲望的儒学首先被当作攻击的对象,自不消说,而诱导人们远离人生、远离现实、寡欲清心、无爱无嗔,要求人们泯灭任何个性、遏制任何本能欲望的佛学,也必然在排斥之列。而人们所找到的与儒学特别是与佛学相对立的思想武器,就是泛神论。与儒学与佛学相比,泛神论超越了具体的偶像崇拜,认为一切自然皆是神的表现,主张“本体即神,神即万汇”,也就是说,泛神论把个人的主观之力充溢到整个宇宙,使之与宇宙的超自然力融汇为一,从而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无疑,泛神论作为一种鼓励人们勇于实践、勇于抗争的积极哲学,为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解放思想、解放自我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把泛神论思想带进五四新诗坛的,除郭沫若外,还有田汉、郑伯奇、冰心、宗白华等,但把泛神论思想发挥到极致的,唯有郭沫若。郭沫若的泛神论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上的泛神论,而是表现在诗歌中的诗人的泛神论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同他的个性主义、表现自我的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诗人赞美创造,赞美天才,赞美“开辟洪荒的大我”。诗中创造者的形象,既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又是一种精神,一种人神,一种自然力,一种宇宙意志。但归根到底,还是诗人自我。然而,诗人并不是用诗歌宣传泛神论,而是借助泛神论,“展开了一个辽阔而丰富的新的世界”[⑤]。“他在一种泛神主义外衣之下歌颂了自己所要歌颂的一切”[⑥]。由于诗人把自我提高到本体和神的地位,又经过主观精神的扩张,达到主客交融、人与自然合一的境地,而且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生命和感情,超越时空、永恒、无限,自我既内在于一切个别事物,又超越了一切个别事物。这样就为诗人个体的心灵自由和情感驰骋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天地。没有泛神论,也许郭沫若难以完成这种高度的“自我表现”,难以达到这种高度的审美意识的自主性。
三、郭沫若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既是郭诗中最可宝贵的东西,也是中国新诗的艺术精魂和生命线所在。
郭沫若的“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就是“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的激越的20世纪时代精神。这在他的诗歌中集中表现在个性与情感解放的深厚度与震撼力上。郭沫若诗歌在冲破束缚人的藩篱中表现出一种勃发的创造活力与人性的放恣状态,即是在对人的自由、个性、权利、尊严的追求与向往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人的解放”的深度、强度与广度。那种被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压抑而丧失殆尽的人的欲望、人的要求,在郭诗中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我们的古典诗歌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就是情感的抑郁、压制,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它都被牵引着进入了克制、压抑感情的有限空间中。要发展中国现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都必须突破这层美学规则的束缚。鲁迅写于1905年的《摩罗诗力说》是第一篇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提出挑战的诗论文章,他从整个文化精神方面革故扬新,“别求新声于异邦”,以西方的魔鬼精神取代中国固有之“平和为物”的思路,提出中国现代诗歌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首先要呼唤“立志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这样的人都有着“美伟强力”,“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先驱者们提出了“反传统”和“人的解放”的响亮口号,而五四新文学则谱写了这一时代情绪最辉煌最耀眼的一页。可以说,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审美意义上的解放,人的一切情感都被引发出来,在空前广阔的审美天地里,作自由、奔放、真实、自然的表现,无所顾忌地追求“天马行空”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与艺术世界,实际上就是追求人的放恣状态,这对于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心灵不自由的中国人,自然也是破天荒的。五四初期的白话小说较早地体现了人的解放的深度和情感表现的力量,而五四初期的白话新诗却没有实现这样的目标,在那些诗篇中,自我情绪是隐藏的甚至是萎靡的。直至郭沫若《女神》的出现,我们才在新诗中第一次感到了自我的情感可以有如此惊人的释放。在这个时期,人的主体意识、个性自由和创造活力增强了,整个心灵之窗洞开了,感情的闸门冲决了。一大批诗人热烈地呼唤感情形态的“生” 的自由、欢乐、愤怒、痛苦、孤独;他们暴露自我,抒写情爱,表达诗哲,抨击现实……他们大胆地表现着自己的情感,自由地宣泄心中的块垒,一切礼法都在强大的情感冲击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特别是浪漫诗派以情感性为诗歌的轴心和灵魂,情感的表现既成为手段又是目的;他们以情感去否定过去传统的陈规,以情感自身来证明人的存在,实现生命的合理冲动。例如冰心的婉约、轻柔和爱的至切,仿佛把那粗鲁的灵魂也要消融;湖畔诗人的爱情渴求与呼唤,更要冲破那囚禁人性的铁笼;闻一多的浓烈沉郁,似燃烧的烛火,“要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红烛》)。以及徐玉诺、朱自清对内心的彷徨、苦闷、寂寞、矛盾的复杂的心绪抒写,冯至对世态炎凉、人间无爱的揭示,都给人以强烈的新鲜的感受。这些都已突破古典诗歌的情感桎梏,但他们都不拥有郭沫若那样的强劲个性和情感的震撼力。郭沫若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无人能与他相比,他以前无古人的情感力量,冲击着封建精神大厦,他那洪钟大吕般的诗歌,奏出了不可遏止的撼人心魄的音调,真正体现了人类情感解放在中国的实现。中国诗人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情感的宣泄,在五四那一个时辰,通过郭沫若这一生命彻底爆发出来了。如果说五四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运动,那么在文艺上真正反映这场革命的极大震动的思想和情感的,则是《狂人日记》和《女神》,鲁迅以强大的思想力量,把五四批判精神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情感力量的表现上,郭沫若则是“最有光芒的,好多的作者都在他面前为之减色”,在其他诗人那里,“那辗转在封建重压之下要求解放的个性,不过是被堰拦住,只是徒然地在堰前乱流的‘小河’的水,到他,这水便一下子泛成提起全身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无限的太平洋的滚滚怒涛”[⑦]。郭沫若的主要诗作都浸蘸着他那青春的血液,满溢着那一时代的兴奋和愤怒,那一时代的骚动情绪,其烈火般的诗情灼灼烫人,其“暴躁凌厉之气”,极为生动地表达出五四时代的狂飙精神。他用生命迸发出代表整个民族的新诗,起到了冲破一切清规戒律和轰毁封建礼教所设置的种种箝制精神的路障的作用,也冲击了旧的陈腐的诗学观念。郭沫若的《女神》代表了人类本性中热烈奔放、无限创造的自由精神,它是诗人自我意识的深化和现代精神走向自觉的表现。它是那样强烈地表现着诗人的个性、气质、心理特征和精神面貌。郭沫若的诗歌真正改变了中国诗歌的性质。尽管郭诗的激情是相当幼稚的,甚至是相当空泛和驳杂的,但作为一种情绪的记载,它带给新诗坛一种新的东西:心灵的自由、心灵的欲望的自由表现,生命的本能、生命的冲动的自由表现。这是中国诗歌极其宝贵的东西,是中国新诗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是中国新诗的艺术精魂和生命线所在。
四、郭沫若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动”与“力”既是对传统诗文化的挑战,也是对一种新的诗歌境界的追求,郭诗的独到之处,超出同代人成就的地方,也在于此。
郭沫若诗歌“动”与“力”即“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不但明显表现为个性和情感解放的深厚度和震撼力,同时还指动态,它是相对于“静止”而言的。或者借郭沫若的话来说:诗人必须有一个“振幅”,读者也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振幅”,而诗歌必须是“动的律吕”。所谓“力”,也不仅仅指反抗的精神,同时也指“诉诸情绪的力”。他要求的是“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⑧]。郭诗的“动”与“力”与他接受泛神论影响有关。他从泛神论思想出发,把宇宙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进化、更新的进程,从宇宙万物看到了“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因而在《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中,都毫不遮拦地表现了伟大,表现了一切不在话下、一切不足惧的气魄。这种“动”与“力”正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动力,是那个时代的进取精神。同时,这种“动”与“力”不仅指内容,还指形式。即是说这种“动”与“力”的诗歌是不同于五四初期“平面诗”的“立体诗”。它不是一幅平面图,而是一幅有景深,有光线的阴暗对比,有时间感,有空间感,有“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在流徙创化”景观的立体图。五四初期流行的小诗,吟咏的意象多是小河、小草、小船及鸽子、乌鸦、蝴蝶之类,虽率直清新,但未能完全摆脱温柔敦厚的传统诗风和狭小境界。郭沫若诗歌则一反旧套,或探究星空,或拥抱地球,或讴歌大海,或赞美太阳,以狂放的笔力,狂幻的境界崇拜着“动”与“力”。在《女神》中,大多数诗篇都充满紧张的动荡感和强烈的情感风暴。诗人把自己和大自然雄伟的力合在一起,展示他那粗犷豪放的性格;他随手拈来一些富有力度的词语融入或嵌进句里,以加强诗的硬度和强度;他往往连续使用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手法,以增强诗的气氛和力感;他所写的人物也大都是英雄、勇士、叛逆者,“他把主观世界的英雄精神和客观世界的一切壮美雄强的形象互相交流,以达到最高的英雄诗的效果”[⑨]。我们读他的诗,无不感受到一种力的冲击波震荡着我们的心胸,无不在精神上生出勇于进取的力量。郭诗的力度感和雄放直率的风格与他那种独特的“奔迸的表情法”相关,他写诗都是“情感突变,一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着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⑩],这就使他的诗“豪放粗暴”而不含蓄蕴藉。宗白华批评他的诗缺少“流动曲折”,希望他从传统诗词小令中吸取“意简而曲,词少而工”的长处,形成一种“曲折优美的意境”[(11)]。实际上这是一个矛盾。郭沫若外向、冲动的性格和偏于直觉、灵感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诗的风格必然以雄放直率为主。他如果真正做到“意简而曲,词少而工”,也就不可能有惠特曼式的“豪放粗暴”的诗。这与其说是郭沫若的缺点,不如说是他的特点。郭沫若这些“动”与“力”的诗歌都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状态下的产物,是诗人整个情绪系统的激动亢奋,是诗人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同时又是诗人个性某一侧面的最充分最鲜明的艺术表现。郭沫若这类诗歌虽然显得直露粗暴,但并不缺乏诗味,这是因为他把强烈的直观感受融化于自己的笔下,使自己的情绪、希望、理想、幻象诗化、个性化的结果。
郭沫若那“动”与“力”的诗歌并不经常表现为高昂的呐喊和反抗,尽管在《女神》中确实常常是高昂的狂歌。另一方面,低调也具有“动”与“力”。如赞美那“高超、自由、雄浑、清寥”的静夜太空和被风摇动拟举手欢呼的松林(《夜步十里松原》),或为清晨的鸟声、鸡声和身过的稚儿而勃兴骤起(《晨兴》),或为大自然的颜色变化、动物的神态而感兴春之胎动(《春之胎动》),或从晚霞和西下的太阳引起遐思和幻想(《日暮的婚筵》)。这些冲淡的诗,虽没有“黄钟大吕”、“大江东去”般的气势和力度,但它却在多种色调、多维图景中构成了一种立体感和动态美。再如《星空》,虽然表现诗人五四退潮以后的极为苦闷与感伤的情绪,但并不使人感到“死寂”;虽然“象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12)],但诗人胸中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愤怒仍然象地火一样在奔涌,这也是一种“动”与“力”的诗歌。
郭沫若诗歌所体现出来的非凡的“动”与“力”,不仅是一种新的诗歌观念的体现,一种新的诗歌境界的追求,也是对传统诗文化的强有力的挑战。凡是对中国文化深刻反省的人,几乎无一不感到中国民族的阴柔性格与西方民族的阳刚性格的强烈对照。如果说西方文化“动”得令人眩目,那么中国文化可谓“静”得使人安睡。但到了郭沫若的诗歌,这种“静”的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郭沫若把西方现代的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对立的思潮,以及西方文化“动”的精神与敢于争天抗俗的竞争意识融进诗里,以表现大震撼大咆哮的时代精神。这种宏大、雄伟、动荡的诗歌精神与格局,与中国小巧、宁静、和谐、拘谨的诗歌传统适成对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的诗歌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郭诗的独到之处,超出同代人成就的地方,也在于此。
五、郭沫若那异常活跃丰富、大胆奇特的想象,使诗的翅膀真正飞腾起来,郭诗的诗性特征也因此大大突出了,中国新诗的质素有了很大的提高。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是一个冲动性的人”。主观性,决定了他的诗重在表现自我;冲动性,则决定了他凭灵感和直觉写诗。因此他与歌德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诗的本职专在抒情”、“以自然流露为上乘”的创作理论。他自觉他的想象力比观察力强,因此强调主观抒情,“爱写历史的东西和爱写自己”。在表达方式上,不是采取象征、隐喻等手段,而是以直抒胸臆的宣泄为满足,他从惠特曼的诗歌《草叶集》那里,找到了“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的“爆喷”的方式。郭沫若诗歌的这种“爆喷”的方式,主要是采取宣泄式、申诉式、独白式等,但这仅仅是外在表现形式,而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在情感作用下的艺术想象力。郭沫若曾给诗歌拟了这样一个公式:
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Inhalt(内容) Form(形式)
由此可见,他是把想象力看作诗人创造一首好诗的生命的一部分,并把它包括在内容范围。事实上,注重想象,充分运用幻想力,抒发他那猛烈喷射的激情,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郭沫若想象奇特开阔,想象在他的诗里,是可以任意驰骋不受任何拘束的东西,它既可以上穷碧落,又可以下尽黄泉,古今可以在须臾中看到,四海可以在片刻中抚就。如吞吐日月的“天狗”,在烈火中更生的“凤凰”,其“开端在地下,结局在天上”的神奇想象,令人倾倒。诗人在五四革命激情冲击下,神思飞扬,他张扬着想象的翅膀,翱翔于太空、穹苍,将强烈饱满的情绪纳入神话传说故事的框架中,创造出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如诗人借凤凰涅槃的情境为舞台,以火中凤凰为化身,来尽情抒发自己的感情,使难以捉摸的情绪得以成型表达(《凤凰涅槃》);又如诗人自诩为“天狗”,唯天狗是威,是能,是力,展现出一幅奇特的画面(《天狗》)。特别在以古代神话和传说为题材的诗篇里,诗人不是拘泥于历史材料(事实),而是通过大胆的艺术想象和夸张,用时代精神和主观想象加以酿造和丰富,诗中的英雄人物都带有诗人理想化的色彩,他们已不是古代社会的英雄,而是五四时期高唱赞歌的勇士。郭诗那奔放不羁、纵横驰骋的想象力,也正好表现了五四时期那冲击一切丑恶事物、推倒一切腐朽势力的力量。
郭沫若把奇特的想象弥漫于他的一切诗篇之上,使人感到无处不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和生命的活力。这是因为郭沫若的泛神论不仅强调“我即是神”,而且因其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把宇宙万事万物都看成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东西。所谓“一切生命都是Energy的交流,宇宙全体只是个Energy的交流”。“Energy的发散便是创造,便是广义的文学。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13)]因此他的诗中“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光海》),使你感到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生气勃勃,充满了生命的跃动感,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同时,郭沫若诗的想象是那样漫无边际,但并不让人感到空泛无味。这与郭沫若创作“以哲理做骨子有关”。宗白华最早看出了郭沫若诗歌的这种特色,1920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道:“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很深。不象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14)]郭沫若用哲学家的智慧、哲学家的胸怀去把握自然,乃至整个宇宙,这就使他的诗的想象有一种哲学的“冥想”的意味。正因为有了这种哲学的冥想,他那无拘无束的想象才不致于流于空洞和肤浅。
中国新诗诞生以来,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艺术想象力的匮乏,初期白话诗的“非诗化”倾向的形成,与此有关。到了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诗人们开始重视想象在新诗中的作用,新诗的“诗”性因素随之增强了。但是,很多诗人善于想象的诗篇大都是从现实的景物、场面的描写中联想开去,从具体的事物中推出遐想,因而他们的这种想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朴实的特点,不同于郭沫若善于以古鉴今,用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题材驰骋想象,具有“通古今而观之”的特点。郭沫若通过非凡的想象使诗歌获得了极大的艺术力量和艺术自由,诗中那些经过夸张、扭曲、变形的形象。在读者心中唤起了真实而强烈的感情。郭诗那富于情感和想象的诗篇,虽不能说在外国诗中没有,但却是中国诗史所无,而为郭沫若所独具的,它犹如希腊神话一般具有永久不可复现的美学价值。因郭沫若的努力创造,中国新诗开始装上想象的翅膀,开始超越经验的时空而达于诗的境地。由此,中国新诗的质素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六、郭沫若的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色调,而象征则是其精义。他把象征纳入浪漫主义的总体框架中,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扩大了诗歌的精神内涵。郭诗的巨大艺术魅力,与此有关。
郭沫若的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导,同时也与现代主义有若干的联系。他曾对表现主义很感兴趣,但从总的情况看,他对西方表现主义,除了情绪上的感应外,对其艺术和美学的把握则不充分,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虽然没有象浪漫主义那样在其思想和艺术上达到身心交融的境地,但在他的创作中却是占有相当比重的;他把象征纳入浪漫主义的总体框架中,使诗歌显示出了独异的精神风采。
在《女神》的很多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样把激情、想象、联想与象征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以致很难对它们作出具体细致的区分。可以说,在郭沫若富于激情与想象的诗篇中,几乎都有象征的意义在,或象征某种精神,或象征某种情感,或象征某种意愿。《凤凰涅槃》这首诗是象征诗,而且还带着神秘的色彩。。“涅槃”是佛家言,谓和尚死后,形骸化灭,神识永生,意指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郭诗题为《凤凰涅槃”》,大概是取其类比之意。诗人把象征与狂幻想的激情、奇丽的联想结合起来,构成了象征“美的中国”再生的神话的诗。长诗的《序曲》抒写凤凰集香木燃火、群鸟飞来观葬的神话仪式;继之以凤和凰的对唱和同歌,发出了诅骂天地的悲愤之音。诅骂宇宙间“冷淡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中“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凤歌思考着空间,凰歌思考着时间,双双叩响着生命与存在,有限与无限,永恒与刹那。再接着《群鸟歌》展示了对宇宙人生的不同层面的理解,以及精神宇宙的主体性。群鸟对宇宙人生的体认与凤凰处在不同的精神层面,说明凤凰的黑暗、冷酷、荒谬的环境中的自焚行为充满了孤独的悲壮感。但凤凰自焚而更生,是一种超生死界限的大境界,融合着原始人类对火的崇拜和佛学对涅槃”的玄思。火具有不可思议的净化和升华的功能,经过自焚后的凤凰异常鲜美,不再死亡了。在长诗最后的《凤凰更生歌》中,可以看到对佛学“涅槃”意蕴的借喻,即更生的凤凰进入了世间与涅槃“无分别”的境界,因而唱出了“一切的一,和谐。一的一切,和谐”,“一切的一,悠久。一的一切,悠久”一类的和鸣曲了。可以说,“作为《女神》中最宏伟奇丽的中心诗章,《凤凰涅槃》是交融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象征现代中国更生的神话诗”[(15)]。《女神之再生》一诗的象征意义也是很明显的:共工颛顼之争霸,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最后都要灭亡,创造光明(新的中国)有待于诗人的努力。诗中女神象征着诗人;女神们不愿再在壁龛中做神像,象征着诗人不应再住在“象牙之塔”。《天狗》也是含有象征意义的诗。它与《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寄托的意义是相同的,可谓异曲同工。《女神》中的《炉中煤》、《晨安》、《匪徒颂》等诗作以及《星空》、《瓶》、《前茅》中的部分诗作,也具有象征的意蕴。同时,郭沫若还善于运用象征性意象以扩大诗的内蕴和强化诗的情感。在《太阳礼赞》、《金字塔》等诗作中,都贯穿着一个热力无比的太阳意象,它象征着青春、生命、激情、力量。
应当指出,郭沫若诗中所运用的象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象征主义,他对西方象征主义诗艺并没有作过认真研究,而是取其“类比”方式。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真正的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升华过的一个象征的世界”[(16)]。正因为文艺都是“象征的世界”,所以郭沫若在《女神》中几乎是在力求“创造一个类比的大网”[(17)],这个“类比的大网”,并不体现为对象征主义的诗艺(符号)的着意经营,而是体现为对象征精神意蕴的关注与探索。象征主义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以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18)],因而郭沫若虽未专注于对西方象征主义的移植,但由于他的传统诗词的深厚功底,也能使他得其精义。郭沫若的富于象征意味的神话诗,大多是诗人随兴之所至而写成的,“兴”的意味甚浓,从而应证了梁宗岱所谓“象征即兴”的说法。还有一些象征意义的诗,是诗人在自然现象面前感受着某些情绪,而把这些情绪各个具象化,使无生命的自然变成有生命的存在,一切无性变成有性,一切平面变成立体。或者说,诗人以自我为中心,把其主观情绪投射到大自然的物象上去,从而在情绪的流变过程中,让自然物象产生变形,使之具有象征暗示的意味。这类诗无田园牧歌式的描绘与赞叹和推崇自然之美的古典韵味,而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确有某种相通之处。周作人曾经说过:“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义。”[(19)]这话用来评价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可说是恰如其分的。郭沫若把象征融入浪漫主义,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丰富了诗歌的精神内涵。郭诗的巨大艺术魅力,与此有关。
七、郭沫若创造了被称作“女神体”的真正的自由体新诗,充分显示了五四“诗体大解放”的实绩。其实,郭沫若的诗是在为青春的热情寻找着诗的语言和形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以形式手段爆破传统精神的自觉努力。
胡适等人虽然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但其白话诗还是旧文人一套习气的缠绕,带有浓厚的旧诗词的痕迹,中国新诗在蹒跚挪步中迈不开前进的大步。郭沫若《女神》的问世,把旧诗词的限制一扫而光,把一切羁绊统统推倒了,中国诗歌从这里真正得到了解放。郭沫若最厌恶一切阻碍思想情感表达的束缚,强调个性的无拘无束的表现;他要为青春的热情寻找恰当的语言和形式,创造出完全合于自己诗歌内容的崭新的多姿多彩的新形式。他接受了泰戈尔、雪莱、海涅、歌德、惠特曼的影响,特别是惠特曼那“豪放粗暴”的诗对他影响极大,他借鉴外国诗歌的形式,并经过崭新的创造,形成了既有鲜明的独创性又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的新形式。那狂热的感动人心的思想情感,正是通过这种天马行空、狂风扫地般粗犷的自由形式体现出来的。郭沫若自己说:“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罢了。”[(20)] 然而正是这种乱跳乱舞的诗,很好地倾泻出胸中“大波大浪的洪涛”,完美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精神。
郭沫若既为青春的热情寻找着诗的语言和形式,又以形式手段爆破一切旧形式的羁绊及其所负载的传统精神,这就决定了他的诗体的大解放和形式的绝端自由。在创作的时候,他的激情与诗歌形式同化了,或者说的激情与形式对象化了。他以自己的思想情绪支配诗行,以情绪的旋律表现诗的旋律。他不愿局限于一个格局,而是徘徊翱翔在所有叙述性、抒情性、戏剧性的形式之间,来回于散文与诗歌风格之间,突破了那风格之一律的旧原则,诗人以“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力量和气魄去推倒一切旧形式,重建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再也不是一种束缚人们手脚的镣铐,而是自如地抒写自己的激情和想象的自由的形式。从郭沫若开始,新诗不再存在固定的格律规范,诗中的语流随着内在情绪的节奏而起伏;读者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对音韵形式美的品味和感知,而主要是以联想的方式投入情绪的体验,从而获得美的享受。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那“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的理论,即“艺术的自由”的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要求每个诗人都成为他自己,要求每个诗人都冲出狭小的空间,走进广阔的艺术天地,它实际上是想唤起每个诗人的艺术的觉醒。
郭沫若创作的“绝端自由,绝端自主”,使他的诗形成了与精巧、精致适成对照的粗糙、粗砺、粗野的特性。有人将此视作郭诗的缺憾。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作历史的分析。必须看到,在五四新文学的开创时期,还不是特别需要讲究精巧的时期,而是要以一种粗野的东西来与传统对抗。中国古典诗歌够精巧、够圆满、够娴熟的了。郭沫若的诗的“粗野”正是对它的反叛,即不但要以这种“粗野”去对抗旧诗形式的精巧,而且要突破节制情绪宣泄的人为束缚,破坏传统的中和之美的理想,一句话,他的诗正体现了以形式手段爆破传统精神的自觉努力。鲁迅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21)]如果说郭沫若的诗还显示着粗糙的毛病,那也只是“大艺术”的粗糙;如果说郭沫若的诗还存在着“未成品的面貌”,那也只是“天才的未成品”!
闻一多说:“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22)],卞之琳也说,郭诗出现以后,“新诗才真象‘新诗’”[(23)]。事实上,是郭沫若创造了中国真正的新诗。“新诗”能在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的中国出现,无疑是一个真正新奇的事物。说它“新”是名符其实,这不仅表现在一目了然的形式的变异上,还更为深刻地表现在它对陈旧而停滞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和突破上。郭沫若的新诗引入直抒胸臆的西方浪漫主义精神,为中国新诗开拓了主体精神的新天地。郭沫若的意义在于,他以新颖、精炼而成熟的现代新诗语汇洞悉现代人的至深的心灵颤动,决定性地将中国新诗推向成熟;他把古今中外诗歌的诸多有益营养整合在自己创作中,从而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新诗的内涵,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新诗形态;他的多种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开拓创新与结合并用,开辟了现代新诗的广阔道路。他的诗不但在表现时代精神方面达到了最强度,而且在新诗文体的创造性上也是空前的。正如周扬所说:“在诗的魄力和独创性上讲,他简直是卓然独步的。”[(24)]他的诗既具有破旧立新的精神内涵,又具有破旧立新的诗学意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真正实现了中国新诗的第一次伟大的综合。他以辉煌的创作业绩,越居五四时期的一切诗人之上。他所开拓的诗歌精神与诗歌形式对中国新诗坛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的诗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有时太注重“自然流露”,过分地让主观情感放纵;为求独创,有时流为奇异;有时过多地采用外国字词,存在“过于欧化”倾向,……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美,表现出某些不成熟性甚至幼稚的毛病。特别是当我们对郭诗粗糙与粗野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肯定时,还须冷静地看到,这种“粗野”从另一层面上讲也是一种缺陷,它对郭诗的艺术性具有潜在的危害性;由于郭诗这种粗野的形式与表现五四时代精神的内容有一定的协调性,因而它的危害性在当时并不显得怎么突出。郭沫若后来不但没有注意用艺术的雅致去修正和规范这种粗野,而且还让这种粗糙更加任性“放肆”下去,结果诗越写越粗陋和粗暴,以致等同于标语口号,他在2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所写的自由诗离“诗”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在确认郭诗粗野形式的历史进步性时,也不能不看到它的潜在危机。但作为继胡适之后的新诗坛的领潮人,郭沫若对新诗的深入试验与创造,使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其功绩是显赫的。他的诗,无疑是横跨中外古今艺术交汇点上的一座耀眼的丰碑;是中国新诗人高起点追求的一个显著标志。
注释:
①参考孙晨:《试论“创造诗派”》,《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3期。② (11) (14)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③转引自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④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⑤冯至:《我读〈女神〉的时候》,《诗刊》1959年4期。⑥ ⑦ (24)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⑧郭沫若:《女神·立在地球边上放号》。⑨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1957年《诗刊》第1期。⑩借用梁任公:《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2)郭沫若:《序我的诗》。(13)郭沫若:《生命的文学》,1920年2月23日《学灯》。(15)杨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新文学史料》1994年5月30日。(16)郭沫若:《文艺论集·批评与梦》。(17)郭沫若:《文艺论集·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18) (19)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第81期,1926年5月30日。(20)郭沫若:《文艺论集·序诗三札》。(21)鲁迅:《坟·论睁了眼看》。(22)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第4号。(23)卞之琳:《新诗与西方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