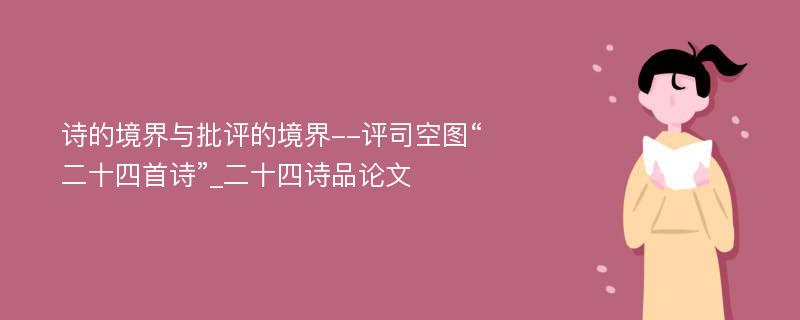
诗歌的境界与批评的境界——重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界论文,二十四论文,司空论文,诗歌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57(2002)03-0027-03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是晚唐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
晚唐社会,政治黑暗,社会板荡,唐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大厦将倾,前途无望,文人士大夫普遍感到颓唐与消沉,对个人与国家的命运都不再抱什么幻想,文学思潮由中唐的注重社会功用、表现民生疾苦,转变为偏于个人抒情、追求艺术之美。司空图早年本是颇有一番济世安民理想的,但在仕途上几经痛苦挣扎后,最终一事无成。绝望之下,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初衷,隐居于中条山王官谷,过起了饮酒赋诗、啸傲林泉的隐逸生活。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宁静,司空图企图从佛老思想中去找出路。他在《自诫》一诗中说:“众人皆察察,而我独昏昏。取信于老氏,大辩欲讷言。”他并不想置身于现实之外,但又不得不超脱于现实之外。司空图晚年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渡过的。现实既然已无任何希望,山水田园与诗酒琴棋就成了司空图心灵的栖息地,他希望在诗歌中创造一个淡泊超脱的佛老精神境界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并不指望以诗歌来经世治国,正如他在《白菊》诗中所说:“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著不平。”司空图的诗淡泊优美,空灵清新,富有禅趣,与王维晚年的诗风接近。由于在审美旨趣上的相近,在精神境界上的类似,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更多地是针对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而言的,同时也是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表明了他个人对于诗歌写作的审美理想。
一
清代性灵说的代表袁枚仿《诗品》作了《续诗品》,他在序中说他很喜欢《诗品》,但“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故为若干首续之。清代另一位批评家孙联奎在《诗品臆说》中也认为“《诗品》意在摹神取象”。尽管《诗品》偶尔也涉及到诗歌创作的具体写作原则,但重点还是放在对诗境的描绘上,而且这二十四种不同的诗境在思想内核与艺术表现上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是佛老的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在隽永、含蓄、自然淡泊的诗境中的体现。
纵观整部《诗品》,司空图更多地还是强调内心修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最完美的诗歌是自然而然从高人逸士的内心世界中流淌出来的,它不能强求,无法强求。当高人逸士真正超脱于世事纷扰与名缰利锁之上,真正达到与自然元气、天地之道的和谐共振时,他就会创造出与生气勃勃、清新秀美的大自然妙合为一的诗境。这一切的关键不在于诗人对写诗的技巧如何孜孜以求、苦心孤诣,而在于诗人的内心境界与风神气质,在于诗人是否具有一种虚静恬淡、超尘拔俗的精神品格,在于诗人同自然造化的契合程度。苏轼有首诗曾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司空图要求诗人的也是这两点:一要宁静淡泊,二要摈弃机心,以容纳宇宙天地精神。
在司空图,写诗的真正目的并不在诗歌本身。对许多中国古代文人而言,尤其是对深受佛老思想影响的诗人而言,写诗是用文字构筑一个虚拟的“世外桃园”与清净乐土,而隐居山水田园则是实实在在地从名利场中抽身而出,在自然山水之中找到真实的精神避难所。隐逸山林与诗酒自娱,成了历代中国诗人寻求精神慰藉与心理平衡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放弃了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的确是比较消极的一种人生态度,但对于一位诗人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诗人忘却红尘、摈弃机心、回归自然时,空寂宁静的心灵对于万事万物才会有深刻的观察与体认,才能潜心进入自然之道的深处,直观把握天地万物内在的玄机。这样一位与自然相契、与造化合一的诗人,在静默之中深深领悟了天道的奥妙,当他写诗作文,诗歌的境界自然也就与造化妙合、与天地浑然一体,没有一点人为造作的痕迹。
既然司空图主张诗人内心世界的了无机心,而对诗歌艺术技巧做苦心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机心”,所以,司空图在很多时候是反对写作中的刻意与苦心的,认为孜孜以求的东西是不自然的,这种不自然会妨害诗歌达到更高境界。比如,在“雄浑”一品中,司空图指出,诗人要获得雄浑之境,必须超脱,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越过具体事物把握事物的实质、把握万事万物内在的不变的根本,而这一切又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不可强求,即所谓“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冲淡”一品说,“遇之匪深,既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一切都是冲淡无痕的,无法刻意追求,也没有形迹可以把握,如果有心去追求冲淡平和、优游从容的境界,倒是愈骛愈远了。在“高古”一品中,末四句说,“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说明“高古”的诗应含思深远,且无迹可求。“典雅”一品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同样强调典雅的艺术风格来自于一种典雅淡泊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修养。“绮丽”一品末四句云,“金樽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殚美襟”,写出了高人雅士对绮丽景象淡然处之的态度。在司空图看来,哪怕是“绮丽”的艺术风格,也来自于人与自然美景的融洽契合,来自于一种淡泊怡然的心境,浓妆艳抹算不得真正的绮丽,没有高人雅士的淡然情怀,刻意制造出来的绮丽就成了粗俗。“自然”一品云,“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得易贫”,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不能强求,无法强求。末尾四句,“幽人空山,过水采萍,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空谷中的幽人,本无意采萍,只因过水而随意采之,幽人能悟解运行不息的自然之道,所以他的行动是自然而然的。由此看来,司空图所说的艺术风格上的“自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要从根本入手,靠内心的修炼与个人的感悟直观地把握自然之道的奥妙,才能真正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实境”一品末四句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要创造“实境”的意境,仍然要顺乎天性与自然,勉强不得,做作不得,它是诗人情性的自然流露,是天籁与诗心的自然契合,可遇而不可求。
在《诗品》中,司空图也谈到过一些重要的写作原则。比如“含蓄”一品,末尾四句,谈的就是“含蓄”的技巧。“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诗人对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只有取其精华,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才有“含蓄”的美。以少胜多,由此及彼,以有限来暗示无限,这是对艺术技巧的重要要求,更是创造“含蓄”美的前提条件。但即使是偶尔谈及写作原则与艺术技巧,司空图也并没有把它细化、具体化。以四言诗这种简约的形式来探讨文学艺术问题,如果花大量的篇幅来论述文学创作方法的具体细节,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何况,文学的生命来自于它的创造性,文学创作绝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法与规则,根据某种教条制作出来的诗歌只能是文字垃圾而已。司空图不去谈具体的写作方法,是他的聪明。具体的写作技巧当然是可以探究的,中国古代各式各样的诗话就花了大量的功夫来探讨诗歌的具体创作方法,这对于人们更好地品味与欣赏诗歌的深长韵致、感受诗歌的艺术魅力是极有禅益的。但当某种具体的写作方法僵化固定为一种写作的路数与教条时,它就会异化成制约文学发展与创新的枷锁。司空图不谈具体的写作方法,出自于他尊重自然天性、崇尚淡泊无为的哲学主张,出自于他对一切“机心”的不屑,同时也出自于他对于文学的自发性、创造性的深深理解。文学的根本来自于诗人内心世界的景象,技巧只是为了把现实人生与内心世界的风景更完美、更忠实地表现出来,文学上的具体技巧,如果脱离了诗人的风神气质与高洁超拔的内心世界,它就毫无意义。因此,司空图在《诗品》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种种诗境,同时也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他理想中的诗人应有的风神气质、精神境界,惟独对于具体的写作技巧几乎略去不谈,他所做的,只是拈花微笑而已,个中玄机,还要靠读者自己的悟性去体会把握。
二
司空图在《诗品》里靠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创造了一幅幅清新优美、空灵超脱或雄浑悲慨的画面,借此来比拟各种不同的诗歌意韵与诗人的内心品格。他理想中的畸人幽人、高人雅士与美丽的大自然一起成为这立体画面的主体,共同传达出作者对不同艺术风格的诗歌意境的细腻体会与深刻理解。
司空图创造的这些画面,完美地体现了人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他笔下的畸人高人幽人,是生机灵动的大自然有机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笔下的大自然,则又成为高人畸人幽人精神世界的生动象征,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纤秾”一品中,作者用了三分之二的笔墨描绘“纤秾”的意境,“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荫路曲,流莺比邻。”这真是一派生气盎然、活泼明丽的春天景象,读者在司空图的引导下,不知不觉间便走入了大自然的深处,在美丽的自然风景里,忘怀了尘世的污浊纷扰,进入一种清明平和、愉快宁静的天人合一境界。诗歌的意境与韵致,是无法用语言明确加以定义的,其中种种微妙的滋味大多只可意会无法言传,所以只能通过巧妙的比喻来加以暗示而已。在这种情形下,特别要求批评家发挥语言丰富的暗示功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的想象力来突破语言的局限性,力求完整地表达出批评家对于文学风格与文学意境的细致理解。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及《诗品》时曾说,“的确,提示各种境界是需要比喻的,尤其是文学上的境界,离了比喻便很难提示,怪不得司空图以此为不二法门了”。
人类情感和思维的很多角落,语言与文字都面临无所作为的尴尬。如何突破语言的局限性表达更为深邃的思想与情感,成为人类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司空图通过一系列比喻创造出一个个可供读者倘佯其间的立体空间,使各种诗歌的意境幻化为呼之欲出的活的画面,通过这些画面来暗示自己的艺术思想。中国绘画与中国诗歌都讲究对空白的处理,讲究留下广阔的艺术空间供读者自由联想,使艺术品成为艺术家与欣赏者共同的创造物。司空图笔下这一幅幅生机灵动的有机画面,以其内在的活力不断地刺激着读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人生阅历来补充空白处的细节,来赋予画面以新的意义与内涵。即使我们不去思考司空图《诗品》的理论价值,我们也会从它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中得到充分的满足。如“典雅”一品云,“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沉著”一品云:“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绮丽”一品云:“露余山青,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豪放”一品云:“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清奇一品云:“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悲慨一品云:“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旷达一品云:“何如樽酒,日往烟萝,花复茅屋,疏雨相过。”这些诗句,让我们步入了中国山水诗画的艺术长廊,步入了高人逸士淡泊宁静的内心世界,与司空图一起分享大自然的美、艺术的美以及远离人世的隐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闲情逸致、优雅品味。从司空图对各种诗境的描写中,读者不仅获得了对于不同艺术风格的强烈感受,而且也直观地感性地把握了在艺术风格背后,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他的风神气质、内心品格以及对于生活的理想。由于司空图的引导,读者对艺术风格的理解不会走向孤立与片面,他会从诗人的日常生活、个人气质、宇宙观与人生观等多方面来理解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同时,这种理解始终与活跃飞扬的想象、醉人心魄的审美快感联系在一起,这一切使得这种理解有可能深入到文字只能暗示却无法企及的部分。
用比喻的方法来进行文学批评,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东晋诗人汤惠休曾说:“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诗如错彩镂金。”颜延之曾问鲍照,己诗与谢灵运诗的优劣,鲍照云:“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到了唐朝,这种以比喻来品题文学的方法更为盛行。比如中唐皇甫湜的《谕业》一文,通篇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评价当朝之士的文章优劣,比如他说:“独孤尚书之文,如危峰绝壁,寄倚霄汉,长松怪石,倾倒溪壑;然而略无和畅,雅德者避之。杨崖州之文,如长桥新构,铁骑夜渡,雄震威厉,动心骇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权文公之文,如朱门大第,而气势雄敞,廊庑廪厩,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规胜概,令人竦观。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诸灌溉,或爽于用。李襄阳之文,如燕市夜鸿,华亭晓鹤,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鲜,悠然高远。”晚唐的杜牧在赞美李贺的诗歌时,用的也是一连串精妙的比喻:“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园陊殿,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用比喻的方式来暗示自己对于文学问题的看法,应该说是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从老庄开始,道家哲学就持“言不尽意”论。到了六朝时期,道家思想与外来的佛老思想及本土的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发展为更具思辨色彩的玄学。魏晋玄学进一步发挥了言不尽意、意在言表的思想,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语言对思想的暗示作用。既然语言无力表现人类思想与情感的全部,那么,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暗示与象征功能,通过刺激读者的想象力,让读者通过联想与感悟,以有限的语言为出发点去体会无限的境界,便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文学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讲究味外味、景外景,文学批评相应地也要讲究意韵深长、余音袅袅,要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供读者回味。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不喜欢长篇大论的分析举证、逻辑推理,不喜欢把一个问题说得过于清楚与直白,而是有意识地惜墨如金,留下广阔的余地与空间,供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正式地在文学批评理论中探讨文学风格问题起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诗歌欲丽”的看法。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应有什么样的风格论述得更为详尽。在风格论的初期,批评家一般是用几个形容词为某种艺术风格定性。到了南北朝时期,品评人物、品评艺术、品评山水成为一时的风尚,对于文学风格的品评也随之细腻精致起来,用比喻的方式品评文章开始成为风气。精妙的比喻比起单纯地用形容词来界定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自然给了让读者更为开阔的想象空间,从客观上刺激了读者的参与热情,激发了读者的创造力,增加了批评的活力与弹性。到了司空图的《诗品》,作者为读者创造的是一幅幅立体的有机画面,它们所暗示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平面的单一的比喻。在充分满足读者的审美快感的同时,这些立体的画面更为有力地刺激了读者的想象力,更为有效地暗示了作者的思想与感受。由于司空图创造的是一种极具生命活力的流动的画面,它的外延是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是万古长存的自然玄机,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补充司空图的思想,来丰富与刷新他对于文学风格的看法,这赋予了司空图的理论以自我更新的能力。当然,这并不是说,司空图的思想缺乏质的规定性,缺乏明确的意图和独特的见解。实际上,司空图对人生与文学的见解,对于宇宙自然之道的见解,在篇幅并不算长的《诗品》里我们已经有了鲜明的印象。作为一位批评家,司空图的不同是,他尊重读者的感受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让读者参与到他的内心世界中来,分享他对于文学与人生的感受。在字字珠玑的《诗品》引导下,读者和司空图一起,不知不觉走进了高人逸士的内心世界,走进了宁静而活跃的大自然怀抱,共同品味那悠然忘我、泯然物化的境界。这是道的境界、诗歌的境界,也是批评的境界。
收稿日期:2001-12-05
标签:二十四诗品论文; 诗歌论文; 司空图论文; 文学论文; 诗品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