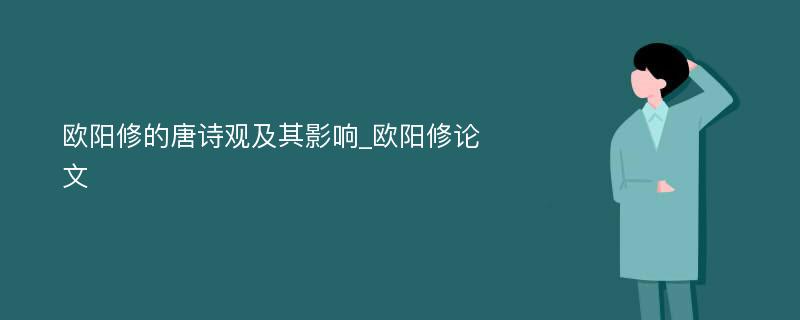
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欧阳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阐述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其对北宋诗学的影响。认为欧阳修推崇韩愈及中晚唐诗的用意在于抵制西昆习尚,开创一代新风;又认为欧阳修推崇李杜诗歌,但并无扬李抑杜之说,后人以为欧阳修将李杜分出优劣,是不符合欧阳修本意的。欧阳修的唐诗观并不全面和系统,但对北宋诗学起到引导的作用,滋养了一代的诗歌学者。
关键词 唐诗观 推崇韩诗 李杜并赞
欧阳修是北宋前期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北宋去唐未远,人们对唐诗的接受比起后代来要亲切些。但唐诗学自唐至宋,为时不久,还处在开创阶段,远不及后来的丰富和成熟。欧阳修是这个时期的文坛泰斗,无论从哪方面看,他对前人的辉煌文学遗产——唐诗,自有其学习、吸收的必要,自然也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以当时已经出现的文学批评的状况看,直感式的认识、点评式的表达乃是最时行的。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笔说》、《试笔》及诗文、书简等就以时行的方式保存了对唐诗的见解、批评,虽然不系统也不全面的,但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客观上为后人认识北宋前期的唐诗学实际状况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一
欧阳修关于唐诗的见解,最鲜明的一条是对中晚唐诗人尤其是韩愈诗歌的推崇。这方面的例子主要有:
(一)在他晚年最后的著作《六一诗话》中,他肯定了韩愈: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
(二)他的《菱溪大石》一诗,描写了从幽谷里运来的一块“惊可怪”、“奇嶙峋”的大石,经过处理,把它作为难得的观赏石。于是,颇有感慨地说:
嗟予有口莫能辨,叹息但以两手扪。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
卢仝的诗,在险怪方面,与韩愈的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欧阳修自认比不上他们。
(三)除了卢仝之外,他认为孟郊的诗也有与韩愈相类似的雄健的风格。《读蟠桃诗寄子美》写道:
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凰。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发生一为宫,揫敛一为商,二律虽不同,合奏乃锵锵。天之产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
意思是说,韩愈与孟郊才力相匹,写起联句诗来,奇特和谐,有如凤凰和鸣。二人的诗一为穷苦,一为浩富,各有特点。而“雄力”“奇怪”则是“寂寥二百年”来所罕见,于是直觉认为二人的诗是“至宝”。
(四)在《试笔》(《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中,他肯定了孟郊、贾岛,认为他们“名称高于当世”。又说: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韩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五)在《六一诗话》中,他粗线条地评价了晚唐的诗,说: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又具体地称赞某些诗人。如:
他肯定了周朴,认为周朴的诗“构思尤艰,每有所得,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
他评价了郑谷,说“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他提到了王建:说“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传得滕王《峡蝶图》。’……唐时一艺之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弹琵琶,米嘉荣歌,皆见于唐贤诗句,遂知名于后世。”这里,他既指出王建写作宫词的基本内容,又无意中道出了唐诗有反映当时艺人技艺的内容。对后人认识唐诗不无启发意义。
(六)在他的《读李集效其体》诗中,在描写了李白天马行空的豪爽风貌之后,用孟郊和贾岛的拘谨和寒涩作对比,说“下视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表明他对孟郊和贾岛的诗歌的评价与对郑谷诗歌的评价一样,是有褒有贬的。
此外,欧阳修在自己的一些诗篇中,还标明效孟郊、贾岛、李贺、王建体,以及效韩孟联句体。
从现存资料看,欧阳修对中晚唐诗人的评点,比对初盛唐诗人的评点要多。我们当然不能由此断定他对中晚唐诗人比对初盛唐诗人有兴趣,但我们却可以由此看出他对中晚唐诗人并不轻视。在唐诗学史上,欧阳修时代还未有“四唐”说,也未有“诗必盛唐”的极端之论,更没有宗唐宗宋之争,但在诗坛上已经出现了影响颇大的西昆派,所谓“刘杨风彩,耸动天下”(《四库全书总目》“西昆酬唱集”条引),他们标傍以晚唐李商隐的诗为宗。在这样的情况下,欧阳修上述的唐诗观就颇可发人深省。
欧阳修对中晚唐诗人颇多兴趣,却对晚唐重要诗人李商隐不置一词,这是为什么呢?从现有的材料看,这是与他对西昆派的态度有关的。当他步入文坛的时候,西昆派的主要人物杨忆、钱惟演刚刚谢世,刘筠可能还健在。他对三人的诗颇多赞赏,一方面是三人的诗确有一些警绝之句,如他在《六一诗话》中举出的杨忆的“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钱惟演的“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等,确是可令人效法的;一方面也因为作为后辈,欧阳修曾得到钱惟演等人的奖掖和推重,在个人感情上,便对他们产生好感。但由于“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六一诗话》)。对于诗坛的这种偏颇,欧阳修心有不满。尽管他说这并不是西昆派的责任,而是学者之弊,即后进学者的责任,但他也无意为“昆体”辨说。他不主张以“昆体”为榜样,但又不像王禹偁那样深致感慨。(王诗《还扬州许书记家集》有云:“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因此回避了对刘、杨所推崇的李商隐的诗的评说,而在实际创作中,却远离李商隐,更远离“昆体”,而另出新境。叶梦得认为:“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石林诗话》卷上)
至于推崇韩愈的工于用韵,就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是韩愈在创作雄健诗歌时,往往不受诗韵常格的拘束,即“波澜横溢,泛入旁韵”。欧阳修对此已经有了感性的认识。正如叶梦得所说:“欧阳文忠公……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石林诗话》卷上)另一种是韩愈在使用“窄韵”时,能“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这其中多少有炫耀学识的味道。这种诗风,正适合作为学问家和诗人欧阳修的口味,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在称赞刘、杨诸人的佳句之后,就称赞他们“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可见,他对韩愈在诗中时有逞才的表现不仅不反感,而且颇为赞赏。韩诗的这一点,为欧阳修和北宋有影响的诗人所接受,好逞才,多议论,成了宋诗一大特色。后人多认为这是作诗的弊端。就宋代而言,其始作俑者,非欧阳修莫属。
欧阳修对韩愈诗歌情有独钟,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在《梅圣俞墓志铭》中称赞梅圣俞的诗,说:
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至于它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
以梅圣俞诗的琢刻、怪巧、老劲为是,以“唐诸子号诗人者”之“僻固狭陋”为非。而所谓“唐诸子号诗人者”究何所指呢?他在《书梅圣俞稿后》中曾说:“诗者乐之苗裔与!唐之时,子昂、李、杜、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由此可见,他所不满的主要是晚唐以来的诗风。尤其是当时后学者争效之,使风雅一变的“昆体”。虽然他极力称赞梅圣俞和苏子美,说“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但苏、梅毕竟难挽诗坛颓波。因此,欧阳修独标韩愈诗风。其深刻的含意,可以认为是以之与西昆派的独标李商隐对抗;假如从韩愈的诗风是在李白、杜甫之后另辟新途这个角度看,则其包含的意义还在于“有意别创新裁以与唐诗立异”(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引言》),也即倡导开创宋诗新路。钱钟书先生说,“他……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宋诗选注》)
如果我们联系一下宋代诗坛的演变,就不难看到欧阳修上述的唐诗观曾滋养了同时代的后学者。众所周知,在他之后,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地受着韩愈诗歌的影响:宏观方面的影响是勇于创新,另辟坦途;微观方面的影响是工于用韵、逞才议论以至意象的构思、语言的运用等。而在对韩愈诗歌的历史评价方面,苏轼充分肯定韩愈在盛唐之后变革诗风的巨大意义(参见拙文《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这个结论的获得,与欧阳修对韩愈的推崇有关。
北宋中后期出现了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的舆论,随之出现了对中晚唐诗的贬抑。并且余风延及南宋。而到了南宋,除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在批判江西诗派时,又重新举起晚唐(主要是贾岛)的旗帜之外,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也颇欣赏晚唐,他的《读笠泽丛书》写道:“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其中的“近日诗人”即指江西派中人。这种复杂交替的现象,除了诗人宗派情绪的因素之外,应该说,与对晚唐诗本身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当历史远离了唐宋时期,人们与唐代有了更大的距离之后,客观地评价唐诗,就得出无可争议的结论:中晚唐诗歌当然比不上盛唐,但中唐之响与晚唐之韵自是唐诗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成就也不容抹煞。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说:“我论唐诗怒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虽是话中有话,但中晚唐诗人的作品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与杨万里却是所见略同。至于晚唐的贾岛,在宋代反复被人推崇,其深刻的原因,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正在苦闷中,贾岛来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惊喜得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唐诗杂论·贾岛》)而这一点,早在唐诗学的初始期,就已经为欧阳修所点破了。虽然欧阳修并未如后来人说得那么中肯和透彻。
二
欧阳修对唐诗的双子星座——李白和杜甫的诗应该说是颇下功夫研读的。《六一诗话》有一则: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
由此可见研读的精细,但对李杜的点评文字并不多。虽然如此,却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李白和杜甫诗歌的高度评价。最突出的例子有二:
一是他用李杜来比苏舜钦(子美)和梅尧臣(圣俞),从而充分肯定苏梅在宋初诗坛的地位与影响。《感二子》诗:
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鸣凤不再鸣。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寞收雷声。百虫坏户不启蛰,万木逢春不发萌。岂无百鸟解言语,喧啾终日无人听。二子精思极授抉,天地鬼神无遁情。及其放笔骋豪俊,笔下万物生光荣。古人谓此觑天巧,命短疑为天公憎。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皇世所惊。……
据资料所载,欧阳修对苏舜钦和梅尧臣是极其崇敬的,用李杜来比况他们的时候,又把李杜比为并世的麒麟与凤凰,可见对李杜的崇高赞美。
二是在提到晚唐诗的时候,拿李杜诗做对比:“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话中对李杜诗歌的豪放风格十分赞赏。据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载:欧阳修的儿子棐曾请书法家张子厚书写欧阳修的《明妃曲》和《庐山高》诗,说:“先公平日,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我能之也。’”可见,在欧阳修的心目中,李杜是诗中圣手。
但中唐以来,文人中有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偏见,于是也有人错会了欧阳修的意思,将欧阳修下列一段文字加上“李白杜甫诗优劣说”的标题。这段文字是: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 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这段文字见诸《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二十九《笔说》。《四库全书总目》“文忠集”条认为:该集惟前五十集(“居士集”)为欧阳修晚年自编,其余皆出自后人之手。而后人对欧阳修诗歌的评价多受苏轼的影响。苏轼所写《居士集序》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说欧阳修诗赋似李白,这是过誉之词。欧阳修的诗,当然有李白的影响,但并不明显。李诗奇丽,欧诗清淡,很难说相似。就上引《笔说》的这段文字看,着重点虽然是在赞扬李诗的豪迈奔放,认为杜甫在这方面不能企及,但又说杜甫“精强过之”。显然,文意是各有褒扬的,但绝不是对李杜诗的总体上的褒贬。而《笔说》的搜集者加上的标题却容易使人误解为欧阳修在扬李抑杜。类似的说法还有:
欧公亦不甚喜杜诗……欧贵韩(愈)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卓飞扬为感动也。(刘攽《中山诗话》)
这种说法,当时已经有人表示不可理解。陈师道说:
欧阳永叔不好杜诗……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后山诗话》)
对这种说法,宋代已有人为之辨正:
世谓六一居士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观《六一诗话》于杜诗既称其虽一字人不能到,又称其格之豪放……岂可谓六一不好之乎?后人之言,未可信也。(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
这里,提到了《六一诗话》中这样一段话:
陈舍人从易……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这其中,流露了对杜诗的赞美。
当然,欧阳修对李白的诗是很喜欢的。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就指出:“欧阳公喜太白诗”。又说:“欧阳公学退之,又学李太白。”正因此,他对李白的豪迈奔放的赞扬,还不止上面一例。在《读李集效其体》诗中,还写道: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
又如《赠王介甫》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称赞王安石有李白的诗才和韩愈的文才,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李白的礼赞。但以上诸例并不涉及对杜甫的评价。更不能认为是对李杜的优劣之评。何况,欧阳修在别的地方也单独称赞过杜甫,如《堂中画象探得杜子美》诗:
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敬可垂后,士无羞贱贫。
人们当然也不能以为这是暗中贬低李白。总之,在欧阳修看来,既可以“李杜”并赞,也可以分开来,李、杜独赞。
李杜被认为是唐诗发展的顶峰,那是以后的事。沈德潜说:“唐人选唐诗,多不及李杜。”(《唐诗别裁集·凡例》)确实如此。殷璠《河岳英灵集》专选盛唐之诗,却只收李诗而不收杜诗;成书于天宝年间的《国秀集》,收入85位诗人的诗,竟无李杜;韦觳《才调集》收诗一千首,却无杜诗;直至北宋初年姚铉编《唐文粹》只收杜诗10篇而不收李诗。由于当时西昆行时,后学者多效之,以至“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1036年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就披露: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而宋初时仅存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直到1059年,王琪重新编辑杜甫诗集的时候,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王琪在刊后本中云:“近世学者争言杜诗,爱之深者至剽掠句语迨所用险字而厝画之,沛然自以绝洪流而穷深源矣,又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余篇,少数十句,藏弆矜大,复自为有得。”(转引自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第 109页)南宋叶适在说到宋代诗派更迭与纷争时,曾指出“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而江西宗派章焉。 ”(《水心文集》卷十二:《徐斯达文集序》)这种时尚的变化,与当时处于文坛领袖地位的欧阳修对杜甫的推崇不能没有关系。
标签:欧阳修论文; 唐诗论文; 韩愈论文; 李白论文; 宋朝论文; 读书论文; 六一诗话论文; 杜甫论文; 李杜论文; 晚唐论文; 六一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