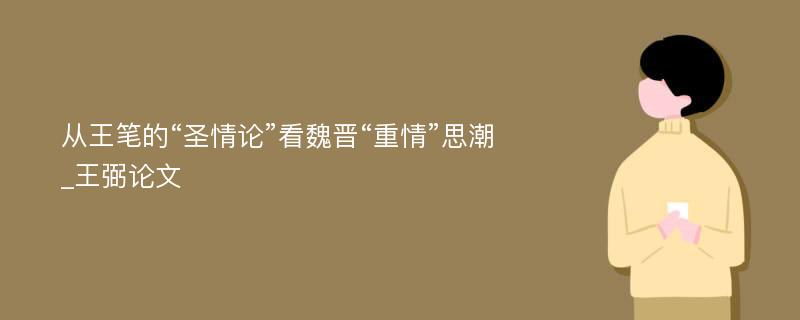
从王弼“圣人有情”说看魏晋时代的“重情”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弼论文,魏晋论文,思潮论文,圣人论文,有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 (1999)02-0018-21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继先秦“百家争鸣”的辉煌之后,能以人生思考和人性探求在士林中蔚成风气而大放异彩的,无疑当首推魏晋时代。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出异乎往代的特殊精神(注: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王弼圣人有情义释》,见《魏晋玄学论稿》。)。虽然“圣人”以“自然”为体、与“道”同极、“无为而不为”的观念是魏晋时代士林的共识,但在“圣人是否可学可至”、是“儒圣”还是“道圣”、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等一系列问题上,人们还是各有取舍、互有争鸣。这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表现。本文无意全面分析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分、同、异、合,只想就王弼提出的“圣人有情”说及其社会影响和文学意蕴作些阐述。
一、王弼“圣人有情”说的含义
王弼提出的“圣人有情”说,是他汇合儒、道的创见,也是他与同时代的何晏等人同中有异的新说。
《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传中又引王弼答荀融书云:
夫明足又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理想人格论既然是魏晋士人的中心问题,则“圣人是否有情”定当成为正始名士清淡的要目之一。从魏晋人立足的思想文化背景来看,孔子虽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也很注重感情的正当表露,但他更注重清除“忧”与“惧”等情绪,落实到伦理生活和人格修养上,他追求的是“内省不疚”(注:《论语·颜渊》。)。随着两汉天人感应、圣德法天思想观念的流行和孔子的神化,“圣人无情而为人伦之至”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被社会普遍接受。墨子也是一个感情极丰富的人。他兼爱天下,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无浓厚的真情实感,必不能如此。但他主张只应发挥兼爱之情,此外的他种情感都有害于事,应予以消除。他把喜、怒、悲、乐、爱、恶称为“六辟”,主张去“六辟”而“用仁义”,只有如此才“必为圣人”。(注:《墨子·贵义》。)关于情,道家创始人老子只讲“无欲”,未言“无情”;庄子则不言“无欲”而言“无情”,极力排斥情为物动。孟子对情的态度,与孔子大致相同,发挥孔子“内省不疚”的人格修养论,主张君子惟务实行道德,遇横逆之来而不动情感(注:《孟子》:《离娄》、《公孙丑》。),提出“不动心”之说(注:《孟子》;《离娄》、《公孙丑》。)。战国末期的荀子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出于“法后王”的政治实用目的,主张“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注:《荀子》:《性恶》、《修身》。),认为惟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情)”(注:《荀子》;《性恶》、《修身》。),虽不讲无情,却主张去情。董仲舒也不主张无情,认为“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注:《春秋繁露·如天之为》。),但他是以阴阳之说区别性情理欲之善恶的。
在董仲舒看来,性为仁,生于阳;情为欲.为贪.生于阴。性善情恶,成了汉代最流行的学说。我们很难想象,据此他们会得出“圣人有情”的结论。因为在那个有意志的天主宰一切的神学时代,被认为“圣德法天”的孔子早已被抽掉五情六欲了。“圣人有情”一直是人们的传统观念。尽管有意志的天道观在汉魏之际受到了桓潭、王充等人的斥破而渐失其势,老庄渐兴而自然天道观遂之日见流行,天道观念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圣德法天、与自然为一、纯理任性而无情的观念,仍然是汉魏之际流行的学说。何晏、钟会等人所持的“圣人无喜怒哀乐”(无情)说,正是当时思想界实际情况的反映。
王弼“圣人有情”说的新见与何晏、钟会等人的意见有同有异。相同点在于,他们作为一代玄宗,都祖述老庄的自然天道观,认为圣人与道合一,“智慧自备”(注:王弼《老子·二章注》、《论语释疑》,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七卷三期。),圣明独厚,故能“寻极幽微”而“无累于物”。相异之处在于,何、钟等人以为“圣人无情”,而王弼则认为“圣人有情”,而有情无情之别则表现在应物与不应物。说圣人无情,是因为圣人纯乎天理,圣明足以寻极幽微,故不以物累;说圣人有情,则是有见于情乃人的“自然之性”,为人格本体之原有部分,它与圣人的“神明”,共同构成“性”之全而“不可革”。何晏因为看到了“凡人任情喜怒,违理”(注:何晏:《景福殿赋》,《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卷三十九。),所以主张“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可谓得庄子之真谛。王弼则从“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注:王弼《老子·二章注》、《论语释疑》,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七卷三期。)的“民之自然”中受到启发,大胆地主张以情应物,做到体用不二,性情为一。因此,他不同意何晏等人因圣人无累“便谓不复应物”,从而去其“自然之性”而认为“圣人无情”的观点。在王弼看来,“情”既然是人的“自然之性”,它感物而动就必然会产生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外在表现。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情与其众多外在表现形式的关系,就是本和末、体和用、静和动、一和多的辩证关系。他的“圣人有情”说,正是把人格本体的“情”与喜怒哀乐等“情之用”结合起来,并引入“感物”、“应物”为中介,作辩证的考察,引导人们去追求“物情通顺,故大道无违”(注:嵇康:《释私论》、《声无哀乐论》。)的人生境界。
由何晏与王弼对圣人是否有“情”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魏晋玄学内在精神的发展趋向。魏晋玄学的圣人人格论,极力提高圣人在“智”、“明”上的优越性。何晏、王弼等玄学领袖也都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足以寻极幽微”。《人物志》的作者刘劭曾给“圣人”下了个定义,认为“圣之为称,明智之极名也”。“智者德之帅。”“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于聪明”。(注:刘勰:《人物志》八观第九及《自序》。)他们都把“智”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应该说,这种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德”为美到魏晋玄学家强调“智”为美的转变,也就是从强调人的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到强调个体智慧才能重要性的转变,并且把人的智慧视作实现道德实践的先决条件——“德之帅”。不同于汉儒神学乌烟瘴气笼罩之下的圣人形象,魏晋人心目中的圣人成了智慧的化身,成了时代注意的中心,而又立足于汉魏之际群雄辈出的现实土壤之上。三国时期的英雄崇拜、才智崇拜成为时代风尚,正是思想界悄然转变的社会心理基础。
魏晋玄学对人的聪明才智的重视和强调,在中国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个体人格研究的新领域,并适应着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王弼的“圣人有情”说,就是在这一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标志着魏晋玄学对人格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展。他不满足于仅仅把“智”从儒家仁义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还一反儒家要求人们“以情从理”、把“情”束缚淹没在烦琐礼法和神学迷雾中的传统,而是把“情”安放在自然人性的位置上,反对否定“情”的价值和割裂人“性之全”,并把主体的“情”与“道”这一无限的本体相统一,提高到无限的人格理想的高度。不是使“情”从“理”或以“理”灭“情”,而是追求“情理兼畅”,这正是魏晋玄学在人格论上区别于传统的最主要的标志。可见,王弼的方向正是魏晋玄学的方向。
二、王弼“圣人有情”说的社会影响
魏晋时代,确是一个高扬个体人格价值的时代,一个重情的时代。正始玄学从人格哲学的高度对“情”的人格价值的论证和肯定,为现实社会中世俗情感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嵇康的行义不屈,阮籍的“歧路恸哭”、陆机的“华亭鹤唳”之叹,以及“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自豪标榜,《世说新语》对“才情”的品题欣赏等等,都足以表现“情”的解放。人们不再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是以“任情背理”、“以情坏法”来张扬自己的人格价值。
“情”的价值一旦被时代哲学确认下来并深入人心之后,它就不仅成了支配士大夫生活的新的伦理价值,而且成了人们解决许多社会现实难题的依据和标准,“以情论理”就是突出的表现。
两晋南朝最重礼学(唐长孺语),一方面是因为世积乱离,旧的礼学传统多遭现实破坏而支离散乱;另一方面,已趋稳定的士族阶层为维护自己的群体纲纪,都需要重建礼学,通过革新旧礼法来安顿新价值,调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情礼之间的冲突。从郭象、向秀为调和这一冲突而共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注:《世说新语·文学》。),到东晋以后玄礼双修学风的兴起,都是这种情势的产物。不仅玄学家兼治礼学,礼学家也在革新礼学,而共有的标准只是一个——“情”。如玄学家谢尚主张“典礼之兴,皆因循情理”(注:《晋书》:《谢尚佳》、《阮籍传》、《嵇康传》。),礼学家则主张“缘情制礼”(注:《通典》卷九十二引曹义语。)等等,类似的言论在《晋书》、《南史》等史籍中几乎随处可见。这说明魏晋以来,人们已把“情”宣扬成了一种最高的社会价值,不但“以情坏法”的社会风气因此而生,礼法本身的因革创制也要以“顺乎人情”为标准了,“即事缘情”于是成了人们处理伦理政制等一切社会问题的新立场和新方法。
同时还应看到,魏晋南朝的“缘情制礼”,不但与先秦两汉儒家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在要求上截然相反,而且在“情”和“礼”的内在含义上,前后也有质的不同。在先儒们看来(特别是汉儒),“情”往往与“人性恶”的观念相表里,是指一己的私情,因而他们更强调“忘”及其对“情”的统摄:“礼”是外在于人的本性而用来束缚、禁锢“情”的,二者的对立性要远远多于统一性。而在魏晋人看来,“情”乃人的自然本性,一切外在于人的典礼之制,皆应顺乎人情,缘情叙情,二者的统一性要远远多于对立性。
总之,魏晋玄学的“圣人有情”论,以“情”乃“自然之性”的观念为核心,空前地重视和提高了“情”在人格本体中的位置和价值,是思想界标志“人的自觉”的一面旗帜。
三、王弼“圣人有情”说与魏晋文学的价值取向
王弼对“情”的价值及其本体意义的肯认和张扬,不但给当时社会的思想、伦理及士人的立身行事奠定了“重情”的哲学依据,同时也给时代的文学开辟了新的价值取向。魏晋文学抒情浪潮的波滚云涌,文学理论批评“以情论文”的新尺度的确立,都离不开对个体感情的高度肯认这一前提。
魏晋文学的“重情”趋向,肇端于“俊才云蒸”的汉末建安时代。曹操对汉末大乱中“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深情叹息,他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襟怀之咏,还有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生命眷恋,无不在反映汉末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的同时,透露出自己昂扬的生命意识和悲凉慷慨的不平激情。“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评王粲语),正是建安群才共同的创作基调。但应该看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风力”,不久就变奏出曹丕《燕歌行》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短歌微吟”,曹植《洛神赋》那流利婉转、华美忧郁的“情心振荡”。尽管这不一定能代表曹氏兄弟的全部创作,但这的确代表了雄浑有力的“建安风骨”向更加婉转切情的魏晋文学的新变,正如沈德潜所说:“孟德诗就是汉音,子恒以下,纯乎魏响。子恒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婉约,能移人情”。(注:沈德潜:《古诗源》卷五。)
到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注:《晋书》:《谢尚佳》、《阮籍传》、《嵇康传》。)的魏晋之际,在阮籍、嵇康等正始作家的笔端,虽因政治的极度黑暗而少了些许婉转清丽,多了比兴、寄托的幽深隐晦,如阮籍的“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嵇康的“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注:钟嵘:《诗品》。),都是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但文学创作中的抒情浪潮并没有因政治的高压而停止,反而被赋予了更强烈的冲击黑暗政治和虚伪礼教的进步力量。应该说,魏晋作家对文学的抒情功能是有自觉认识的。王弼从“情”乃人的“自然之性”的哲学本体论出发,进一步揭示出“喜怒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的心理机制和艺术规律:而嵇、阮等人也正是循着这一方向,对属于客体的“声”(诗)与属于主体的“哀乐”(情)作了严格的区别论证(注:钟嵘:《诗品》。),指出“心之于声,明为二物”,“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他们基于对客观之“声”与主观之“情”的严格区别而建立起来的“声无哀乐论”,既与传统儒家“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的荒谬之论有本质区别,又没有割断诗、乐与情感的联系,第一次向人们申明:哀乐之情出于人心而不在声音,尽管“人情不同,自师所解,则发其所怀”;但只有明乎此(既“声无哀乐”),才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嵇康对主体自身情感状态在艺术活动中重要作用的强调,在两晋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声无哀乐论”成了士林中的“言家口实,如客来之有设”(注:《晋书》:《谢尚佳》、《阮籍传》、《嵇康传》。)了。
从汉末到魏晋的文学流变,“重情”的趋向在晋代以后更加明显。人们在不断感慨“建安风力尽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同时,又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它归罪于社会对“缘情”文学的追求。刘勰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晋虽不文,人才实盛,……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注:嵇康:《释私论》、《声无哀乐论》。)晋代文坛领袖张华,人“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注:钟嵘:《诗品》。);“妙解情理,心识文体”的陆机,只因其揭出“诗缘情”的纲领,人讥其“陆生所知,固魏诗之渣秽耳”(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定势》。);更有人认为晋代文学“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注:纪昀:《云林诗钞序》。)。在封建正统文学史家的笔下,六朝文学的“缘情而绮靡”,历来是被判定为“六朝之弊”的。而现在看来,魏晋文学的创作实绩不但无愧于“缘情”的旗帜,而且也正固此而倍可珍贵。
作为魏晋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结晶而又指导文学创作的魏晋文论,同样也是以“以情论文”表现出最为主要的时代特点。如果说曹丕以“气”(作家的个性气质)论文(作品的整体风格)还更多地带有汉末建安文人志在经国的功利色彩的话,而经过玄风沐浴的魏晋作家如陆机等人,便转而从探讨作文之“用心”来“以情论文”了。陆机把作家的主观感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本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作为自己探讨的中心问题,正是晋代文坛“先情后辞”的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的鲜明体现。“情”与“文”的关系问题也被当时的玄学家时常论及,如“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张华父子“先情后辞”的文学主张,陆机兄弟宗其言而提出“诗缘情”的文学标准,都未必不受当时“缘情致制”、“即事缘情”等普遍社会心理的影响,而与王弼开创的玄学新风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对于二陆文学主张的转变(即由“先辞而后情”到“先情而后辞”的转变),齐梁时代的文论家刘勰有“可谓先迷而后能从善”(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定势》。《南齐书·王僧虔传》。)的赞语,暗示了刘勰本人对“以情论文”的前代传统也是心香供奉、有意薪传的。从“情”和“采”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上来剖析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正是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主要特点。
从王弼对“自然之性”的“情”的张扬,到魏晋社会对这一新的社会价值的自觉追求,再到“即事缘情”、“缘情立制”等社会实践新方法的确立,以及它的社会政制、家庭伦理等社会各层面的广泛应用,还有魏晋社会唯情心理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主张中的主导作用,都是王弼首倡的“圣人有情”说在时代精神中的潜衍化生。
收稿日期:1999-01-02
标签:王弼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国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晋书论文; 诗品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