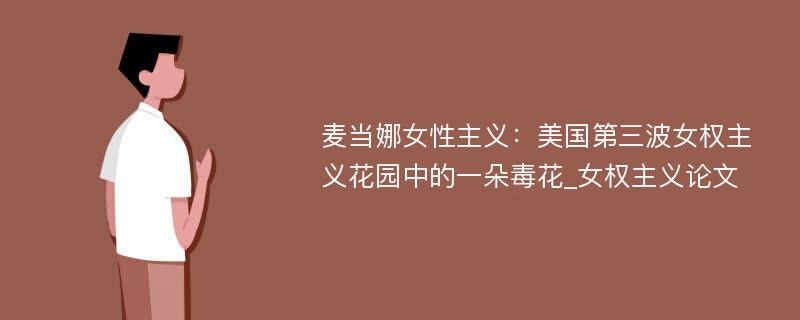
麦当娜女权主义:美国第三波女权主义百花园里的一支毒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百花论文,一支论文,麦当娜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07-09 麦当娜“揭露了永远长不大,总在抱怨的美国女权主义清教徒式的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卡米拉·帕格利亚[1] 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角度看,1990年代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10年之一。在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里根和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随着各种新科技的发明,消费领域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这个10年中还涌现了五光十色的新文化现象。在演艺界,麦当娜以张扬的个性和多变性感的艺术形象横空出世,风靡全球。麦当娜还受到了不少当时兴起的第三波女权主义的推崇,甚至被其中有些人称为“女权主义的将来”[1]。 虽然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宣告的“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凸显了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引领的世界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取得的显著成就,但是具有不断反思传统的西方各种新老女权主义在1990年代对第二波女权主义进行了又一轮的回顾。在学术、媒体、商业和大众视野中,一支“麦当娜女权主义”名噪一时①。这支女权主义虽然内部多元,理论上各持己见,但是都含有4个重要的共识:指责第二波女权主义是“受害者女权主义”;重提性别的生理性、自然性,提出应重建女性气质;强调身体是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关键;如麦当娜一样,认为性是赋权女性的最佳途径。2014年好莱坞电影《消失的女孩儿》(Gone Girl)再现的“坏女孩女权主义”凸显了这支女权主义对当代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 1990年代,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面临的新的社会现实,虽然其表述方式与西方不同,但上述4个层面的议题也逐渐进入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视野。本文回顾那一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特瑞莎·艾伯特(Teresa L.Ebert)和西方一些带有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倾向的女权主义学者对麦当娜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娜奥米·沃尔芙(Naomi Wolf)和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的主要论点、议题、修辞策略和宏观理论框架的评析,希望引起中国妇女研究学界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涉及这4个层面的议题的反思。 一、指责第二波女权主义是“受害者女权主义” 要让年轻人相信她们是受害者,她们从上一辈继承的遗产除了受害别无其他,这实在、实在不是个好主意。 ——卡米拉·帕格利亚[2](P274) 针对1960年代以来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个人生活等层面进行的全面的“女权主义的干预”取得的成就,麦当娜女权主义指出,主流女权主义的理论和运动都基于把女性界定为父权制的受害者的前提。主要表述在沃尔芙的《以火对火》(Fire with Fire)(1993)一书中。在这本著作中,她首先发明了“受害者女权主义”这一概念。在回顾30多年来女权主义运动的成就后,她认为女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然后她强调:“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是抓住这个契机,实现性别平等,还是游离而去,抓住过时的受害者形象不放。”[3](Pxv-xvi)她把受害者女权主义总结为:鼓励女性以受害、被动为荣,把隐名埋姓、自我牺牲和集体思维视为领导力、公众承认和个人成功的关键。帕格利亚进一步指出,女性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过。她认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近30年所做的一切都不外乎抱怨男性。这是一种青少年的心态。主流女权主义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于父权制的理论带有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导致理论上的破产[1]。 艾伯特等人对麦当娜女权主义把女权主义指责为“受害者女权主义”的质疑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她们非常不赞同沃尔芙等人认为女权主义发展近30年后,父权制式微,或根本不存在了的观点。艾伯特以1990年代印度男性通过包办婚姻,在全球大肆贩卖少女学徒工的现实为例强调当代性别压迫不仅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严酷。父权制的一个新的特征是打破了地域的局限,日趋全球化②。艾伯特指出,沃尔芙等人否定父权制的存在实质上是维护现存的对女性的剥削压迫制度,以此否定女性变革社会的必要性[4](P179)。 第二,对第二波女权主义对父权制建构的宏观的认识论不是不能质疑,而是从什么角度以及怎么来质疑。艾伯特等人认为,帕格利亚等人把第二波女权主义建构的有关父权制的系统的宏观认识论指责为清教徒式的说教,实际上涉及要不要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建构对女性受性别压迫的深层的社会根源的认识论。她们认为,沃尔芙在这个议题上的理论框架基于当时西方风行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述的思潮,特别是法国哲学家琼-弗兰斯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其《后现代主义条件》(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一书中用差异、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局部主义来质疑宏大叙述的一统性导致的集权主义。他有句名言:“让我们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一统化。”[5](P82) 艾伯特认为,利奥塔提出这个反对宏大叙述的理论背景是1960~1970年代后殖民主义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深入人心,同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停滞。这些都激发了西方思想界重新从宏观上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背景下,利奥塔质疑的宏大叙述指的是17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建构的推翻封建社会的启蒙主义的叙述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叙述。他认为这两大宏观叙述都已经丧失了可信性[5](P37)。艾伯特指出,根据利奥塔的理论,1960年代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反体制的群众运动中表述的诠释各种压迫性等级制、具有解放意义的宏观认识论,比如第二波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认识论、美国黑人对种族主义的认识论和世界各国殖民地人民对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的认识论都是没有理论根基的[4](P184)。 为此,艾伯特等人特别强调建构对当代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合力剥削和压迫妇女的系统、宏观的认识论的重要性。她们认为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氛围中,传统的父权社会机制及其意识形态逐步崩溃,父权制不得不以新的方式和意识形态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其在经济层面的一个主要的新策略是将社会性别自然化,以降低女性的劳动力的价格,为资本主义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父权制和全球资本主义新的联姻的后果是加剧了体制性的男女不平等和女性生活状况的恶化。在谈到印度的贩卖少女案时,艾伯特指出,“这些少女被买卖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和财产关系”[4](P179)。 美国少数种族女权主义学者凯瑞琳·索瑞斯欧(Carolyn Sorisio)列举了凯瑞琳·卡切(Carolyn L.Karcher)和弗兰西斯·福斯特(Frances S.Foster)等人对美国土著印第安妇女和黑人妇女受压迫和抗争的方式的研究,指出女权主义不仅不能放弃继续建构对父权制的宏观的认识,而且更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辨方式,把妇女局部的、多元的生活现实与父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探索其内在的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系统地建构对父权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宏观的认识论,以此为基础建构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解放政治[6][7][8]。 二、重提性别的生理性、自然性,提出应重建女性气质 是父权社会解放了我,让我重做女人。——卡米拉·帕格利亚[2](P37) 帕格利亚的这一言论代表了麦当娜女权主义在这个议题上的主要论点。她的著名的《性面具》(Sexual Personae)(1990年)一书充满了对男女差异的自然化的界定,以此维护父权制存在的合理性。她对男女差异的界定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用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来界定的性别差异。即阿波罗神象征男性的社会性别特征,代表光明、文化、艺术、秩序和理性认识。帕格利亚认为,男性是聪慧的,是美和秩序的创造者和捍卫者,男性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而狄奥尼索斯神象征女性的社会性别特征,代表自然、原始、身体和大地崇拜,具有破坏性。她因此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男性为女性和儿童提供了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安全保障”[2](P6)。受尼采和叔本华的影响,她认为,男女有别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皮层不一样。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是男女的自然性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她进一步指出,19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极力解构这种男女有别的建构,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崩溃。沃尔芙也与她呼应,认为女性缺乏侵犯性、暴力性。女性要解放,不应反对父权制,而应该更加女性化[3](P144)。 艾伯特等人从3个层面质疑麦当娜女权主义重建男女气质的观点。她们首先着眼这些言论的历史背景,指出197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女性就业的高潮。到了1980年代初期,女性在教育和就业领域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据统计,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时期在大学中第一次女学生的人数超过男学生的人数;第一次50%以上的女性就业;美国人口普查部门第一次允许女性为户主[9](P67)。 大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这个突破虽然与第二波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有关,但是更与19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美国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后对女性劳动力的新的需求有关[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男性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地下降。据统计,靠男性的工资养家的白人家庭中男性的工资减少了22%左右。靠男性养家的家庭几乎绝迹,只占8%[9](P65)。 1991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指出,1980年代以后,面对因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男女之间的矛盾,美国各种保守社会势力挑起男性对女权主义运动的恐惧,炒作了一场“男性气质的危机”。当时在任的里根总统率先为这次反弹推波助澜。他宣称,女性就业的增加导致了男性的大量失业[9](P67)。一些民意测验机构也纷纷通过相关的调查为这次反弹摇旗呐喊。1988年《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对3000男性的调查发现,只有1/4的男性真心地支持女性独立和平等的诉求,绝大多数男性认同传统的女性社会角色。主流媒体大肆宣泄男性的一种失控的情绪:“现在女性的强大导致我们的独立性不仅在家庭中丧失,而且在公众生活中被践踏。”[9](P62)同期好莱坞和出版界极力重塑凶悍的男性气质。宗教界更是掀起了一场“男性运动”,鼓励男性抵制女性化,激发内在的野蛮性。虽然帕格利亚常常自誉是当代最伟大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她公然宣称是这次反弹的一部分[4](P256)。她认为:“现在没有任何发展男人气的空间。男性气质已成为只能在电影里模仿的东西了。”[10]帕格利亚的这些言论受到了当时美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的赞许。右翼评论家肯尼·阿切提(Kenneth Atchity)等人把帕格利亚称为“知识分子中的贞德。”[11] 在理论层面,艾伯特等人指出,19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一直强调把男女的性别差异自然化、本质化是历史上所有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女权主义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理论。帕格利亚等人在1990年代再次将男女性别差异自然化,是重拾女权主义已经颠覆了的父权意识形态的性别建构的牙慧,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一种倒退、反动。艾伯特认为,帕格利亚等人建构的这种本质主义的话语的核心是为男性的统治辩护,为基于男性气质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辩护,目的是把女性重新推回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建构,即回到父权制的家庭中去做妻子和母亲。因此她将麦当娜女权主义称为“父权女权主义”(patriarchal feminism)、“复古女权主义”(retro-feminism)[4](P253,P257)。这些女权主义强调这种父权女权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密切关系。沃尔芙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压迫,但认为女性之间的阶级压迫是健康的,“是我们全面参与社会的结果”[3](P18)。她还宣扬私有制对女性有利,认为有钱就“能把女性从深重的性别压迫中赎买出来”[3](P9)。帕格利亚更是把资本主义赞美为“一种艺术形式”,是阿波罗精神的创造,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剥削和压迫是自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2](P38)。 法露迪以1980年代在美国财富500强中美容业内女工就业的遭遇为例来凸显帕格利亚等人认同的父权资本主义建构的女性气质对广大劳动妇女身心的危害。这些企业不仅乘重建男女气质之机生产各种新型的化妆用品,盈利大增,而且在这些企业内利用传统的女性气质阻止女性就业,对就业的女工进行百般的刁难。她特别提到了在美国氰胺公司(American Cyanamid)就业的贝蒂·瑞格斯(Betty Riggs)等女工的遭遇。该公司以美容产品含有有毒化学成分对女工的身体和生育能力有害为由,对瑞格斯等人提出要么绝育,要么回家的苛刻要求。为了生存,瑞格斯等人不得不选择绝育。即便如此,后来她们还时时面临被解雇的危险[9](P441-445)。因此,艾伯特指出,帕格利亚等人所建构的女性气质帮助了全球资本主义从男女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和消费中获取暴利。她们有关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理论遮蔽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源分配上存在的性别的不平等,因此否定了广大劳动妇女提出解放和社会公正的正当性和必要性[4](P257)。 三、宣扬身体是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关键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由于不射精,不把她们的体液抛出体外,女性是安详的、自我容纳的动物。因此,女性对自己的现状是满足的。女性不具备变革、革命所需的暴烈的侵犯性。——卡米拉·帕格利亚[2](P28) 199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把有关身体的理论提高到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的高度。同样,身体理论也是麦当娜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其上述对男女差异自然化的界定源于其对女性身体的生理性、动物性的认识,认为身体决定了女性的本质和主体性,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对帕格利亚来说,女性的身体指的是她们的性和生育的功能,尤其是女性的性激素、体液和身体的节奏等。在谈到她之所以认为男性创造了人类文明和进步时,她指出,“男性小便呈抛物线状和射精时的勃起是所有文化发展和认识论深化的轨迹”,女性,“就像狗一样,是蹲着小便的”,因此她们用不着抽象思维就能生存[2](P17)。 艾伯特等人对麦当娜女权主义的身体理论的讨论有3个重要的层面。第一,认为帕格利亚等人对女性身体的界定强调女性对身体的自然功能的体验,带有强烈的反理性思维的倾向。这种倾向最终导致否定女性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建构的理性认知,即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必要性。众所周知,女权主义有关身体的讨论历来是围绕着卡迪尔的头脑与身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论把男性界定为理性的;女性是身体的、感性的。第一、二波女权主义有关身体的理论虽然是多元的,但是都质疑这个二元对立,认为这个二元论是传统的性别等级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艾伯特等人认为,对身体的界定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与文明、身体与理性的关系是辩证的,应该在具体的社会氛围中审视。帕格利亚等人的身体理论不仅不质疑这种二元对立,而且进一步深化这种二元对立。在女权主义多年来解构这种二元论之后,她们把女性身体的生理特征夸大到极致,目的是抹去女性劳动的全部历史,否定父权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女性生产力剥削的基础上的历史现实;同时,在女性的身体上重写父权制意识形态建构的宏大叙述,以此替代女权主义基于女性集体的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理性认知的解放理论[4](P270)。 第二,这些学者认为,帕格利亚等人以男女小便姿势的差异决定男女差异的理论导致对身体的不可知性。在质疑帕格利亚等人的身体理论时,艾伯特特别强调概念对建构女性解放理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概念是理论的重要基石,概念编织了理论之网。概念从来都是社会建构。艾伯特指出,有关身体的概念,不仅是哲学的、认识论的、认知性的,而且更是女性解放的历史图表。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初期的“提高觉悟”的“诉苦”活动的一个主要侧重就是解构父权制意识形态中那些掩饰性别统治的概念,建构能够诠释女性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表述女性主体意识的概念。比如发明了“社会性别”“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等概念。艾伯特认为,帕格利亚等人利用后现代主义有关语言涵义的不确定性的理论,将1990年代的父权意识形态对身体的建构嵌入主流女权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中,用以颠覆女权主义解放理论的有效性。比如在有关身体的概念中重新注入西方古代封建社会对男女身体的建构[4](P252-253)。 艾伯特认为,在政治上,帕格利亚等人把性别等级制建立在女性的身体上,以此把女性受父权制的压迫归罪于女性本身。这种对身体的自然化的建构转移了女权主义对现实生活中父权资本主义对女性身体的暴力的视线。她强调,这些暴力不仅包括性暴力和战争对女性的杀戮,而且涵括与身体有密切关系的经济上的剥削,以及贫困、饥饿、童工、移民、贫民窟、贩卖妇女、危险的工作场合、没有充分的医疗保险,以及剥夺女性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尊严等[4](P271)。据美国经济学者阿马塔·森(Amartya Sen)1990年代初的统计,世界上一百多万女性正在因这些暴力致死或失踪[12]。 第三,这些学者质疑帕格利亚等人在阐述身体理论时所使用的修辞策略和逻辑。她们指出,修辞策略是理论的一个重要层面,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修辞逻辑有时对理论的传播起关键作用。艾伯特注意到,在阐述身体理论时,帕格利亚的修辞策略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采用肆无忌惮、极端的论点和逻辑来达到惊世骇俗的效果。在《性面具》一书开头帕格利亚就宣称,应该承认“性别的刻板形象中内含的真理”[2](Pxiii)。她坦言,她就是要用“一种耸人听闻的形式”来表述她的言论[2](Pxiii)。艾伯特认为,这种修辞策略内含强烈的极端性,多是带有煽动性的宣言,因此在理论上缺乏严肃性,旨在挑衅女权主义30多年来致力颠覆的父权意识形态建构的所有的神话、价值观念和民间语汇及其理论前提。她特别提到这种极端的逻辑与好莱坞电影《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1991年)中对女性身心极端残暴的再表现手法吻合。比如影片中剥女人的皮的再表现方式。她指出,这种极端的艺术再现的危害是淡化了女性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性暴力,使女性感到性暴力存在是自然的、常见的、不可避免的。她认为,这种修辞策略在政治上非常有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保守势力利用[4](P259-260)。 帕格利亚等人的修辞策略的第二个特点是以调侃、诙谐的语气营造闹剧的效果。帕格利亚在讨论男女身体差异时多以“下半身”作为比对参照,强调男女的动物性和生理需求的差异。这种修辞手法显得与众不同,好似给人以新鲜感、幽默感。艾伯特认为,为了修复女权主义对父权意识形态的重创,重新建构性别差异,父权资本主义特别注重再度把性别等级制自然化,以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父权资本主义又不可能简单地、照搬不动地重拾过去的牙慧,因为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有些层面在现实中已经失效了。这种调侃、打诨的修辞策略营造的闹剧的目的是帮助父权制重建的意识形态躲避严肃的理论辨疑。马克思有句名言,历史不断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13](P15)。如果说,传统父权社会意识形态对身体自然化的建构导致女性的悲剧性的遭遇的话,那么在20世纪末重复这种建构,就很可能沦为人们嗤之以鼻的闹剧了。但是闹剧也是一种论证的方式。帕格利亚营造的闹剧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在人们对重谈熟悉的谬论的不以为然中,进一步诋毁女性的身体,引发男性的怀旧和失控情绪,发泄对女性的恐惧。因此,这类闹剧在当代的政治生活中是极其危险的。她总结道,帕格利亚的这两种修辞策略正在帮助当代父权资本主义有效地加剧生产中的性别分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分配[4](P259)。 四、宣扬“性”决定女性的命运,“性”是赋权女性的最佳途径 麦当娜教导年轻女性在完全掌控自己生活的同时充分表现她们的女性气质和性感。——卡米拉·帕格利亚[1] 麦当娜女权主义的身体理论的一个重要落点是性理论。帕格利亚认为,“麦当娜对性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即)性的动物性和艺术性。”[1]麦当娜女权主义性化万物,也因此被称为“以性赋权的女权主义”(sexual empowerment feminism)。这种女权主义认为女性的权力是生而具之,源于女性的身体,特别是性。因此,女性的权力是性化的权力。性是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源泉,性决定了她们命运的轨迹。 第一,艾伯特等人首先质疑这种“性决定论”。她们认为产生这些认识的背景是自1960年代避孕技术发明以后,人的性从生育的功能中剥离出来,性功能多元化。19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进入一段繁荣时期,其意识形态和市场顺势将女性的身体和性进一步商业化、消费化,以赚取最大的利润。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1990年代美国右翼在大众文化中炒作有些女权主义“不要性别平等,要性高潮”的风尚,相当有效地把女权主义指责性暴力的舆论转变成性愉悦的话语。同期在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在这种话语和消费文化中建构了新的诉求,认为性感是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最佳途径。同时,女权主义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特别是福柯的“性,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理论,把性建构为一个重要的“权力点”,使性成为女性争取自由、独立的新空间[14](P66-67)。 艾伯特等人指出,这种性决定论首先有个阶级层面,即以性赋权的女权主义属于中产阶级女性的思想范畴,表达她们通过性来抵制父权制的诉求。但是这种话语并不触及建立在性上的等级制及其依附的经济基础——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其次,这种以性赋权的女权主义无视大多数女性的性经历,无视父权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女性的生产力和性的剥削和压迫上的现实。对广大劳动女性来说,她们的性的主要社会功用,一是生育新的劳动力,二是性服务。艾伯特认为,随着医学,特别是生育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日益深入女性的身体和性的空间。世界各国的贫困妇女为了生存,不仅出卖她们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其中很多人还不得不出卖她们的身体和性,比如卖淫,或为有生育困难的中产阶级夫妇代孕,出卖卵子和器官等[4](P271)。 第二,联系帕格利亚对法国18世纪以性虐待文学著称的马克·德·萨德(Marquis deSade)的崇拜,艾伯特等人指出她推崇的性内含强烈的施虐倾向。帕格利亚认为性是“黑暗的、暴力的,是男性独有的特权。”[2](P55)在谈到强奸这个议题时,她宣称,“强奸是一种自然进攻的形式”[2](P23)。虽然性学界内对“性虐待”议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德国生态女权主义者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等人认为,帕格利亚的这些言论凸显了麦当娜女权主义以性赋权的理论的虚伪性。密斯强调,性暴力的实质不是性行为,而是利用性来表达权力的行为。应该把性暴力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性暴力是制度性的权力和高压统治的一部分,以达到对妇女的剩余劳动价值的“超级剥削。”[15] 这些学者认为,帕格利亚等人性理论中的这个层面为1980年代后期美国加剧的性暴力推波助澜。法露迪特别提到1985年美国心理学学会呼应这股逆流,把性虐待界定为一种新的心理疾病,以淡化性暴力的犯罪性。在谈到1980年代中期男性运动的发起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在美国各地巡回举办的、每次上千男性参加的讨论班时,她指出,这个以爱情和性为主题的讨论班的宗旨是为了赋权男性的权力,指导他们怎么控制女性的性,怎么用暴力赋权他们的性。比如在1987年的一次讨论班的奖品中有零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当有个学员抱怨,“当我们告诉女人们我们的性欲,她们不答应”时,布莱指示他们,“那就把这些手枪插到她们嘴里去”[9](P310)。 艾伯特等人进一步指出,麦当娜女权主义推崇性暴力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1990年代以后美帝国主义为掠夺世界经济资源多次发动的战争宣传鸣锣开道。在谈到1991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时,沃尔芙只字不提这场战争杀害了20多万伊拉克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反而极力把美国女兵推崇为赋权女权主义的标杆,“女兵们挥舞着火力强大的武器的形象,……不仅能让人感到她们的爱和欲望,而且感到尊严,甚至恐惧”[3](P17)。艾伯特等人指出,当代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强奸和其他性暴力来征服对方。这特别反映在1992年的波黑战争中以有组织的强奸和性奴役来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据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约5万妇女在这场战争中被强奸[16]。 第三,艾伯特等人质疑麦当娜女权主义的性决定论的第三个层面是其修辞策略的色情化。帕格利亚是色情的积极支持者,她认为,色情揭示了人类的性中“最黑暗,但是最深刻的真理”[17]。她宣称,“我们的文化不允许女性成为女人。网上的色情业越来越成为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无性的文化中挖掘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最原始的能量’”[9]。虽然美国各派女权主义对色情业至今还争论不休,但是艾伯特认为帕格利亚为低俗、淫秽的色情文化辩护的修辞策略与上述提到的以极端的逻辑和以调侃、诙谐以达到闹剧的效果的另外两种修辞策略相辅相成,导致“思想的色情化”[4](P264)。她指出,在封建社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的性和有关性的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多被边缘化。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后期的今天,过去被边缘化的事物失去了被边缘的缘由,有些被资本主义反过来为其统治所用。1990年代以来“性”爆炸性的转身就是一例。帕格利亚本人也认为,这种思想的色情化出现在1980年代后“政治和宗教对人的控制逐步式微的背景,等级制注入了性的空间”[2](P264)。艾伯特认为,她建构的思想色情化有两个层面。一是利用人们对色情、绯闻的专注转移他们对父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系列的假设的思辨。同时以感官和性愉悦的话语来重写建立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上的社会关系,颠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二是把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色情化,用以为资本主义商业经济赢取暴利,掩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特别是劳动力分工基础上的性别化的阶级等级制,为统治阶级实施剥削和暴力应负的责任开脱。她认为这个修辞策略非常有效,是父权资本主义后现代时期的意识形态区别于之前的历史上其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逻辑和修辞策略,导致当代资本主义引领的各种意识形态和认识论,其思维方式和内容、语言表述的方式和修辞策略都不仅被性化了,而且被色情化了[4](P263-264)。 五、结论 女人应该从人而不是从女人的立场出发……——波伏瓦[18](P267) 1990年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10年。随着与“全球接轨”和经济改革的深化,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起来。同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开始逐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以上描述的这些麦当娜女权主义关注的议题或多或少地也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所表现。且不说这一时期大众文化低俗化,色情文化开始泛滥,就文学领域来说,1990年代男性作家的“流氓文学”和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尤其是“下半身写作”更是刺目、火辣,引人注目。在妇女研究领域,乘1995年联合国北京妇女大会的东风,西方女权主义高举“社会性别”的大旗登陆中国。199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在探寻将“社会性别本土化”的道路上,突破了1980年代开启的“去解放”“重新社会性别化”的理论瓶颈,逐渐成为妇女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思想脉络和思维方式[19]。同期,女性主义行动主义空前活跃,开始了重点以身体、性和欲望来赋权女性的主体意识的新时期。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的妇女研究是否正视1990年代遗留的这类议题,将决定今后理论研究的走向。 怎么审视这些重要的议题,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诠释。不难看出,艾伯特等人围绕麦当娜女权主义的讨论有3个重要视角: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审视这些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辨方式;注重研究这些涉及女性现状的社会议题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的等级制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建构扎根深受全球父权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阶层妇女的生活现实和认知的妇女理论,不改女权主义解放所有妇女,解放全人类的初衷。这些是不是也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应该坚守的视角呢? 注释: ①对这支女权主义有很多种想法。如本文后来提到的“父权女权主义”“复古女权主义”“性赋权女权主义”等。中国的搜狗网称之为“反女权主义”。“麦当娜女权主义”是笔者给这支女权主义的命名,这一命名基于这类女权主义对麦当娜的崇拜。帕格利亚本人就宣称她是学术界的麦当娜。 ②在中国妇女研究中,性别等级制一般被称为男权制,但是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普遍被称为“父权制”(Patriarchy)。因为其词源指建立在以父亲为家庭的家长的社会制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