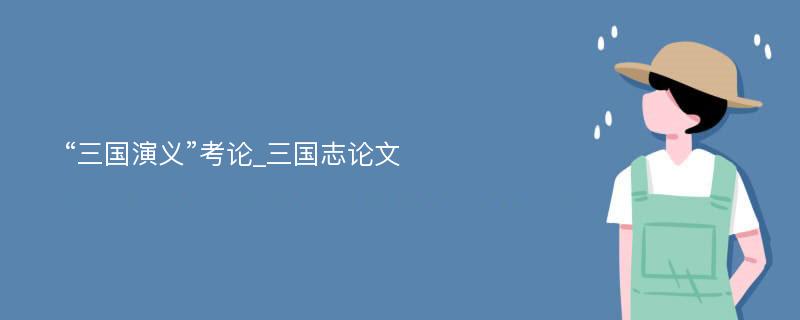
《三国志》戏文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文论文,三国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三国志》戏文的考察,了解明代三国戏文的变迁,辨明南戏对于元及明初三国故事杂剧的袭用,证明《三国志》戏文中存在若干今佚的北杂剧套数;元末开始的“移北入南”现象,为北曲昆唱的渊源所自。
〔关键词〕 《三国志》戏文 三国故事杂剧 北曲昆唱的渊源
有关三国故事的杂剧作品,在元明间颇为流行,成就既高,传存亦多。而南戏除《连环记》外,《桃园记》、《古城记》、《草庐记》等戏,实与杂剧关系颇为密切。《三国志》戏文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明代三国戏文的传演情况及其与杂剧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此种《三国志》戏文,原未见著录。今存者见《风月锦囊》续编第二种,题《精选精编赛全家锦三国志大全》。目录作《三国志桃园记》:版心亦署作《三国志》。其第一段录叙剧情大意的〔沁园春〕词云:
关羽英雄,张飞勇猛,刘备宽仁。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天长地久,意合情真。破黄巾三十六万,功盖诸邦名誉馨。十常侍贪财贿赂,元矫受非刑。 弟兄肃(啸)聚山林,国舅将情表圣君,转受(授)平原县尹。曹公举荐,虎牢关上,战败如(奸)臣。吕布出关,李确(傕)报怨,黄(王)允正宏俱受兵。《三国志》辑成词话一番新。
此本所录凡十八段。其中第十八段为关云长单刀赴会,第十五段则见于《古城记》。这些情节已非前引剧情可以概括。从晚明曲选本所录有关三国戏文的折子情况看,这本《三国志大全》,当是将当时南戏舞台上传演的三国戏文都作了摘引,遂以《大全》或《三国志》为名,而不仅限于《桃园记》一戏。这一点可以从明人曲选或题《三国志》(亦作《三国记》),或据所录剧本直接题作《桃园记》、《古城记》、《草庐记》等情况得到证明。兹将所摘各段曲文略作考证如下(锦本为上图下文,除前四页仅录一副对联外,均有横额,大多可视作下栏曲文之概要,故亦引以为各段之情节概要):
(一)即前引〔沁园春〕词;属南戏“副末开场”。据其所述,当为今佚之《桃园记》的内容。锦本所摘有关三国戏文,似以《桃园记》为主,故目录亦署作《三国志桃园记》。
(二)北〔仙吕·点绛唇〕套,凡〔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三曲,首曲标作〔刘〕唱,自叙志向。上栏图联作:“帝里展经纶,茅檐嗟未达”。
(三)北〔中吕·粉蝶儿〕套六曲:〔醉春风〕〔普天乐〕〔快活三〕〔脱布衫〕〔小梁州〕;关羽唱,标作〔关〕。自叙旅况,兼明志向。上栏图联作“迢递家千里,沧岭几万重”。
(四)〔驻云飞〕四曲,前二曲未标何人唱,第三曲标〔刘〕唱,第四曲标〔张〕唱。上栏二图有联作“沽买新丰酒,方交结义人”;“声名传万古,结义重千金”。叙刘关张相见相识,准备赴桃园结义。
(五)有二图,其额及联作“其诣丘山:故人邂逅情无极,花下论文酒一樽”;“桃园结义:携友游观多少趣,风光一望浩无边”。所叙即“桃园结义”之事。录〔八声甘州〕四曲,首曲标〔生〕即刘备唱,次曲标〔外〕即关羽唱;三、四两曲未标。又〔尾声〕一曲;〔降黄龙〕四曲,依次为〔净〕〔生〕〔外〕〔末〕唱。其中净扮张飞,生扮刘备,外扮关羽;末角自称“仆当贺喜,愿从此三人,莫生疑虑”,但不知所扮何人。又〔滚〕二曲,〔尾声〕一曲,未标何人唱。
(六)录〔耍孩儿〕二曲,末尾四句系〔合唱〕,故当属南曲〔耍孩儿〕,标〔末〕唱。此段未有相应之图,据“月下钢刀带血磨”等语,似为黄巾头领所唱。当与“共破黄巾三十六万”情节有关。
(七)上栏图题作“黄(王)允夫妇桑园同乐:相逢话旧欢无极,花下传杯听鸟□。”录〔淘金令〕四曲,依次为〔外〕〔占〕〔外〕〔占〕。外扮王允,占(贴)扮其妻。
(八)上栏图作“三兄弟嗟叹:兄弟三人曾战敌,徒然几度费心机。”录〔甘州歌〕四曲,依次为〔生〕〔外〕〔净〕〔丑〕唱。丑角不知所扮何人。“合”语有“十常侍,久弄权,贪赃枉法把君欺”,嗟叹平黄巾立战功,因奸臣弄权而不为君上所知。与〔沁园春〕词可对看。
(九)上栏图作“吕布自叹英雄:志气扬名真得誉,英雄姓字肯嗟吁。”录北〔耍孩儿〕一套五煞并〔煞尾〕。标〔吕唱〕。自名“凤仙”,按:小说作“奉先”。〔煞尾〕云:“明晨发上都,征进西凉府。俺忠心赤胆扶君父,要使得青史标名传万古。”当为辞义父董卓西征前的情节。
(十)上栏图作“貂蝉见吕布:夫妻今日重相见,香阁深闺月再圆。”录〔耍孩儿〕二曲,〔尾〕一曲,标〔旦〕唱。据其所叙,为貂蝉与吕布在董卓堂中重相见而不敢认,二人原为夫妻,“间阻不觉已三年”,故貂蝉在黄昏月下烧香拜祷。
(十一)上栏图作“花烛洞房:洞房花烛煌煌夜,□□调和瑟与琴。”录〔画眉序〕三曲,第一曲标〔旦〕唱;据文意,三曲均为旦唱。此三曲后,锦本有标作〔又〕者二曲并〔尾〕。但据曲律,此二曲非〔画眉序〕,曲牌待考;所唱者当是〔众〕。此段情节,当为诛董卓后,吕布与貂蝉花烛洞房的场面。
(十二)录〔桂枝香〕二曲,分别标〔外〕〔丑〕唱。外所扮当为吕布;而第一曲之“昔关前拒敌,非伊之罪,本是梁王叛逆”云云,似为刘备之语。又丑语云:“将军忠烈,主公仁义,今日里新谷既登,旧谷何须提起。自今如始,自今如始,同扶社稷。”当是吕布窘迫之时,前来依附刘备,故刘备向关羽解释,向日乃董梁王之故,而丑语则望不提旧事,同扶社稷。
(十三)此段录有二图,“关羽叹张飞:生擒吕布如翻掌,旌旗按北势无双。”“貂蝉见关羽:轻衣缓步来相见,只愿江山属汉王。”录北〔正宫·端正好〕一套七曲:〔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滚绣球〕〔倘秀才〕〔尾〕。其中第三、四两曲标〔旦〕唱。据文意,第五曲及尾声也为旦唱。按:图栏“生擒吕布如反掌”一联之语,分见于第一、二两曲,则此二曲似为关羽唱。若如此,则该套北曲为旦与外分唱,不合惯例。故关羽所“叹”者当只是白文,而锦本未摘;本套则全由旦唱。前二曲系旦从中军帐前看到张飞擒吕布的情形;第三曲以下则叙貂蝉“弓鞋出洞房,金莲款步忙,我安排着语言的当,到帐前拜见关张”,“忙斟琥珀觞,高扳着小叔央”,“若遇英雄我立在傍,我两人此夜明蟾须共赏”。貂蝉颇有以色相诱之意,引出后篇关羽斩貂蝉。
(十四)此段录有四图,可见大意:“夜读春秋:五夜沉沉明月在,好将书史着留心”;“关羽问貂蝉:正是酒淹衫袖湿,果然花压帽檐低”;“貂蝉夸关张:吕布英雄曾盖世,□女变弄巧花言”;“关羽斩貂蝉:形魂杳杳归阴府,四海扬扬名誉传”。由北〔中吕·粉蝶儿〕与〔耍孩儿〕二套构成。依次为〔粉蝶儿〕〔醉春风〕〔脱布衫〕〔小梁州〕〔幺〕〔上小楼〕〔幺〕〔快活三〕〔朝天子〕〔四边静〕〔满庭芳〕;〔耍孩儿〕〔五煞〕〔四煞〕〔三煞〕〔二煞〕〔一煞〕〔煞尾〕。第一、四两曲标〔关〕唱。而两套实均为关羽唱。所叙当承前段,关羽在灯前读〔春秋〕,貂蝉献媚,夸关张而贬吕布。关羽所唱第一套,为吕布申辩,责貂蝉“唆吕布全无些谏忠言”,第二套则叙斩貂蝉之情状。
按:〔耍孩儿〕套,《群音类选》官腔类卷十二收录首曲及〔三煞〕〔二煞〕文字,曲牌作〔滚〕;题作“关斩貂蝉”,署谓出于《桃园记》。实已经过改造。又按:元人杂剧有《关大王月下斩貂蝉》,见《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著录;《远山堂剧品》著录作《斩貂蝉》,注谓五折。无名氏作。该剧今佚。但从有关《三国志》戏文多移用北曲杂剧套数的情况看,〔粉蝶儿〕〔耍孩儿〕二套当即《斩貂蝉》杂剧之佚文。斩貂蝉情节虽为元人杂剧的喜用,但《三国志演义》小说未取;而明代以降,民间戏曲中仍广为流传。如《缀白裘》第十一集卷三即录有折子;晚至清后期及近代,京剧等剧种仍有《斩貂蝉》剧目流传。如清车王府抄藏曲本中,即有此目(见《车王府曲本提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此外,明代涉及貂蝉的戏文,最著名者当为王济的《连环记》;但《连环记》多据史实及演义,无斩貂蝉之事。另据《九宫正始》所录题《貂蝉女》或《王允》的宋元戏文佚曲二支(参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或为锦本所摘的有关貂蝉戏文的最早来源。
(十五)上栏图作:“江糜二妇下徐州:挂印封金辞汉朝,迎兄遥望远途还”。录有六曲,依次为:〔混江龙〕一曲,系关唱,叙驿舍光景;〔驻云飞〕五曲,首曲标〔关〕唱,次曲标〔旦〕唱,以后关与旦依次间唱,分别叙二人从樵鼓初更到五更时所思所想。按:此段见于《古城记》第十一出《秉烛》,据文林阁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其第一曲曲牌作〔点绛唇〕。曲词基本一致。此段又见《词林一枝》卷二摘录,题“关云长秉烛待旦”,署云出《古城记》,与文林阁本文字一致。
(十六)上栏图作“千里独行:独行斩将应无敌,刀偃青龙出五关”;“许褚进炮:千里寻兄恩义重,刀尖挑却锦征袍”。录北〔仙吕·点绛唇〕一套,依次为〔点绎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哪吒令〕〔鹊踏枝〕(此曲后半曲以下,锦本原残脱一页),首曲标〔外〕唱,馀均标作〔关〕唱。按:此套叙云长辞别曹操后独行千里事,亦见《雍熙乐府》卷四收录,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移录,谓系元人杂剧套数无疑。但该套与今存元明间无名氏杂剧《关云长独行千里》不合,故赵景深疑其为《斩蔡阳》杂剧之一折。
又,《古城记》第二十六出《服仓》有关羽唱〔新水令〕一套,实出于锦本底本而又加改动。其中〔新水令〕脱自〔点绛唇〕曲;〔折桂令〕出于〔混江龙〕曲;〔雁儿落带得胜令〕出于〔油葫芦〕曲;〔收江南〕出于〔天下乐〕曲;〔园林好〕曲词间出于〔哪吒令〕曲。可知《古城记》在锦本的基础上作了改动。锦本所据者,为《古城记》早期传本。此外,晚明曲选本又多选录“千里独行”一出,文字大体同《古城记》之《服仓》套。如(1)《尧天乐》卷二下层录《关云长独行千里》一出,署出《古城记》;(2)《歌林拾翠》卷二录《独行千里》出,署出《古城记》;(3)《时调青昆》卷二上层,录《独行千里》出,署出《古城记》;(4)《群音类选》卷十二录《独行千里》,署出《桃园记》。
(十七)上栏图作“孔明自叹:片时妙论三分定,一席高谈自古无”。因前残脱一页,此段第一曲仅残存半曲,另三曲完整,标作〔又〕,未知曲牌作何。系孔明唱。据其情节,与下段联系更为密切。
(十八)上栏图作“羽赴单刀:藐视吴侯似小儿,单刀赴会敢平欺”;“鲁肃送关王;当年一鼓英雄气,今朝独知在渑池”。录〔双调·新水令〕一套,曲牌依次为:〔新水令〕〔哪吒令〕〔庆东园(原)〕〔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搅筝琶〕,标作〔关〕或〔羽〕唱。按:此套实出于关汉卿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有元刊本及脉望馆抄本)。两相比较,在曲牌方面,锦本〔新水令〕后半另为一曲,失标曲牌,应据杂剧补〔驻马听〕曲牌。锦本〔哪吒令〕,脉望馆本作〔胡十八〕。脉望馆本末尾之〔离亭宴带歇指拍煞〕,锦本未摘,其余曲牌均同,而字词略有差异。但这种差异比之其他晚明选本所录“刀会”折子,则又相对更接近一些了。昆腔著名折子《刀会》,一般人均知其出于北剧,为北曲昆唱,但其最早如何进入南戏演唱,则多不甚明了。今可知它是在南戏移用北剧的过程中,融入南戏的;而关汉卿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使这套曲文深受人们喜爱,以至成为南曲戏文与传奇演唱中的著名折子,从曲词到曲谱得以流传至今。它作为单出,为明人多种曲选选录,这些曲选本所题出处,又为我们了解其流传过程提供了材料:
(1)《乐府红珊》卷十一,录“关云长赴单刀会”一出。署:《三国志》。该出之首有末扮关平唱南〔玩仙灯〕引子,外扮云长唱南〔凤凰阁〕引子,然后再接北〔双调·新水令〕套,曲牌名目及序次则全部同关剧,包括录有〔歇拍煞〕。
(2)《珊珊集》卷三,录《单刀赴会》〔双调·新水令〕一套(只录曲文),题:《三国志》。较之脉望馆本,未标〔得胜令〕曲牌,将此曲合于〔雁儿落〕曲内;〔尾声〕只录关剧〔煞尾〕之末五句。较之《乐府红珊》,未摘二支南曲引子,以其不属于该套的缘故。
(3)《怡春锦·弦索元音御集》,录《四郡记·单刀》一出,曲牌同《珊珊集》,未录《乐府红珊》之二〔引〕。净扮关羽。
试比较诸本的曲词:
元刊: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
脉本:○○○○○○○,○○○○○○○○○○○○○
锦本:○○○○○○○,趁西风 ○下 ○○○○
红珊:○○○巨○○○,趁西风 ○○○○○
珊珊:○○○巨○○○,趁西风 ○○○○○
怡春:○○○巨○○○,趁西风 ○○○○○
可知锦本底本首取自关剧,后三本均从锦本底本化出。但从《怡春锦》所署,它所据的底本作《四郡记》;已经透出信息:总名“三国志”当即属三国故事戏文而归于一处,它们本身尚有别名。正如前文所录别出于《桃园记》《古城记》,却同归“三国志”名下一样。
关汉卿《单刀会》杂剧,被移录于南曲戏文者,并不限于第四折。它的第一折和第三折,也同时被移于同一本南戏中:
第一折叙鲁肃向乔公求计,分别见于:
(1)《大明天下春》卷六,录《鲁肃求谋》一出,署:《三国志》。
(2)《大明春》卷五下层,录《鲁肃计请国(正文作“乔”)公》一出,署:《三国记》。
(3)《乐府红珊》卷九访询类,录《鲁子敬询乔国公》一出,署《桃园记》。
(4)《乐府菁华》卷六上层,录《鲁肃求谋》一出,未题出处。
四本均为外扮乔公,唱南〔生查子〕引,后接北〔仙吕·点绛唇〕套,曲牌依次为〔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上马娇〕〔后庭花〕。前三曲同关剧,后三曲曲词仍出自关剧,但已对关剧词句作了重新组合,故前后序次错综不一,曲牌便不相同。
第二折训子一套,分别见于:
(1)《天下大明春》卷六,录《云长训子》一出,署:《三国志》。先是〔羽〕、〔平〕各唱南〔菊花新〕引一曲后,由〔羽〕唱北〔中吕·粉蝶儿〕套。曲牌依次作:〔粉蝶儿〕〔醉太平〕(关剧作〔醉春风〕)〔朱履曲〕(关剧作〔十二月〕、〔尧民歌〕二曲)〔石榴花〕〔么篇〕〔斗鹌鹑〕〔满庭芳〕(关剧无此曲牌)〔上小楼〕〔么篇〕〔鲍老催〕(此曲关剧作〔鲍老儿〕,以下尚有〔剔银灯〕〔蔓青菜〕〔尾声〕诸曲;但此数曲的文字锦本已化入前列各曲内)。
(2)《大明春》卷六上层,录《云长训子》出,文字全同《天下大明春》,署作《结义记》。
(3)《乐府万象新》卷三上层,录《关云长数功训子》(正文作《关云长训子》)一出,署:《三国记》。文字同《天下大明春》。
(4)《乐府红珊》卷四训诲类,录《汉寿亭侯(正文作“关云长”)训子》,署《桃园记》。
昆曲著名折子《训子》,即来源于此。
可知关汉卿《单刀会》杂剧,四折之中,至少有三折被全文移入南曲中,正如《千金记》移用《北追》一折、《金貂记》移用《北诈》、《红梨记》移用三折北杂剧同名作品的情况相同。换言之,锦本的底本也应有《求计》《训子》二出,只是锦本未摘而已。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如《天下大明春》卷六所录,版心题《三国志》的五出戏文,其中《翼德逃归》别种选本或署出《古城记》(见后);《赴碧联(莲)会》实出于《草庐记》四十五出:《鲁肃求谋》和《云长训子》二出已见前引,别种选本或署出《四郡记》或《桃园记》;《武侯平蛮》当出于《平蛮记》(按:《大明春》卷六录《武侯平蛮》,署出《兴刘记》;《诸葛出师》出,署出《征蛮记》),所录五出之中,参照别种选本,则至少来源于三种不同剧目。同样,《乐府万象新》卷三录《张飞私奔范阳》和《关云长数功训子》二出,均标出自《三国记》,而《私奔范阳》别本或题作《古城记》(如《时调青昆》;按今本《古城记》实无)。此外,《乐府红珊》卷一庆寿类录有《关云长公祝寿》(正文题《汉寿亭侯庆寿》),署出自《单刀记》,虽然可能是书估标新立异,正如该集录《训子》出,别署《结义记》,录《求计》出,别署《桃园记》一样。但也确实有一种叙单刀赴会事为主的《单刀会》或《四郡记》存在。《单刀记》,原应作《单刀会》(称“记”是明后期风气),据《宦门子弟错立身》咏传奇名〔哪吒令〕中“这一本是《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句,可知元后期已有《单刀会》南戏。这本《单刀会》南戏,当是南戏发展到元顺帝朝,“忽亲南而疏北,作者猬兴”(《南词叙录》),化北入南的产物。关氏《单刀会》的三套曲文被移入南戏,最早当始于此。《四郡记》,据《曲海总目提要》卷四十五:“此记未知何人所作。与《古城记》皆以刘备、关羽为主。《古城》所演,系刘关前截,在徐沛间事;《四郡》所演,系刘关后截,与孙争荆州事。刘关起手,大略相仿,诸葛亮、鲁肃、周瑜等,则《古城》所无也。”《玉谷新簧》一卷下层录《周瑜差将下书》《云长护河梁会》《曹操霸桥饯别》四出,署出《三国记》。按《云长赴河梁会》,《乐府红珊》卷十一收录作《刘玄德赴河梁会》,署:《桃园记》。其情节《草庐记》之赴碧莲会实同,但文字全别,护会者《草庐记》为孙乾(后半出忽作简雍),此则为云长;而赴会情节两本均出于无名氏《黄鹤楼》杂剧,唯杂剧中护会者为姜维;《饯别》出,主要录〔转调鹤(货)郎儿〕一套,与《古城记》第二十出《受锦》文字上相近,原出明初朱有燉《关云长义勇辞金》杂剧。《八能奏锦》所录近《古城记》,但署作《五关记》。上述选出都属于三国故事戏,虽分出于不同之剧,但人们为了方便,也往往统而称之为《三国志》或《三国记》;换言之,在《三国志》的总名下,包含三至四种系列之剧。故《远山堂曲品》说:“《三国传》中曲,首《桃园》,《古城》次之,《草庐》又次之。”按:《三国演义》明建阳刊本多作《三国志传》。
在明代统称为《三国志》或《三国记》的戏文,实包含数种首尾相续的系列剧本,即:《桃园记》(佚)、《古城记》(存)、《草庐记》(存)、《四郡记》(佚,或别称《单刀记》,其前身则或为元代南戏《单刀会》)、《平蛮记》(存《平蛮图》一种,清钞本,十六出,北图藏)。其中,《桃园记》与《古城记》之间,可能还有一种《貂蝉女》(或《斩貂蝉》),锦本所叙貂蝉故事各段,也可能属于该剧,即《貂蝉女》为《桃园记》袭用。除《草庐记》和《四郡记》可能在某些情节上会有重叠外,它们作为三国故事戏,本身前后衔接,并不重复。故锦本以及其他明人戏曲选本也以《三国志大全》、《三国志》或《三国记》作为总名,选录各剧的散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以《三国志桃园记》或《桃园记》来代指各剧,前者如锦本目录所题;后者如《群音类选》、《乐府红珊》。此外也有以《古城记》来概指三国戏的,如《时调青昆》等。
锦本所录《三国志大全》十八段中,移用北曲套数达十一套,以至有人将它归于杂剧类(见孙崇涛《风月锦囊考释》之一,中华戏曲第八辑)。但无论《三国志大全》或别加题称的各个剧本,它们属于南戏,应是没有疑问的。它们的一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一)它们可以说都属于化北为南的作品,即以杂剧三国戏为依托,加以联缀贯穿。(二)它们都大量、原封不动地移录了北曲杂剧的套数。不仅锦本《三国志大全》是如此,今存的《古城记》和《草庐记》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如《群音类选》所录《桃园记》散出,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从前举锦本及明人选本所摘引之曲与《古城记》相比较,锦本中直录的北曲套数,在《古城记》中有的以“滚”或别题曲牌的方式改造为南曲;故《古城记》、《草庐记》今存本已是晚明“传奇化”之后的产物,它们的前身应更多直录北曲,如《训子》《求计》等仅加一二支南曲引子,便直录北曲套数,作为南曲中的北曲演唱。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古城记》等在后来传奇化过程中的改造,主要也就是消除这类生吞活剥的痕迹,所以虽多用北曲入戏,但并不显得生硬。究其原因,元代后期以降,南北合套的出现与用北曲入南戏,为这种移用提供了方便。(三)从锦本看,其中所录,凡袭自北曲的套数者,多标称〔关〕〔刘〕〔吕〕所唱,以人物为称;而南曲则多以角色称,如〔生〕〔外〕之类。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的北曲套数基本上来自杂剧,虽然其中有一些可能是明杂剧,如今本《古城记》十六出《斩将》北〔新水令〕套和《受锦》出之文字实袭自朱有燉《关云长义勇辞金》杂剧。两者字词稍有出入,可能是《古城记》在传奇化的过程中受到进一步改删的缘故,而早期《古城记》本子当更为一致。正如前举《古城记》等袭用锦本、《雍熙乐府》所录《独行千里》套,却又加以变换,化成南曲〔折桂令〕一样。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象《单刀会》杂剧的一、三、四折,因为在元代已经移用于南曲戏文,它们同时也是属于南戏的范畴,成为我们了解南戏与杂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材料。
*本文1997年1月16日收到。
A Textual Study of the Xi Wen The Three Kingdoms
Huang Shiz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Xi Wen The ThreeKingdoms and its changes in the Ming Dynasty,the present article finds out Nanxi's borrowing of the Zajubased on the storiesof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proves that,in the Xi Wen The Three Kingdoms,there are some northern Zaju succession balladswhich arein oblivion today,Wecan trace the singing of Beiqu in Kun tune to the phenomenon of usingBeiqu inNaxi beginning from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标签:三国志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貂蝉论文; 关羽论文; 吕布论文; 单刀会论文; 吕布奉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