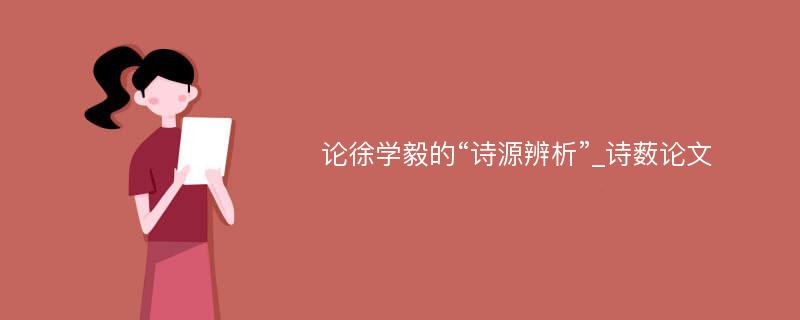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许学夷论文,诗源辨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江阴布衣学者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历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诗歌史观、审美标准及自觉的批评意识三方面,将《诗源辨体》(以下简称《辨体》)与严羽、胡应麟等名家理论进行比较,以期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通变”的诗歌史观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发端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诗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支柱,源流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其中影响最大、专治诗歌辨体的著作是胡应麟的《诗薮》。《辨体》成书时间晚于《诗薮》,许学夷对胡应麟论诗推崇备至。两人同属复古派,都深受《沧浪诗话》的影响。《辨体》中多处引用胡应麟的观点,或赞同,或辨驳,受其启发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诗史观与《诗薮》并不完全一致。
《诗薮》“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论诗主旨,为其确立了复古主义的基调。胡应麟看到了一种文体的发展必定是由盛转衰而亡,最终不得不为一种新文体所替代,这是“势也,时也”,是诗歌艺术发展自身的要求,亦与时代之“气运”有关。
同时,胡应麟又论道:八代诗人“其文日变而盛,而古意日衰;其格日变而新,而前规日远也”,“楚一变而为骚,汉再变而为选,唐三变而为律,体格日卑”。当“体以代变”赋予了“格以代降”的内涵,封闭性的退化论诗史观便很明显了。
《辨体》开宗明义,阐发题旨:“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源与正一致,从“三百篇”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律诗是一脉相传的。流与派都属于变。许学夷辨体侧重于辨一种诗体于不同时代的变化。源与流、派,正与变的界定本身就是有高下之分的品评,《辨体》无疑具有尚古的倾向,但与盛、衰、亡、高、卑的界定相比,其内涵则更为宽泛,更有变通的余地。
胡应麟认为诗歌“格以代降”,因而评论新的表达风格,要依据“前规”,“为其题者,不用本格,便非本色”(内编卷二)。完全以“第一义”的作品为标准,僵化了严羽的“本色论”,是严格的拟古论。如对宋诗的评价,皆以盛唐律诗和六朝古体为价值取向,而不是从诗作本身的艺术特征来评论宋诗的长短。对此,许学夷论道:“元美、元瑞论诗,于正虽有所得,于变者则不能知。”(后集纂要卷一)又说:“宋主变,不主正,古诗、歌行、滑稽、议论,是其所长,其变幻无穷,凌跨一代,正在于此。或欲以论唐诗者论宋,正犹求中庸之言于释老,未可语释老也。”(同上)许学夷点到了七子派以唐诗论宋诗的要害之处。当然,他并不认为韩、白、欧、苏诗是诗之正体,仍是变,是变而美者,在宗唐的前提下,肯定了宋诗有其“凌跨一代”的审美价值,这正是宋诗对唐诗的变异之处,发展之处。
许学夷论正变,讲究正、正变(正中之变)、变中之变(指宋元以后诗)。重视变中之变与他一贯地注重艺术家的独创精神是相关的。在对正与正变的评述中,尤其是在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评价中,极力赞扬他们的创造精神。
在明代复古思潮中,许学夷为何能较为辩证地看到“变”的价值呢?我认为,除受中华民族注重“变易”的思想影响外,主要应归结为:许学夷的文学活动时代经历了公安派的兴与衰,虽然他对公安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颇为不满,却也能部分地吸收其有进步意义的内涵。袁宏道说:“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序小修诗》)文学发展贵在变化出新,惟有变才能求发展。许学夷评道:“袁中郎于正者虽不能知,于变者实有所得。”(后集纂要卷一)格调派与公安派的诗学在此作了折中的调和。我们可寻出许学夷受袁宏道论“变”思想影响的轨迹。他在评论苏轼论诗时,亦赞苏轼论诗能“权变”。
《辨体》几次提到“通变”一词。识通变之道为论诗的基本原则:“汉魏五言及乐府杂言,犹秦汉之文也。李杜五言古及七言歌行,犹韩、柳、欧、苏之文也。秦汉、四子各极其至;汉魏、李杜亦各极其至焉,何则?时代不同也。论诗者以汉魏为至,而以李杜为未极,犹论文者以秦汉为正,而以四子为未极,皆慕好古之名而不识通变之道者也。”(卷三十四)论元结收辑沈千运等七位不知名诗人的五言古诗为《箧中集》:“诗至于唐,律盛而古衰矣,今元所选,声虽合古,而制作不工,乃云‘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是于唐律一无足采,而惟古声是取耳,岂识通变之道哉!若曰唐人古、律混淆而录千运等古声以为法,庶几近之。”(卷三十六)反对贵古贱近,既承认“通”,又肯定“变”。
由此,许学夷的诗史观是“通变论”的传统文学史观。既不是七子派的由变而衰,也不是公安派的只讲“变”而忽略“通”,而颇似于清代诗论家叶燮论“变”:“或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得无因变而益衰者。”(《原诗》内编上)前者如陶、李、杜、苏,后者如唐之钱、刘诸子,宋之黄、陈。既主张会通与适变相结合,又坚持诗歌具有本体特征,即诗之正体。
兼融并包的审美标准
明代格调派论诗重视摹拟古人的体格声调。但一味地追似古人的古调高格,必定流于剽袭古人。格调派也不可能无视宋以前确立的对诗歌艺术特质及审美标准的认识与概括。他们在倡“格调说”的同时,也在寻找诗歌创作的动力,倡导新的审美准则。如李梦阳强调诗歌应“情以发之”;李开先提出“诗贵意兴活泼”;王世贞融合“才”、“思”与“格调”,崇尚“神与境合”的境界;王世懋特标“高韵”、神情。稍后的胡应麟沿着这条路,欲把“格调”与“神韵”统一起来:“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矣。”(《诗薮》内编卷五)审美标准逐渐走向丰富。
《辨体》是明代后期屈指可数的以“格调”论诗的著作。它吸收前人成果,审美标准可说是兼融并包,上述种种审美标准在书中都有所运用。如卷十四:“融化无迹得于造诣,故学者犹可为,气象风格得于天授,故学者不易为也。”卷十七:“盛唐诸公律诗,形迹俱融,风神超迈,此虽造诣之功,亦是兴趣所得耳。”但许学夷受严羽诗论的影响更为直接。他说:“沧浪论诗之法有五:一曰‘体制’;二曰‘格力’,予得之以论汉魏;三曰‘气象’,予得之论初唐;四曰‘兴趣’,予得之以论盛唐;五曰‘音节’,予得之以概论唐律也。”对严羽的审美特征论尤为推崇,曾表明:“沧浪论诗,与予千古一辙。”(卷三十五)
严羽把“悟”确定为学诗、作诗的基本思维方式,并认为有深浅之分,即不假悟、透澈之悟和一知半解之悟。对此,许学夷有所阐发:“汉魏天成,本不假之悟;六朝刻雕绮靡,又不以言悟;初唐沈宋律诗,造诣虽纯,而化机尚浅,亦非透彻之悟。唯盛唐诸公,领会神情,不仿形迹,故忽然而来,浑然而就,如缭之于丸,秋之于奕,公孙之舞剑,此方是透彻之悟。”(卷十七)形象地表达了“透彻之悟”的审美效应。他理解的“悟”更接近于来不可遏、忽然而降的审美直觉。
“悟”是怎样获得的呢?严羽论道:“先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乃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诗是美感对象之一,学诗者应通过对佳作的“熟参”而获得丰富的美感经验,此即严羽之谓有所“悟入”。许学夷认为,盛唐诸公律诗悟入“乃自功夫中来”。他引吕居仁的话:“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间。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卷十七)说明“顿悟”发挥它神奇般的效力,是以创作主体长时期的感受、注意、观察、捕捉和挑选含有某种本质意义的现实生活形象为前提的。两人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强调创作主体审美经验探索的重要性;不同之处在于,严羽的“悟”只停留在对审美经验的“悟”,而许学夷认为真正“悟”的发生,不在于对诗“熟参”之后,而在于主体与客体“相遇”的瞬间。在此,许学夷顾及了另一审美对象——客观现实。
究其实,“妙悟”产生的原动力在于诗人的情感。“妙悟说”与“兴趣说”是相通的。严羽的“兴趣说”突出了诗与一般以理见长的文字的区别,强调诗有自己特殊的旨趣,具有抒情性、趣味性及非逻辑性等审美特质。而许学夷正是以“兴趣”作为评诗的主要审美标准。
严羽品唐诗有“兴趣”与“意兴”之分。“兴趣”与“兴”有关,与“趣”也有关。“兴”从创作主体来讲是“睹物兴情”(刘勰语),从审美感受来讲是“文已尽而意有余”(钟嵘语)。而“趣”是由于兴的引发,情与物遇而产生的一种审美趣味。“兴”与“趣”合起来就是兴味、情味。不过,两者亦有区别。《辨体》论盛唐诗与杜甫诗的区别,为此作了较为恰当的注脚:“前言‘兴趣’,而此言‘意兴’,正兼诸家与子美论”;“盛唐诸公律诗,得风人之致,故主兴不主意,贵婉而不贵深。冯元成谓‘得风人之旨而兼词人之秀’是也。子美虽大而有法,要皆主意而尚严密,故于雅为近,此为盛唐诸公,各自为胜,未可以优劣论”(卷十七)。主“兴趣”与主“意兴”的区别有如风与雅之别。风与雅,本是《诗经》的两种体裁,后逐渐衍化为两种风格特征,既相异相对,又相辅相成,不可缺一,亦不可以优劣论。此论深识唐诗变化之旨、情与理的辩证关系。
“诗而入神”、“无迹可求”是古典诗歌最高的审美境界。许学夷论盛唐诗有正宗、圣与神三个等级之分。符合正格正调的为正宗;盛唐诸公律诗,“融化无迹”的都能“入于圣”,唯太白、子美“皆变化不测而入于神也”。圣品只能列入“妙境”,唯有“入于神”才能达于“化境”。关于“化境”的创造,许学夷认为胡应麟“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是“造诣之功”,“此由初入盛之阶也”(卷十七)。造诣,是诗人的学问、艺术技巧达到的程度,与才力有所不同,“高岑之诗,才力胜于造诣,王孟之诗,造诣胜于才力”(卷十六),“唐人诗贵造诣”,故异于汉魏的不假之悟。许学夷赞同何仲默的说法:“富于才识,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斯可论盛唐之化也”(卷十七)。才力、学识必不可少,然作诗的关键还在于领会人与世的“神情”,“临景”结构诗句,就丝毫没有摹拟“作用”的痕迹。当主体之神与客体之神一相遇,诗便“入神”了。许学夷已初步意识到这一点。
由此,《辨体》较为本质地把握了以严羽诗论为代表的中国诗学审美理论的精髓,体现出鲜明的纯艺术观。其审美标准兼融并包,论诗能博取众长,亦不乏独到之见地,体现出许学夷对诗歌审美特质研究之精到。
自觉的批评意识
古典诗歌艺术发展到明代,题材无所不及,风格无所不备,极尽变化,可供明代诗人开垦的土地所剩无几。他们没有能够走向新变,而是返回头来学古格古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不能“自创一堂室”的风尚。胡应麟说:“明不致工于作,而致工于述,不求多于专门,而求多于具体,所以度越元、宋,苞综盛唐。”(《诗薮》内编卷一)明诗的特点,不在独创,而在于绍述古人,不追求某一体有所突破,而追求各体兼工,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度越元、宋,苞综盛唐”。
《辨体》后集纂要卷二共104条专论明代诗歌, 对明诗人学古之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元美识越一代,力敌万人,有兼功而无专力。总诸体而论,乐府变数篇,可称诣极;五言古,选体最劣,唐代稍胜,变体及学东坡者,多有可观;歌行,六朝、唐、宋靡所不有,而入录者不能什一,中虽有奇伟之作,而纯全者少,变体始多全作;五言律,仅得百中之一,而实非本相;七言律,意在宗杜,又欲兼总诸家,然臃肿支离,复多深晦,晚唐奇丑者亦往往见之,此英雄欺人耳。”王世贞是明中叶诗坛盟主,追随者众多,他亦不过是“有兼功而无专力”,多拟古之作,缺乏创作个性,“英雄欺人”。明代格调派诗歌创作的一般状况由此可知。
《辨体》特以两卷的篇幅,历论自曹丕以来数十家的诗论及自《文选》以来30种诗歌选本,约略现出古典诗歌批评发展的轮廓。对诗论和选本的批评集中体现了许学夷的文学观和批评观。首先还是要能“识其正变”,“选则未易能也。苟有中正之识,则凡汉、魏、初、盛唐雅正之诗,或可选也。若夫言诗,得其中者必遗其偏,明于正者多昧于变,能于三百篇、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各得其正、变而论之者,鲜矣”(卷三十五)。指出历代“言诗”能各得正变而论之的,非常少。他批评《昭明文选》以类分而不以体分的选诗标准,“今人知学《选》而不知辨,故其体不纯耳”(卷三十六),仍是格调派的眼光。
许学夷还指出了宋元诗论“困于法”的弊病:“独于章句之间搜剔穿凿,愈深愈远,诗道至此,不止扫地矣。”(卷三十五)宋元诗人好“资书以为诗”,与宋元诗论好谈句法章法有很大关系。他批评元人诗话《诗家一指》说:“言作诗先命意,如构宫室,必法度形制已备于胸中,始施斤斧。予谓:此作文之法也。‘三百篇’之风,汉魏之五言,唐人之律绝,莫不以情为主,情之所至,即意之所在;不主情而主意,则尚理求深,必入于元和、宋人之流矣。”(卷三十五)反对作诗有成法,诗论一味研究法度。诗之道乃在达人情性。明代,讲道的理学异常盛行,而在这里,“情”摆到了根本的地位。当然许学夷的“诗主情”说,仍属于传统的儒家诗教的“诗缘情”说,与公安派提出的“情”还有区别。
作为论诗和选诗的前提,许学夷要求论者与选者应具“中正之识”、“识理势之自然”(卷三十四)。他提出选诗的标准:“选诗者须以李选李,以杜选杜,至于高、岑、王、孟,莫不皆然,若以己意选诗,则失所长矣。”(卷三十六)尽管选诗难免带有己意,但根据诗人自身的创作风格,客观、准确地选诗,仍是重要的准则。他对批评家和选家的思维特点作了最一般性的规定。
许学夷自觉的批评意识还表现于在批评视角方面提出了总体把握的主张:“古今人论诗,论字不如论句,论句不如论篇,论篇不知论人,论人不如论代。晚唐宋元诸人论诗多论代、论人,至论篇论句者寡矣,况论字乎。”又说:“诗有本末,体气本也,字句末也,本可以兼末,末不可以兼本。”(卷三十四)论“代”、论“本”意识的确立,与“审其源流,识其正变”一致,也与格调派倡学汉魏盛唐高格古调、反对宋人单纯摹拟唐人字句有关。只有总体考察每一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特色,才能把握诗歌发展与流变的历史,只有辨清诗歌的体格气象,才能把握住诗歌的本体精神。
作为这一理论最好的实践就是《辨体》对“三百篇”到晚唐诗歌进行的评述。其在《凡例》中说“《辨体》中论‘三百篇’、楚辞、汉魏、六朝、唐人诗,先举其纲,次理其目”,“论汉魏诗体浑沦,别无蹊径,然要其终不免有异,故先总而后分;至唐人则蹊径稍殊,体裁各别,然要其归则又无不同,故先分而后总。若李杜,则皆入于神,韦柳则并移冲淡,故亦先总而后分。至元和、晚唐,则其派各出,厥体甚殊,故但分不总也”。由纲举目张、总分有序、注重比较所体现的系统性,应归结于总体把握诗歌发展流变的思想。与传统表述形态的诗话,或纪事,或随意地谈感悟相比,《辨体》是一部系统性较强的论述诗歌发展流变的专著。
许学夷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从《诗源辨体》,我们既可以演义出明中后期诗坛理论争论的实况,又可见到明清诗歌理论的接轨之处。它的价值与意义,仍有待于发掘,它的光辉不应被历史的积尘所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