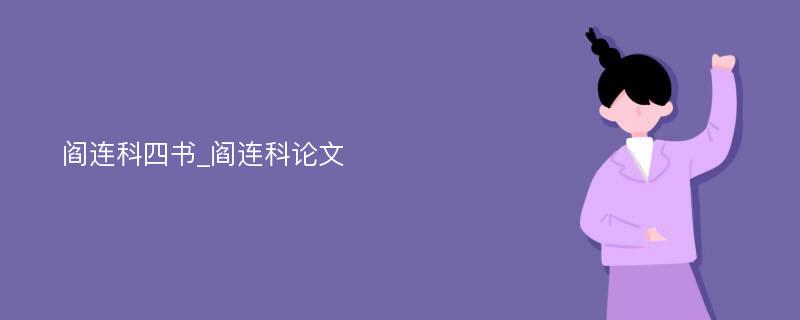
阎连科的《四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阎连科论文,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阎连科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四书》,印制了“亲友赠阅版”,我有幸得到一册。我想,得到这赠阅版者,人数应该也颇不少,所以我不妨来谈谈读后感。何况我深信,这部多少有些奇特的长篇小说,或迟或早,是广大读者都能读到的。但我先要说一句:这“亲友赠阅版”校对功夫不大到位,错讹处时有所见。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地点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劳改农场。在这里劳改的“罪人”,原本都是学术文化界的“精英”。当然,小说中没有出现具体的年代,也没有出现“劳改农场”的说法,但这些读者自能明白。小说中罪人改造的地方叫“育新区”,具体在小说中出现的,则是育新区的第九十九区。小说的叙述,亦真亦幻,高度抽象同时又极其具象,十分荒诞同时又异常真实。小说中人物都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姓名。几个主要人物依他们先前的某一种社会身份命名。“学者”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学者;“音乐”原来的身份之一是钢琴家;“宗教”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基督教徒;“作家”原来的身份之一是作家;“实验”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实验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以其生理年龄命名,这就是九十九区的管理者“孩子”。阎连科别出心裁,把这九十九区一百几十号文化罪人的管理者设置为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孩子并且是这里惟一的主宰者。
小说以《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新西绪弗神话》四部分组成,故称《四书》。前面三部分,在小说中交织着出现,构成小说基本的结构方式。最后一部分《新西绪弗神话》,是作为最后一章(第十六章)出现,只有数千字。这四个部分,有三个叙述者。《天的孩子》集中叙述孩子的故事。阎连科没有按照那年代劳改农场本来的“管教”方式来叙述这育新区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第九十九区像是一个原始部落,而最高统治者孩子,像是一个酋长、一个头人。《天的孩子》的叙述者,身份不明。《故道》和《罪人录》,叙述者都是小说中的作家。作家在小说中是罪人之一,但他同时又是孩子安插在罪人中的耳目,负有向孩子秘密报告众罪人不轨言行之责。《罪人录》就是作家以告密者的身份向孩子打的报告。作家卑鄙龌龊,但又并未彻底泯灭天良。他在以告密者的身份为孩子写《罪人录》的同时,又在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写《故道》,真实地记录这育新区发生的故事。在小说中,学者一直以紫药水写一部书。直到最后一章,读者才知道这部书叫《新西绪弗神话》。小说最后一章的数千字,就是这部书的绪论。学者写的这《新西绪弗神话》,是以随笔的方式表达哲学性思辨。阎连科将这作为最后一章,当然有“卒章显其志”的意思,是在借小说中人物之手,表达自己的理论思考。《罪人录》在小说中虽多次出现,但每次篇幅都很短。《新西绪弗神话》就只有最后一章的数千字。所以,小说的主体部分,其实是由《天的孩子》和《故道》构成。
据阎连科作为后记的《写作的叛徒》中说,《四书》的封面来自鲁迅《彷徨》的封面,“四书”二字也是从鲁迅的手迹中摘取,并说这是出版者执意坚持的。《四书》封面是整体的枣红色,没有任何图案装饰,正上方竖印着“四书”二字。这两个字确实是鲁迅的字体,但《彷徨》的初版封面,似乎并不如《四书》这样,不知出版者根据的是何种《彷徨》版本。既然阎连科称写作此书的自己为“写作的叛徒”,说明他认为这部小说是颇违常规的。阎连科在后记中说,此书出版前不得不有许多删节、修改。原稿如何不得而知。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亲友赠阅版”,在叙述方式上,确乎“怪异”,有些不合常规。但我觉得,也并没有“怪异”和“违规”到可称作者为“写作的叛徒”的程度。《四书》并不难把握和理解,也并无明显的阅读障碍。对我来说,它还是好读、好懂的。
二
读小说,我首先关注的是语言。如果语言不好,如果语言没有特别的美感,如果语言对我没有吸引力,什么结构上的突破,什么思想上的创新,都是哄骗人的东西。汪曾祺先生说得好:“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也可以说,语言的粗糙就是思想的粗糙。至于语言粗糙而结构精致,那就像用草绳绣花,会是怎样的货色呢?令人欣慰的是,阎连科的《四书》,在语言上有着独特的追求。在我的印象中,阎连科本就是语言意识强烈的作家,一直在寻找一种适合于自己的语言。这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素质。《四书》吸引我读下去的,也主要是语言。小说最先出现的是《天的孩子》。这是开头:
大地和脚,回来了。
秋天之后,旷得很,地野铺平,混荡着,人在地上渺小。一个黑点渐着大。育新区的房子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地托着脚,回来了。金落日。事就这样成了。光亮粗重,每一杆,八两七两;一杆一杆,林挤林密。孩子的脚,舞蹈落日。暖气硌脚,也硌前胸后背。人撞着暖气。暖气勒人。育新区的房子,老极的青砖青瓦,堆积着年月老极混沌的光,在旷野,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光是好的,神把光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样分开。暗来稍前,称为黄昏。黄昏是好的。鸡登架,羊归圈,牛卸了犁耙。人就收了他的工了。
这样的叙述语言,以一种陌生的力量撞击着我的审美习惯,像一种麻辣食物刺激着我的味觉。这描绘的是一幅油画,“浓油重彩”。这样的叙述语言远离甜俗,也并不能称为高雅,倒是有几分土气。《天的孩子》的叙述者,常常让我感觉到像是黄河岸边的一个老农。句子极短,句号极多,甚至把句号用得违背文法规范,是《天的孩子》基本的叙述方式。阎连科在《天的孩子》这一部分,刻意追求一种生涩、凌杂、峭拔的美学效果。用“粗重”来形容落日的质感,用“一杆一杆、林挤林密”描述落日的光线,都堪称新鲜。《天的孩子》的部分,还有一种特点,就是反复。同样几句话,同样一种意思,往往用短促的语言,反复说,反复表达。短句给人以简洁、急促的感觉,而反复则给人啰嗦、冗杂的感觉。这两种矛盾的感觉同时产生,便使叙述别有意味,或者说,便使叙述有了怪味。再举一例:
人就翻地,散在田野。一早起来,人就翻地。吃了早饭,人就翻地。到了午时,人就翻地。排开来,是第九十九区。上边说,把分散在黄河岸上的人、地、庄稼,命为育新区吧。就有了育新。上边说,把区的人、地编排号码,便于改造惩治。天管地,地管人。让他们劳作。人有他人来指派。他人就在此编了一区、二区……直至第九十九区。上边说,这是好的,让他们劳作。可以奖惩,可以育新。就让他们日夜劳作,造就他们。不管他们原在哪儿,京城、南方、省会、当地;原是教授、干部、学者、教师、画家、学府(富)五车,才高八斗,尽皆云在这儿劳作造就,育培新人。三年二年,五年八年,简或一生。
反复是《天的孩子》这部分叙述的常见现象。叙述急促而反复,便如山泉跳跃着向前,却又遇阻而回旋,或者说,像条奔腾的小溪,不停地打着漩涡而前进。《天的孩子》在叙述上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频繁使用三字句和单音词。句子常常短到只有三个字,有时候,竟把一个完整的单句硬从前面三个字处断开,像是在说快板书。至于一字一词的单音词,又往往是名词或形容词的动词化。现在举一个频繁使用三字句的例子:
可上边有话说,国家有难了,是被外国人、西方人,勒了国家脖子才饥馑大饿的。国民和国人,都应恨那外国的——西方大鼻蓝眼的。都应为国家——度难把裤带束紧一圈儿。育新区,由每天二两供给改为一两了。孩子管着粮,每周发一次,一人一牙缸的红薯面,约为六七两。有这每人每天一两粮,人就饿不死。饿不死,也决然难活成。冷得很,屋里如旷野。风可卷进人的骨髓里。卷进人的心。冷又饿。有人就出来,看那没有光的天。天上只有云,阴的冷,人把所有衣服穿身上。有人披被子,走到哪,都把被子裹身上。因为饿,格外冷。因为冷,格外饿。冷饿到极时,就有人,活过今天不说明天了。明天死,今天也不愿冷饿到极处,把半牙缸黑面取出来,到一个避风无人的地方全煮了。煮成糊,全喝了,用指头去刮碗里留的糊渍汤。又用舌头去舔碗。吃了这一顿,身上暖和了,到来日,别人煮汤他就只能看着了……
三字句的频频出现,使叙述给人以参差感。单音词的经常出现,也产生同样的效果。下面举一个《天的孩子》中单音词的例子:
……天空依然发白光,白里含黄金。暖烫的白,在空旷大地的冬日里,没有风,只有寂的闷。
下面加点的字,都是他人一般不会如此使用的单音词。超短句、三字句、单音词,都是为了让读者产生参差、生涩、凌杂、峭拔和急促的感觉。而之所以要追求这样一种美学效果,显然与孩子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有关。某种意义上,孩子才是《四书》的主人公,才是阎连科最倾注心血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阎连科的哲学思考,或者说,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主要通过这个人物表现的。——这个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中确实是很独特的。
三
前面说过,《四书》其实主要由《天的孩子》和《故道》两种叙述交织而成。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叙述风格。《故道》是以小说人物作家的口吻叙述的。这种叙述不像《天的孩子》那样怪异,比较合乎常规。但《故道》的叙述语言仍然是精细、考究的,并且也时有尖新之语。粮食生产大放“卫星”的荒诞不经、大炼钢铁的荒谬绝伦、大饥饿中的惨绝人寰,主要是在《故道》中表现出来的。如果说阎连科在这里让我们心灵震颤了,让我们精神恐怖了,让我们痛苦地思考了,这首先是因为他用精细、考究的语言,表达了那种荒诞、荒谬和苦难。粗糙和劣质的语言,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的。
“懊恼厚在脸上,如一块城砖砌在半空里”;“从房里传来累极的鼻鼾声,泥泞泥黄,如雨天滞在土道上的浆”;“他问我时嗓子里似乎有些抖,说话急切,声音沙哑,仿佛是他自己用手把话迅速从他嗓子里扯拽出来”……这一类的语言在《故道》中时常见到。比喻新奇而妥帖,因而十分富有表现力。顺便指出,《故道》的叙述语言虽与《天的孩子》大有差异,但将单音的名词或形容词动词化,却是两部分都常见的。说《故道》的叙述语言精细、考究,并不只是因为时有这类奇句。在总体上,《故道》的语言都是精雕细刻、绘声绘色的。
《四书》中的集中营被称为育新区,即“国家”要在这里把那些罪入改造成所谓“新人”。结果当然适得其反。这些本来的专家、教授,这些本来的文学家、音乐家,这些本来的读书人,在这育新区里,道德直线滑坡,精神迅速堕落。他们身上积淀着的“文明”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快速变质。《故道》部分对这一过程有精彩的叙述。由于检举揭发他人有奖,有“重大立功表现”还可以获得自由,“在这育新区,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检举另外一个人”。《故道》中有对“捉奸”场景的叙述。罪人自然有男有女。男女长期一起生活难免发生私情。而如果捉住正在通奸的男女,就是大功一件。于是,罪人们都渴望着能有一对正在幽会的男女落入自己手中。“在区院的东边围墙下,我俩看到了窝在那儿的一对人,蹑脚过去把一柱灯光突然射过去,看到的却是我们排的另外一对男育新,也猫在那儿捉别人的奸。我们朝围墙后边走,又看到了墙下有人影在晃动,把灯光射过去,竟又看到了三排有个男罪伏在草地上,问说干啥儿?答说听说区里有奸情,希望自己捉到可以立个功。我们三个人一道朝着前边一片树林走过去,人还未到树林边,有四柱灯光同时射过来”,原来这又是一些也在捉奸的人。“那一夜,到月落星稀时,人都有些冷,觉得天将亮了应该回去了。大家都朝区里回,才发现出来捉奸的男罪共有六十几个人,占九十九区一半还要多,最大的六十二岁,最小的二十几,排在一起,队伍长长的,如一条游在夜野的龙。”这样的场景当然未必真实出现过,但它比那些真实出现过的场景更“真实”。
比真实出现过的场景更“真实”的,还有《故道》中作家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小麦的场景。这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为了种植出几株可以晋京献礼的小麦,作家不停地用自己的血为小麦施肥。这一过程叙述得细腻绵密,也读得人心惊肉跳。
……我把右手食指上捏着血口的拇指顺便拿开来,让刚刚凝住的血口再次张开嘴,血滴再一次涌在指尖上,滴在水碗里。每一碗水里我都滴入两到三滴血,每一株干叶的麦苗我都浇了两碗带血的水。血滴在清水碗里时,先是殷红一珠,随后又迅速浸染开来,成丝成丝地化在水里边,那碗清水便有了微沉的红,有了微轻微轻的血腥气。我把这血水倒在麦苗周围的浇坑里,待水渗下去,用土把那浇坑盖起来,并用手把浮土拍实稳,使旷风直接吹不到麦苗根部去,麦苗又可以透过那土的缝稀(隙)呼气和吸去(气)。
第二天,再去观察那两株麦苗棵,黄叶干叶没有了。那两株麦苗的肥壮黑绿比别的土质好的麦苗更为厚实和鲜明,且它的麦叶似乎也有些狂起来,硬起来。别的麦叶都含着隐黑弓状地顺在地面上,可它们,有几片叶子如不肯倒下的铁片剌剌地直在半空间。我知道它们接血了,那血生力了。我就这样侍奉供养着我的麦……
这只是以血浇麦过程中的小小片断。以血浇麦本身固然有震撼人心的可能,但如果叙述得粗糙、平庸,就非但不能动人,反而会让人觉得别扭、矫情。在这方面,阎连科之所以做得很成功,就在于其叙述语言的精细、考究,就在于他把这一荒诞的过程叙述得细腻、绵密,从而使每一个具体情境都纤毫毕现,产生一种直逼人心的“真实”。以血喂养小麦便能让小麦长得异常茁壮,便能让麦粒像玉米粒那么大,这是否有科学上的依据,已毫不重要。这一行为本身已具有象征性。它极其有力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心智上的迷狂、错乱和愚蠢。也可以说,以血浇麦,是对那时代无数迷狂、错乱和愚蠢行为的“概括”和“抽象”。当然不只是以血浇麦这一件事具有象征性。《四书》中捉奸的场景,孩子用奖红花和红五星来治理罪人的方式,以及人们在大饥饿中的种种表现,都具有象征意味。也不仅仅是这具体场景、具体事件具有象征意味,《四书》总体上就追求一种象征性。在一定意义上,阎连科以亦真亦幻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寓言,以无数真实得令人颤栗的细节支撑起了一个寓言。
四
育新区以“育新”之名,摧毁着人的道德观念,迫使人突破道德底线。当大饥饿来临时,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份品性便无可挽救地变质。人身上那份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形成的,要变质,却又快得很。饿上三天、五天,这种品性便可能变为自己的反面。人本来是禽兽之一种。在漫长的过程中,人类身上一点一滴地产生了“人性”。人猿揖别后,人与禽兽之间,便有了一条万里鸿沟。这万里鸿沟一经产生便不会消失,只不过其显示的意义会发生巨变。人们习惯于认为人性——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是会消失的。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人性一经产生、形成,便永不会消失。在常态中,人性意味着“文明”,意味着区别于禽兽的理性、智慧,意味着禽兽所没有的道德禁忌、礼义廉耻。而在非常态中,人性便可能变质。但这种变质,不是变化为“兽性”。当人性变质时,人不是堕落到禽兽的水平,而是一定沉沦到禽兽之下。当人猿揖别后,人要么居于禽兽之上,要么沦于禽兽之下,而决不可能回复为禽兽。离开了禽兽世界的人,永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界。所以,变质了的人性,不是兽性,只能称之为“魔性”。当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发生变异、走向反面时,人就成了魔鬼。阎连抖的《四书》,展示了在惨烈的大饥饿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如何变异为魔性,人怎样变成了魔鬼。
但《四书》的主旨却又并非在揭示“人性恶”。《四书》毫不含糊地表现了人身上的魔性,但作者更感兴趣的,却似乎是人身上的“神性”。《四书》尽情地写了在特定情境中人所表现出的恶,却又让我们看到这恶中显示着善。年轻美丽的钢琴家,为了得到半个馒头、一把黄豆,不惜向那么肮脏丑陋的男人出卖肉体。然而,她付出了全部的尊严得到可怜的一点食物,却又并不肯全部塞进自己的辘辘饥肠中,总要偷偷塞一部分给学者——自己的情人。“饥饿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学会憎恨”——这是艾青《乞丐》一诗中的句子。饥饿确实是可怕的。它使一个年轻美丽的钢琴家似乎彻底丧失了羞耻感。然而,饥饿的力量却又并非对任何人都是无限的。它能摧毁许多被称为“文明”的东西,但它却无法摧毁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它能改变许多被称为人性的东西,但它却不能令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变质。当女钢琴家木然地向那个肮脏丑陋的男人出卖肉体时,她仿佛从人变成了魔。然而,当我们明白她这样做的目的中也包含着为情人挣一点救命食物时,她的形象又顿时圣洁起来,放射出神性的光辉。
人性变异为魔性,魔性中又有着神性,这种现象在作家这个人物身上也同样发生了。作家负有暗中监视其他罪人并向孩子汇报的使命。学者与音乐的私情就是他揭发的,这使二人遭受残酷的凌辱、迫害。然而,在作家的内心深处,又始终有着负罪感,又有着对自身罪孽的忏悔和对赎罪的渴望。当其他罪人对他施以惩罚时,他没有怨恨,只有心灵的畅快。最后,他竟然烹煮自己的肉,骗饿得要死的学者吃下,并以自己的肉祭奠死去的音乐。作家内心深处的善,还表现在《故道》的写作。当他在写着告密的《罪人录》时,还同时写着记录育新区真相的《故道》,这也是作家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神”在一开头就出场了:“光是好的,神把光暗分开。”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的叙述。读完全书,我才明白,这并非一句随意之语。《四书》中最先出现的是《天的孩子》,《天的孩子》中一开始就有神的光辉。而这孩子,最终也皈依了神。孩子才是阎连科精心塑造的形象。这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显得十分另类。用那样一种怪异的语言叙述孩子的故事、塑造孩子的形象,也是为了叙述语言能与孩子的形象吻合。孩子作为第九十九区的“酋长”,当然也恪尽其政治职守。但是,始终有着一种灵魂深处的善在阻止他走向穷凶极恶。他驱使罪人的方式也十分奇特。每当他需要罪人们配合他的重大行动时,便以自我伤害相要挟。当音乐试图向他出卖肉体时,他在跪着谢绝的同时,仍然让音乐带走一点食物。收缴上来的几册讲述基督教故事的连环画,使孩子走近了基督教的神。最后,彻底觉醒和悔恨了的孩子,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样的结局理应让我感动。但对我来说,更希望这孩子在现实中以一种世俗的方式为自己赎罪。如果他带领这些罪人走出集中营,冲向检查站,并死在“专政”的枪口下,我会更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