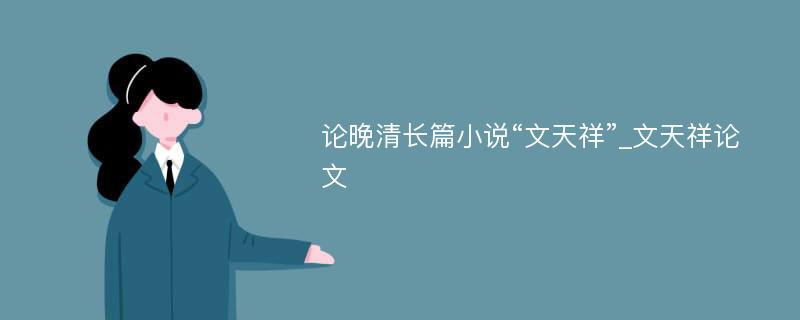
评长篇历史小说《末朝顶梁柱——文天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顶梁柱论文,长篇论文,历史小说论文,文天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长篇历史小说《文天祥》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湖南曾为此专门组织作品研讨会,认为是一部内容充实、主题鲜明、艺术上较为成熟的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同时是一部讴歌民族英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形象化教材。作者杨友今作为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十年磨一剑,为祖国文学事业默默奉献,实在可钦可敬。本刊特发表评论两篇,以期进一步引起读者的关注。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读完了《末朝顶梁柱——文天祥》这部小说。在目前纯文学倍受冲击,高雅严正的创作题材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文化背景下,杨友今先生积10年艰苦努力之功,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爬梳卷帙浩繁的史料,从中精选丰厚深刻的创作题材;艰苦跋涉,行程数万里,实地考察文天祥生前生活和战斗过的许多地方,捕捉历史的审美信息,三易其稿,提练加工成这部长达46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为我国精神文化宝库添加了一颗璀璨夺目的艺术明珠。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选德同志一直关心该书的写作,并在百忙中抽空写序,表现出对文艺事业的关怀,对基层文艺工作者的热情支持。湖南文艺出版社鼎力支持其顺利出版,实在是一件嘉惠士林,泽被后世的大好事。
13世纪中叶,是一个严酷而伟大的时代。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血雨腥风,壮烈激昂的抗元斗争,造就了一代爱国英雄文天祥。700多年来,他那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和正义之举,一直激励人们奋发进取。《文天祥》作为我国第一部集中描写文天祥生平业绩的长篇小说,是作家辛苦不同寻常、呕心沥血精雕细刻出来的“工夫型”力作,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化教材,其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小说以其丰富翔实的历史事实为基本素材,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恰当处理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关系;巧妙构设情节,匠心独运地塑造了成功的艺术形象;将文天祥充满坎坷与艰辛的人生遭际、赤胆忠心报国为民的豪迈情怀与丰功伟业、英勇悲壮至死不屈的人生操守,同宋末元初风雨如晦、复杂多变、矛盾多端的历史发展紧相结合,谱写了一曲高昂激荡、美丽动人的爱国主义壮歌,达到了“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的艺术高度,具有强烈的美学力量。而这,正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作品最为突出鲜明的主题和不可磨灭的审美价值。从中,正表现出作家庄严的使命感和神圣的社会责任意识。
依我看来,创作一部成功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历史小说,并非一件易事。较之于一般的创作活动而言,作家的责任更重,难度更大,所费心机更多。因为作家必须把握历史小说创作的内在的特殊规律,在人物形象、艺术语言、情节结构等各方面,体现出历史小说的特殊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创作背后隐匿着比生活真实更为严肃庄重的历史线索问题,给创作带来了特殊的规定性。这种制约是作家必须遵守又不得不加以突破和超越的。因而从内容到形式都会打上一种尊重历史的印痕,稍不留神,便会形象无力、苍白泛味,主题枯燥、人物说教,以至于近乎历史事件的翻版、再现。而综观长篇历史小说《文天祥》,其成功之处是很多的,特别是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及两者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在作家创作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而又不违历史规律的问题上,给人的启示是很多的。
一、深沉厚重的历史感。
历史材料的积贮,是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第一源泉,而艺术技巧的运用,创作手段的选择等,是完成创作的途径。最终呢,在于表现一种历史意识,以此揭示作品从丰厚繁多的史料中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也许,这正是历史小说的一个特点。长篇小说《文天祥》在这方面是很杰出的。作家通过作品所表现的历史感是深沉的、厚重的。作家花数载功夫,探究史料,实地考察,占有,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熟悉了解了与主要人物相关的历史,具有史家的胆识和眼力,为写出成功的作品打下了基础;同时,作家有自己的历史观,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筛选素材,使所描绘的生活具有时代感、真实感,从中能使读者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从小说可以看出,杨友今先生对文天祥的诗文、哲学观、人生观、政治道德观等,均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研究,因而在很多地方能够将文天祥本来较为复杂的思想意识融汇到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之中,使文天祥这个人物血肉丰满地站在读者面前。确实,从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材料中取出题材,提炼主题,写出主要的事件、人物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并刻意描摹其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历史真实的还原,历史感、真实感成了历史小说的基础,既能反映出历史的本质,表现一种历史精神,又能吸引人、打动人、陶冶人、提高人;尊重历史,又有别于历史传记,能在兴感怡悦的基础上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天祥》所写的基本事件与史书大体吻合,既写出了文天祥一生的坎坷经历,包括其读书、为官、抗元等主要活动,交友、爱情等日常生活,再现了南宋朝廷的腐败堕落,对太皇太后、理宗、贾似道等人物作了描写,又写出了元人的兴起与力图统一中国的雄心,包括忽必烈、白颜、麦术丁、素娜等人物的主要活动。在“狼烟滚滚”节中,便大致介绍了忽必烈及其祖父身世,是一部长轴的历史画卷。而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达到了理性的高度,追求文史哲融于一炉的审美价值,这是历史小说的最高境界。某一时期历史的发展结果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本身便源远流长地构成一种文化形态,文天祥的一生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线索,也莫不如此。文天祥作为宋末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思想深处,积聚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他至死不信佛、道教,信守自己法天不息的人生哲学,认为“人生”要在“不息”二字上孜孜不倦以求之,从不息中求进取,求改革,追求自我完善和国富民强。应该说,文天祥又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为国救难,为民除苦,自强不息的思想和意志,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因此,要成功地写出文天祥这个人物,本身便是在勾勒描摹一种文化传统及其流变。小说正是引人入胜地揭示了这样一个文化秘码。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时,渗和着抽象的逻辑思维、哲学思维,有生动的感性认识和创造灵感的浸润,也有理性化哲理化的蕴涵。这在介绍文天祥的诗文著作,写文天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时,有时虽不免存在一些略显多余的语句,但更多是通过人物本身来说话的。读完这部小说,不仅深深为文天祥这个人物形象所打动,同时也会深感周身浸泡在一种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文化精神之中,有文学的睿智、史学的熏染和哲学的启迪。在唐浩明先生的笔下,曾国藩的形象栩栩如生,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写出了曾国藩作为理学名卧心灵世界的变化。而相比之下,唐先生的创作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曾国藩本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其二重性格特征非常明显,且骨子里深深浸润着性格的矛盾和心灵的冲突、情感的两极,同时,曾国藩所面临的文化氛围更有特色。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下,运笔相对更为自由。而在杨先生的笔下,文天祥刚正不阿的性格一方面具有可歌可泣的一面,但又显得单一和纯净,要从历史真实中透出人物的美学价值,写出艺术魅力,在追求文史哲、真善美统一的前提下,将人物写出深度,有可读性,就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作家作了有益的探索。这种探索我认为也是成功的。
二、精雕细构的艺术美。
除了要有历史真实作基础外,历史小说必须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即作家必须融进自己的主体创造性,精雕细构地追求它作为小说而存在的文学性,这便是史与诗的融汇,哲理与诗情的互渗。作家必须在尊重基本的主要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基础上,广泛地恰当地开展联想和想象,倾注自己的情感,进行艺术虚构,可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根据人物情感与心理逻辑的必然,进行艺术化的推导和臆想。但是,建立在历史真实性之上的艺术创造,是有自身特殊难度的。作家的艺术视野自始至终受史料的局限,其审美创造力受到了制约,其联想与想象等艺术虚构手段也被历史真实所削弱。作家只有正确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程度,才能取得完满的审美效果。创造性不强或缺乏艺术虚构,则与史书无异,而太强太过呢,又背离了历史真实,人物的生存失去依据。这就给作家的审美创造带来了历史的定向作用,也许正是在这点上,《文天祥》的有些章节理性色彩浓了点,而艺术审美效果冲淡了,但这是不能苛求于作家的。在“东归历险”节中引《指南录》的材料及其议论均显得多了点。同时,由于受历史真实的制约,作家要以生动形象的语言传达历史信息,对其语言提练和表达功夫也就提出了更高要求,力避史家笔法,又不能充分脱开史家的眼力。而在《文天祥》这部长篇巨制中,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性上,作家是花了不少功夫的,可谓精雕细构,虽然局部还有不足,但整体上是成功的。衡量艺术真实性即历史小说有没有文学性,首要的是看作家选材的方式,投没有投入情感,是否有想象、联想,即能否放开手脚,进行能体现主体创造性的艺术虚构。从《文》看,这些方面是成功的,表现了作家的文学素养和美学原则,也是他熟悉和驾驭历史的艺术概括力之所在。
(一)采用大量灵活多变的对话和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以刻划人物。收复梅州时,巩信与鞠华叔的交战及对话,较为充分地表现了文天祥的人情味、战略战术及惜才爱才的思想,也表现了巩信的人性人情;在“募兵勤王”节里,通过文天祥与母亲的对话,“宁可朝廷负我,我不负朝廷”,一则突出了文天祥誓死报国的坚强决心,坚定志向,二则说明了文天祥从小受到了优良家风的熏陶,渗透进了亲子之爱等人性内容,但目的在于表现文天祥舍小家为大家的人生追求。在文天祥看来,“勤王”便是救国,事关重大,不得拖延,特约了江西制置副使黄万石来孤台商议,等了又等,一直不见黄的影子,“文天祥的拳头用力一挥,不慎碰在栏杆上,划破了皮,涌出了鲜红的血,他没有心思理睬,让鲜血流淌着”,这个细节,生动传神地表达了文天祥报国心切的真情,且用文天祥的心理活动及言语与黄作了对比。至于在写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时,许多细节描写与对话对人物刻画则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来,言为心声,且人的生活经历总是通过细微的动作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人物,基本线索有史可循,而其具体的言行,并非能详详细细有案可稽,作家在保持人物整体原貌的前提下,根据其性格发展进行细节和对话描写,对深化人物认识,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便是说,情节是性格发展的历史,细节和对话是性格合乎逻辑的延伸。
(二)巧妙采用了对比手法和环境描写以推进情节,烘托人物。主降、主和与抗元是对比,腐化堕落与革故图新是对比,而且在许多人物形象刻画上,是采用对比手法加以突出的,通过对比写出了不同的矛盾,从而推进了情节。从张世杰等最后被困于崖山脚下,无水可喝而面临性命之危时,老百姓却冒着危险偷渡港湾,自觉送水的事实,可看出当时大宋的百姓并没有失去知觉,失去自信,变得麻木,而是可组织的,可自立的,正如元军将领李恒所言,他们不愧为好百姓,只是没有好擎天柱,朝廷仅靠他们,也难以维持。从中,衬托出了文天祥的历史地位,与南宋朝廷的腐化形成了对比,这种笔法是很多的。正是在强弱不同,志趣有异的对比中,推进了情节,强化了主题。这种对比,尽管在很多地方很符合历史真实,但作家的组织与安排,本身体现了艺术性,是一种创造。至于以环境描写衬托人物,以景抒情,借物状人,在小说中虽少而精,但均很有力,起到了出神入化的作用。以冻云低垂雪花紧写“风雪夜行”;以微拂的轻风、啁啾的小鸟写“青梅竹马”;以风声霍霍,闪电耀眼,隆隆雷声写“曾凤除奸”;以皇宫歪歪斜斜、淳朴清雅的梅树,写“征程坎坷”;以北风飒飒,宫灯昏暗写“单骑见虏”;以后花园的幽静深雅,依崖傍壁而流的清溪写“一厢情愿”;以海风发狂,黑浪掀天写“福安沦陷”;以风卷松涛,乱云翻滚写“海丰军溃”;以霞光染天,天水血色一片写“崖山海战”;以天悲地惨,日色天光写“雪霜松柏”;这些精细的环境描写,状物传神,运用恰当,使人读后余味无穷,含蓄隽永,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三)历史发展是连续的、复杂的,作家在描摹这一过程时,不能平铺直叙,兼收并蓄,而应重点突出,进行能体现作家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段的选材和剪裁。杨友今先生的题材安排在这方面是突出的、成功的。正因为历史小说不能写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理应在其中有所侧重,有所选择,以突出某一事件,某一人物,表现深刻突出的主题;既要能保持历史发展的整体线索,又得从中体现出作家本人的历史观、美学观、文学观和主体创作功能。文天祥人生道路艰辛,作品开头没有直写主要人物,而是风雪夜行,从介绍曾凤父女,从恶劣环境的描写开始,为主人公出场,对抒写社会大环境作了铺垫,是一个始基。接着写曾凤父女入文仪家,顺理成章地对文天祥的成长环境作了介绍,家教原则即文天祥的处世基础,通过“不速之客”将文、武相联,并交代曾凤的身世,而此人正是对文天祥一生影响最大的,往下便写文天祥的志向、读书、教养、初恋、性格等等,篇幅不长,但对人物和整体抒写,对历史线索的把握,又显得十分重要。在整个情节中,“殿试夺魁”、鄂州失守、虎口余生、南剑聚兵,可以说是文天祥一生的几个转折点,作家重点抓住了文天祥人生道路的转折与变化,注意了笔法的放与收。“殿试夺魁”,是一个美好的台阶和起点,应试、答卷,处处表明了文天祥的宏伟志向,那报效祖国,为民请命的雄心,得到了表现。文天祥由此走上了为官之道,人生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鄂州失守”节有过渡和转换作用。承前看,文天祥从文而武,告别文职生涯,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新的人生征程;启后说,文天祥前期的思想、抱负、志向找到了归宿,有了用武之地,既是一种机遇、选择,又是必然的人生归趋。这是由文天祥博学多才的文化功底和报效祖国的志向所决定的;从时代背景看,交代了忽必烈等建立新王朝,稳定北方的统治时,始终末忘统一南宋的历史事实,交代了对4岁的赵昰即位等宋朝内部一系列较为复杂的人、事。既是历史转折点,又是文天祥人生的新台阶,说明文天祥从武职也是自然的事;从作品表达效果分析,简中有详,详略兼顾,既细密,又粗疏,这一节是整个情节的一个关节处。接着,作家重点把笔力集中在文天祥的抗元斗争上,这是作品的主体部分。到1276年“南剑聚兵”标志着文天祥将以独立的力量与元军展开激战,血雨腥风6年时间,占近1/2的篇幅,集中表现了文天祥的爱国精神。这种重点突出,详细分明的艺术组接过程,正是作家的一种艺术匠心所在。
(四)多线索推进,且主副分明,繁而不乱。文天祥一生的政治活动、抗元斗争及围绕在文天祥周围的人物群体,是主线,其它的南宋内部的斗争、元宋之间的冲突等均是副线。在整个情节发展过程中,主线突出、主次分明,随着主线的发展,逐步展开矛盾,层峦跌宕,错落有致,写出了宋、元两大统治集团与文天祥的矛盾。副线围绕主线而展开,有张有驰,有紧有松,服从和服务于主线的发展。可以说,文天祥一走上仕途,便与南宋统治集团展开了斗争。1259年至1274年,他宦海浮沉15年,三起三落,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但文天祥从中看清了仕途的险恶,人心之叵测,种种不幸遭际及无中生有的罪状都没有改变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没有改变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斗争意志。相反,正是在官宦的风雨之途中,练就和养育了他一以贯之的执法严,为人正,不怕恶,不循私的英雄气概,为他未来的人生之路立下了基础。小说的情节发展,在写文天祥募兵、聚兵的抗元斗争时,浓墨重彩,强化了主要线索。这种安排,对突出主题和人物性格,是有益的。在主副线交织展开中,将有关内容作了穿插性交代,使副线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换作用,如“牧草青青”、“四面出征”、“鄂州失守”等,对于整体艺术效果又不可缺少。
(五)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人物群象。除主人公文天祥这位爱国英雄的形象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外,围绕在他周围活动的一系列人物群,也呼之欲出,各具特征,富于艺术感染力。文学是人学,历史小说要突破史料的框限,其主要的一个途径便是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写出主要人物的人性深度和人性魅力,给人以艺术感召力。《文天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成功的,其中一个突出特征是人物群象鲜活生动,与主要人物交相辉映。吕武精明过人,深思熟虑,很有谋略:杜浒刚烈顽强,侠义,很有主见;刘洙幽默大度,不循成规:曾凤、水仙、金应、巩信、赵时赏等人的性格也很有个性;另外对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理宗赵昀、贾似道、张世杰、陆秀夫等也着了不少笔墨,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伯颜、素娜这几个人物,出场不是很多,但个性十分鲜明,给人印象尤深。忽必烈在最后与文天祥的几次对话及在对待文天祥生死问题上的犹豫态度、劝降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思索,几笔就将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忽必烈的爱才惜才及其复杂的思想写活了。
(六)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技法,继承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使复杂的材料组合有序,增强了可读性。在此基础上,同时进行了联想想象,倾吐了自己的情感,对一些史料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作了适当延伸、发挥,作家最善于写战争场面,虚构了崖山海战等许多大规模的战争细节。如果说历史真实是历史小说的基础,那么艺术真实就是其生命,只有两者的高度统一,才能显出作品文学价值、审美价值,才能做到真善美的统一,经过杨友今先生的精雕细构,完全可以说,《文天祥》是这样一部上乘之作。
三、雄浑高昂的主旋律。
在提倡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今天,要求作家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自身社会责任和艺术良心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后,爱国主义可以说是文艺创作的永久题材。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文天祥》所表现的爱国主义主题,可谓高唱了一曲历史的壮歌,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在这部历史小说中,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是通过豪迈激越的悲壮美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是一个悲剧人物,在他的悲剧命运里,浸泡着爱国爱民的情怀,贯穿着重人格轻生死的凛然正气,顶天立地,气贯长虹。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便构成悲剧。文天祥的悲剧正是这样的悲剧,虽说以个人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凝聚于他高尚的人格精神和恢宏的人格力量之中,但也总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因为文天祥的追求和斗争正代表了时代的方向和历史的发展动态。他的利益,便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他的生存与国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真可谓是时代的顶梁柱。而由于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壮志难酬,不能实现。在这种冲突中,便构成了悲剧。文天祥从小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养育了美好的人格。28岁时他出任地方官,任瑞州知州,打破常规,实行改革,办实事,造福于民,不闹个人矛盾,用人无私,勘察民情,修复碧落堂,重视文教,惩治皇甫嵩及其两个儿子的恶行,为民除害;在组建义军时,他四方张榜,八方招贤,自力更生筹措军饷钱粮,把全家的财产当成军费之资,连家中老小的私房积蓄都奉献出来了。从元军中投出来后,文天祥历尽艰险,一步拖一步地走,随时有蒙军哨卡,有性命之忧,但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坚韧不拔,不屈不挠,正是爱国爱民的坚强精神支柱给了他力量。他自脱险于真州,到达台州时恰好整整两个月。这是文天祥生命史上历尽艰险的两个月,是衔接他两次起兵抗元的两个月,是导致战争风云骤起并延缓南宋命运的两个月。1276年11月14日端宗入海行朝,在南全靠文天祥独木支撑。尽管元军使尽种种高超劝降手段,文天祥抗元不息的硬骨头精神,从来是硬朗的,没有丝毫的媚骨和奴颜,仍自强不息地组建军队,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练兵训将,一举收回了大片失地。即使在元被囚,文天祥仍不忘出逃复宋,不为富贵所动,威武所屈。他的民族气节,是高官厚禄不能收买的,刀光剑影也无以动摇,艰难困苦更难以变易。他的一片爱国心,一股民族气节,与生命共始终,直至最后讲了一句“死则死,没有言语”。这就是文天祥精神,这就是作品所着力表达的爱国主义主题,所奏响的文艺主旋律。
而细究造成文天祥悲剧的原因,元军入侵当然是直接理由,而南宋内部的腐化则是根本,因而矛盾的焦点在文天祥和宋朝统治者的对立、斗争。“鲁港败绩”没有直接写文天祥,但从侧面写出了南宋内部军队腐败混乱不堪的状况,写出了贾似道无才无德、沉湎声色,专横跋扈,骄奢淫逸的程度。南宋朝廷的政权,一直牢固地掌握在投降派手上,家国两分,只图保全性命,当了亡国奴也心甘情愿,与文天祥“家事国事天下事相比,我只能舍小家为大家”的思想背道而驰,与他精忠报国的言行形成鲜明对照。此后,焦山之役再度大败,南宋已丧尽元气,文天祥才得到入宫的圣旨,但一直受排挤,右丞相留梦炎对他处处有戎心,不但不重用,反而遭削兵权,明升暗降。正当文天祥组建“勤王”之兵准备与张世杰一同进驻临安时,可征途坎坷,阻力重重,太皇太后听信谗言,将他们一并排出临安,且投降的论调在狂欢。此时文天祥设计了一套完整而具体的挽救危机的方案,但以太皇太后为首的投降集团根本末予理会,最后文天祥只得被迫把军队拉到平江。即使在赵昰登基后,朝廷实为张世杰挟持,而张不顾主客观条件,不以大局为重,凭意气办事,不与文天祥配合,致使多次失去了时机。帝昺登极后,张世杰仍竭力排斥其他力量,生怕文天祥力量过人,具有非凡号召力,有害自己,超出自己,使自己失去力量。文天祥于1278年想见张世杰,写了三道奏疏,晓明事理,但因张世杰专权,文天祥始终未能入朝,终至兵败,另外,文天祥的悲剧,也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悲剧。当元将布里几见到唯独文天祥组织的军队比宋军不同时,也曾给蒙住了,认为宋朝本大有人在,皇帝为什么不发动他们来打却要乖乖投降呢?未必当亡国奴好些?他也觉得小皇帝可笑,“那么一丁点儿大,连自己都招扶不过来,怎么能治国安邦嘛……”,且不说赵昰,赵昺在那样的背景下立为皇帝,在历史的长河里多少有些幽默味,而下面的大臣却也一律讲究祖宗成法,大做官样文章,即使面临灭顶之灾也忘不了多余的礼节。这一点,文天祥是明白不过的,他深知宋朝的病根“是祖宗的专制之法,也深知要铲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病根极不容易,但既知其病而不医治,是常人都不会那么做的”。他“明知不可为而勉力为之,不可救药而竭力救之”,因而必然是悲剧的结局。在忠君和爱国的问题上,文天祥勇于冒死打破传统。皇帝降了,他偏偏一人不降。在“爱国”二字上,他不从皇法,不死守忠君。这种爱国情怀,正是对落后于时代进步要求,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封建宗法制的背叛,因而也就充分显示了自身独有的个性。而其本身,便是一种悲剧,一种必然的悲剧。在这点上,作家的态度十分鲜明。在《文天祥》中,豪迈激越的悲壮美,不止体现于文天祥一人身上,在他的其他战友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因而是一个悲剧人物群,如巩信等将士的光荣牺牲,便较为典型,其雄伟壮观的场面,真令人大为慨叹。文天祥的悲剧是历史与时代的悲剧。在这个悲剧的演示中,唱出了一首爱国主义的壮歌,在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为祖国的统一,为祖国的富强和进步而自强不息,顽强奋斗。
有人曾经认为,这些年来,号称“湘军”的湖南文学创作萎落了,滑坡了。今天,当读到《文天祥》这样的长篇巨著,想到湖南近年历史小说的创作所呈现的繁荣景象时,会不自觉地对文学的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当然,《文天祥》在许多地方还可进一步求得完美,理性色彩的消褪,心理描写的增多,史料的浓缩和主体创造性的放大等,都有待作家作深入探索,也必将进一步提高作品的美学品位。但是,决不能以此苛求于作家,也不能因此而削减对湖南文学光明未来的自信。相反,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工作者,能有如此毅力和精神磨砺文学,追求精品,本身便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作家创作出更多更美的好作品,期待文学“湘军”雄风不老。
标签:文天祥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宋朝论文; 南宋论文; 张世杰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