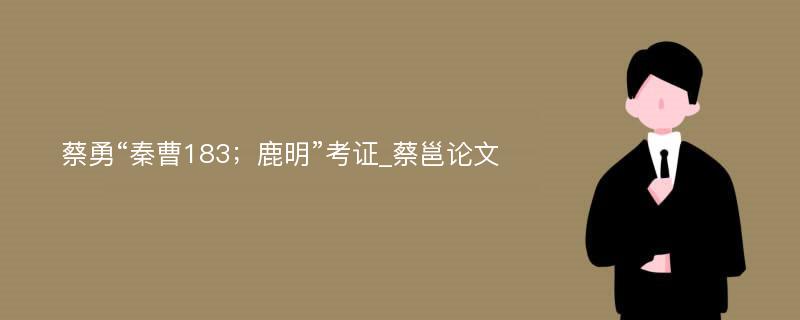
蔡邕《琴操#183;鹿鸣》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蔡邕论文,鹿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0)03-0141-05
《鹿鸣》是《诗经·小雅》中首篇,先秦时期《鹿鸣》作为雅乐被广泛运用到多种场合。时至汉代,雅乐《鹿鸣》虽被沿用,但使用的场合及次数明显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伴随着楚歌的兴盛和琴曲地位的提升,琴曲《鹿鸣》产生了。蔡邕在《琴操》中对琴曲《鹿鸣》的解题,内容上借鉴《鲁诗》诗说,但其解题和传统雅乐《鹿鸣》的主题迥异。要理清传统雅乐《鹿鸣》和琴曲《鹿鸣》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二者的流传作详细的考辨。
蔡邕《琴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琴曲解题专著,收录了歌诗五曲、九引、一十二操、河间杂歌二十一首等近五十篇作品。其中歌诗五曲部分所收录五篇作品的题目全部取自《诗经》,分别为《鹊巢》、《鹿鸣》、《驺虞》、《伐檀》和《白驹》。对于《鹿鸣》,蔡邕作了如下解说:
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旨酒佳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小人在位,周道凌迟必自是始。故弹琴以讽谏歌以感之,庶几可复歌:“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兽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伤时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而刺之。故曰鹿鸣也。[1]
在这里蔡邕将《鹿鸣》定性为刺诗,认为《鹿鸣》之诗是周大臣鉴于王道衰微,奸臣当道,忠臣被疏远的政局有感而作,其出发点在于对当政者的讽谏。然而对于《鹿鸣》一诗,《毛序》却做了如下解说:
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2]551
与蔡邕解说不同,《毛诗》将《鹿鸣》定性为赞美之诗,《鹿鸣》描绘的是一幅君主宴会群臣,君明臣忠,君臣相得的场景。显然蔡邕在《琴操·鹿鸣》中所作的解题和《毛诗》说法相背离,也和当时该曲的使用情况格格不入。前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乐考十》中引用了《乐书·琴曲》的如下材料:
自馀歌诗操引,不可胜纪,要其大致,亦不出乎此。然以诗推之,《鹿鸣》之宴群臣,《伐檀》之刺贪鄙,《驺虞》之美王道成,《鹊巢》之美夫人之德,《白驹》刺宣王之不用贤,与是说不类矣。岂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诡为之说哉?[3]1217
《乐书》的作者为宋代的陈旸,可见他已经发现蔡邕对歌诗五曲的解题和《毛诗》诗说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并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而仅是对这一问题作了“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诡为之说”的简单推测。
然而,仅以“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诡为之说”就对这一问题作结是很草率的。从诗学背景来看,蔡邕是《鲁诗》传人,对于《诗》中名篇《鹿鸣》应该很熟悉,他自然不会不加辨析地对“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诡为之说”加以采用。考察《鲁诗》学派对《鹿鸣》的解说,蔡邕对琴曲《鹿鸣》的解题更是渊源有自。司马迁是《鲁诗》传人、汉代大儒孔安国的弟子,其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写道:“《鹿鸣》者,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酒食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此言禽兽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也。”[4]可见司马迁对《鹿鸣》的解说和蔡邕所言大体一致,在语言上就有诸多重合之处。从二人的诗学背景和生存年代来判断,不排除蔡邕在对《鹿鸣》解题时借鉴了司马迁的成说。
除了蔡邕和司马迁,《鲁诗》传人中王符和高诱也对《鹿鸣》有过说解。王符在《潜夫论·班禄篇》中写道:“忽养贤而《鹿鸣》思”,指出《鹿鸣》诗的创作源于当政者对贤者的忽视和疏离。而高诱在注《淮南子·诠言》“乐之失刺”时写道:“乡饮酒之乐,歌《鹿鸣》。《鹿鸣》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怒而刺上者。非也。”对于该句,王先谦认为高诱“是虽用鲁说而以怨刺为不然”[2]119。
从以上《鲁诗》传人对于《鹿鸣》的解说可以看出,从西汉到东汉《鲁诗》学派一直是将《鹿鸣》作为刺诗来解说的。蔡邕在《琴操》中对《鹿鸣》曲所作的解说并非是对“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诡为之说”的采用,而是对《鲁诗》学派对该诗传统解说的继承。对此,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对《驺虞》题解的辨析时说道:“《琴操》五曲,唯《鹊巢》亡阙,《驺虞》、《伐檀》、《鹿鸣》、《白驹》并存,其三诗皆合古义,则以《驺虞》为邵女所作,亦古训相传如是。”[2]119
问题至此可以作结,蔡邕对《鹿鸣》的解释和《毛诗》的解说不同,其原因就在于,蔡邕在为琴曲《鹿鸣》作题解时沿用了《鲁诗》诗说,其解说渊源有自,并非是“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诡为之说”。然而,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蔡邕在对琴曲《鹿鸣》所作的题解仅仅由于他是《鲁诗》传人吗?琴曲《鹿鸣》和作为儒家经典《诗经·鹿鸣》之间是什么关系?先秦时期存在的歌诗传统就已经将《鹿鸣》作为雅乐使用,琴曲《鹿鸣》和雅乐《鹿鸣》又是什么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艺术天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且均有精深造诣。他和音乐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传世的典籍中保存了许多蔡邕和音乐的传说。作为一位音乐特别是琴曲方面的专家,自然对琴曲的演奏使用情况(诸如琴曲《鹿鸣》曲调的来源,琴曲的适用场合等)了如指掌。第二,蔡邕在对琴曲解题时并非简单借鉴成说,而是根据琴曲的实际情况对既有的解题有着选择和淘汰。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对《雉朝飞操》的解说。蔡邕之前即已经存在对琴曲《雉朝飞操》的题解,扬雄在《琴清英》中写道:
《雉朝飞操》者,卫女之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日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焉。傅母好琴,取女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邪?”言未卒,俱飞而起忽又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5]而在《琴操·雉朝飞操》中蔡邕却作了如下解说:
雉朝飞操者,齐独沐子所作也。独沐子年七十无妻,出薪于野见飞雉雄雌相随,感之。抚琴而歌曰:雉朝飞鸣相和,雌雄群游于山阿。我独何命兮未有家,时将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1]732
从作者、主题、故事的主人公、情节,二者差异很大,几乎看不出什么关联。蔡邕在为《雉朝飞操》解题时没有借鉴沿袭扬雄的成说,而是作了新的解说。
同样如陈旸在《乐书·琴曲》中所言,出现疑问的琴曲解题并非只有《鹿鸣》一首,《驺虞》、《伐檀》、《鹊巢》、《白驹》都“与是说不类”。
综上可见,蔡邕在《琴操》中对《鹿鸣》的解题,并非对《鲁诗》派诗说的简单沿袭,他对歌诗五曲的解说应该有另外的一个标准。而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则需要从《鹿鸣》曲的流变中寻找答案。
钩沉史籍可以发现,《鹿鸣》曲在汉代的流传情况主要见载于《汉书》、《后汉书》及《大戴礼记》中。《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列传》,有如下记载:
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於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童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6]
这段文字叙述的是益州刺史王襄为了宣扬风化,命王褒作了《中和》、《乐职》、《宣布》三首颂扬盛德的诗歌,并让“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据此可见推断,在汉宣帝时《鹿鸣》作为一个固定的曲调而保留下来,并可以根据需要配词歌唱。而《中和》、《乐职》、《宣布》为歌颂太平盛世的颂扬之作,属于雅乐正声的范畴,而对这三首诗进行演唱时选择了《鹿鸣》曲,那么此时的《鹿鸣》曲调也应是正声,其应用的场合为庄重之所。何武等先是在成都以合唱的方式进行表演,何武等人长安,又歌唱于太学,传入皇宫。
汉明帝刘庄是东汉王朝的清明之主,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的三十年间,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史称“明章之治”。汉明帝提倡儒学,注重刑名之法。《后汉书》中出现《鹿鸣》三次,都与汉明帝有关,其中两处出现在《后汉书·明帝纪》。第一次在永平二年,汉明帝幸辟雍,初行养老礼,其所颁布的诏书中写道:“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7]102
养老礼是汉明帝时复兴的礼仪。诏书对养老礼设置的意义、时间、参加人员、礼仪程序作了详细说明。其中对仪式上的乐舞作了如下规定:“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对此,李贤注云:“《鹿鸣》,《小雅》篇名也。《新宫》,《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声也。《燕礼》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7]102表演《鹿鸣》是乐工登台而歌,主要突出人的歌声,乐器伴奏起着辅助作用。此处《鹿鸣》曲的表演沿袭了先秦《鹿鸣》作为庙堂之乐的基本形态,包括表演场合、演唱方式等。
第二次在永平十年,汉明帝“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7]113。校官是汉代的地方学校,颜师古注写道:“校,学也。《鹿鸣》,《诗·小雅》篇名。从演奏的场合和人员组成来看,此处《鹿鸣》指的是先秦《鹿鸣》曲。
另外一处载于《第五钟离宋寒列传》,明帝永平年间出现灾异,钟离意上疏劝谏,其在奏疏中写道:“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也。”[7]1409此处《鹿鸣》指的是《鹿鸣》诗,从“《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可以得知,钟离意认为《鹿鸣》诗是正声,赞美之诗。
正史之外,关于《鹿鸣》的一处重要记载见于《大戴礼记·投壶》中,其文如下: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宾、拾声叡挟。[8]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投壶礼来源于射礼。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9]这是投壶比较早的记载。虽然投壶之礼产生时间较早,但《大戴礼记》出自西汉末期戴德之手,因而这段记载还是可以作为汉代史料来解读。根据《礼记·投壶》的记载可知,时至汉代雅诗中可以歌的有八首,分别为《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其中《鹿鸣》在先秦礼仪中属于升歌三终的曲目。王聘珍注写道:“案《仪礼》,乐凡四节。工歌《鹿鸣》、《四牡》、《皇华》,所谓升歌三终也。”[8]王聘珍所说的《仪礼》相关篇目,指《乡饮酒礼》、《燕礼》、《大射礼》,其中对于演唱《鹿鸣》的叙述大体相同。其中《乡饮酒礼》、《燕礼》记载,表演升歌三终,“工二人,二瑟”,《大射礼》是“工六人,四瑟”。《大射礼》级别高,所以,演唱和伴奏人员较多。表演《鹿鸣》等三首雅诗是以乐工演唱为主,采用合唱的方式,乐器伴奏则起辅助作用。汉代礼仪对《鹿鸣》的表演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继承的是《仪礼》的传统,《鹿鸣》作为表现欢乐、赞美之情的诗篇和曲调看待。
以上是关于《鹿鸣》在汉代流传的资料,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关于《鹿鸣》记载很少,正史和礼书中共计出现五次,其中两次是作为《鹿鸣》诗出现的,三次作为《鹿鸣》曲出现。和先秦时期相比,《鹿鸣》在汉代出现的次数明显减少。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以《鹿鸣》为代表的雅乐古曲在汉代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和传统雅乐古曲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汉代另一种雅乐曲调却勃然兴起。《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刘向的《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10]刘向明确指出,西汉时期新兴起的雅歌,其基本特点是声清调哀,以表现悲哀之情为主。
《礼记·乐记》称“丝声哀”,丝声指琴瑟之声,古人认为琴瑟这类弹拨乐器适于表达悲哀之情。从战国时期开始,琴受到士人的特殊关注,流传着许多琴师的故事,《吕氏春秋·本味》篇有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结知音的传说,桓谭《新论·琴道》篇有雍门周以琴打动孟尝君的大段叙述。既然汉代新兴的雅乐以悲哀为基调,因此,表演汉代新兴雅乐的乐器,琴曲也就成为首选。刘向《别录》写道:“君子因雅琴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11]337刘向生活的西汉后期已经把琴曲称为操,并且把它的基调定为闭塞悲愁,抒发的是抑郁之情。扬雄和刘向是同时代人,他在著述中提到的琴曲有《子安之操》: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乐。唯念眷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这是一则凄惨的故事。儿子因受迫害而投水,扬声悲歌,思念父亲。尹吉甫感觉到儿子生命的呼唤,援琴而抒发自己的感慨,《子安之操》是一首悲哀的琴曲。
扬雄著录的琴曲还有《雉朝飞操》,是傅母思念已故公主所作,也是一首悲曲。还有一首琴曲未出示名称,还是以悲著称,“援琴而鼓之,晋王酸心哀涕。”[5]320
扬雄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对音乐推崇雅乐而排斥新声。桓谭《新论·离事》云:“余颇离雅乐而更为新弄。子云曰:‘事浅易善,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宜也。’”[11]549扬雄对桓谭弃雅而为新弄采取讥讽态度,认为是浅薄之人所为。以此推断,扬雄所著录的三首琴曲属于雅乐,是西汉新兴的雅曲。
对于汉代的琴操雅曲,刘向《别录》有如下记载:
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赵氏者,勃海人赵定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净,少言语,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
师氏雅琴者,名志,东海下邳人。传云:言师旷之后。至今邳俗犹多好琴也。[11]327
刘向对于琴操雅曲的兴起作了历史的追溯,它的高潮出现在西汉盛世宣帝期间。在当时主持朝政的魏相的推荐下,勃海、梁国、下邳等地能够演奏琴操雅曲的艺人被陆续招进朝廷,不时地进行演奏。其中赵定除演奏琴操雅曲外,“时间燕为散操”,散操指民间琴曲。既然是琴操雅曲,不但曲调雅、取材也雅,往往多取古事。扬雄所录三首琴操雅曲都以古事为题材。桓谭《新论·琴道》篇提到的《舜操》、《禹操》、《微子操》、《文王操》、《伯夷操》、《箕子操》,都是古代题材,蔡邕的《琴操》也是如此。
《隋书·音乐志》记载南朝沈约奏答梁武帝萧衍时的如下言语:
至于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十篇。[12]
刘向《别录》所载的琴曲目录表明,汉代中后期,琴操雅曲已经在用于庙堂的正统雅乐之外别成一个系统,并且蔚为壮观,附于汉宣帝时期著名的雅乐琴师名下的曲目亦为不少,赵定、师志分别是七篇和八篇,龙德名下的琴曲最多,达到一百六十多篇。值得注意的是,列在最前面的是《乐歌诗》四篇,没有附于任何人的名下。既然后面提到的都是琴操雅曲,因此,《乐歌诗》四首也当属于此类,是琴操雅曲。从所处的位置判断,《乐歌诗》四篇所产生的时代早于后三者,并且很重要。沈约的上述话语都是围绕雅乐展开,包括音乐典籍和琴操雅曲。由此推断,《乐歌诗》四篇当是取自《诗经》的琴曲,即用汉代新兴的雅曲琴操演奏《诗经》的四首歌诗。如果并非如此,不会把《乐歌诗》四首置于如此显著的位置。蔡邕《琴操·序首》写道:
古琴曲有歌诗五首,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1]727
在此之后又依次罗列十二操、九引、河间杂歌。蔡邕的古琴曲歌诗指的是取自《诗经》的作品,沿用古词,并且把这类琴操雅曲置于其他各类的前面,在所用名称及排列次序方面与刘向的《别录》一脉相承,只是曲目数量稍有差异。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早在西汉后期,属于雅乐的琴操就已经把《诗经》的四篇歌诗作为表演的曲目。到了蔡邕所处的东汉后期,琴操雅乐取自《诗经》的歌诗五篇。刘向的《别录》、蔡邕的《琴操》,都将取自《诗经》作品的雅曲琴操称作歌诗,将之与其他雅曲琴操的名称相区别。从琴操的传承来判断,刘向《别录》的《歌诗》四首,应在蔡邕《琴操》首列的五首歌诗范围之内。至于哪首诗是《别录》所无,而《琴操》所有的篇目,已经无法认定。
《汉书·艺文志》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而刘歆的《七略》又以其父刘向的《别录》为基础。可是,《汉书·艺文志》没有专列琴曲,而是将各类可唱的诗称为歌诗。这样一来,从中无法找到琴操雅曲生成、传承的线索。琴操是与朝廷正统雅乐相区别、自我独立的一个系统,班固正统观念较重,这是《汉书·艺文志》未给琴操雅曲独立的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有赖于《别录》的相关记载,尽管留下来的文字很简短,却提供了考察琴操雅乐的重要线索。
作为汉代琴曲《鹿鸣》,它不再是先秦时代在重要礼仪上所演唱的《鹿鸣》曲,而是汉代琴人创造的新曲,它和汉代流传的先秦《鹿鸣》曲是并存的,但不再属于一个体系。这一点通过先秦《鹿鸣》曲的流传可以看出:“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生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东汉之末,礼乐萧条,虽东观、石渠议论纷纭,无补于事。曹孟德平刘表,得汉雅乐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习,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馀声不传。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鸣》一篇,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臣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鸣》,必歌《四牡》、《皇皇者华》,三诗同节,故曰工歌《鹿鸣》之三,而用《南陔》、《白华》、《华黍》三笙以赞之,然后首尾相承,节奏有属。今得一诗而如此用,可乎?”[3]1246
曹操生活的年代为汉末,比蔡邕稍晚。《琴操》作于东汉末年,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公元179年至公元190年)。而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曹操平刘表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而此时雅乐“惟《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馀声不传”,距离《琴操》编撰最多不过三十年。如果琴曲《鹿鸣》、《驺虞》、《伐檀》、《白驹》、《鹊巢》也为传统雅乐,其中《白驹》、《鹊巢》不会再短短三十年之间同时消失。同样,如果《琴操》中的五首琴曲歌诗是作为朝廷传统雅乐来整理的话,那么蔡邕在编撰《琴操》时一个最大的疏忽就是把《文王》给漏掉了。但是这种解释又不能成立,因为蔡邕作为汉末有着音乐天赋的大儒出现这种纰漏的可能性极小。
因而最合理的推测就是,琴曲《鹿鸣》和朝廷传统雅乐《鹿鸣》属于两个不同的雅乐系统。而《琴操》一书的性质及其内容也证实了这个推测的合理性。琴音以悲为美,琴曲多为哀怨凄婉之作。这点在《琴操》中鲜明的体现出来,其中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曲目都是哀怨之作,整部书呈现出浓厚的悲情意识。很明显这部书并非是蔡邕对汉代琴曲的简单搜罗汇集,而是经过他精心的选择和编排。其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符合琴曲哀婉的音乐特色。先秦雅乐《鹿鸣》很明显不符合这一标准,《琴操》中所收录的《鹿鸣》自然也不是先秦雅乐,而是汉代新创制的琴曲雅乐。
汉代朝廷雅乐《鹿鸣》是对上古音乐的沿袭,而琴曲《鹿鸣》则是汉代乐人的创造。如上所述,汉代传统雅乐日益衰落,琴曲的地位上升,创制琴曲成为当时一批歆慕雅琴之士的风尚。而在琴曲创作的过程中,借鉴《诗经》的歌诗,成为早期琴曲创造的一个重要途径。琴曲创作中对古代雅乐的最重要的借鉴之一就在于题目,即用雅乐古题命名琴操雅乐。这就是汉代出现了以《鹿鸣》、《伐檀》、《驺虞》、《白驹》、《鹊巢》为代表的歌诗系列琴曲的原因。这些琴曲虽然和雅乐古题重名,但是其实质内容和它们没有多大关联。至于蔡邕在《琴操》中对歌诗五曲的解释,则是根据《琴操》整部书的编写体例及琴曲的特性,在汉儒的诗说中选择较为适合的解说对琴曲题目加以阐释,其中对于《鹿鸣》的解释借鉴《鲁诗》诗说,其主要原因在于《鲁诗》诗说更能体现琴曲的特性,符合《琴操》整部书的内容风格,而并非仅仅取决于蔡邕作为《鲁诗》传人的诗学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