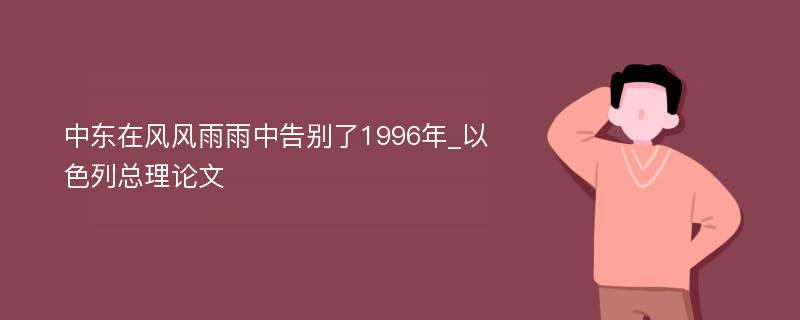
中东在跌宕起伏中告别199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跌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中东和平进程离开了它原定的程序和时间表,放慢了它的速度,某些方面甚至停滞和倒退了。人们忧心忡忡,各种力量行动起来,力图推动和平进程继续向前。和平进程之所以出现曲折,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变化。
一、以色列政局右转
1996年,以色列发生两件大事,影响了和平进程的发展。1、以色列人选择了内塔尼亚胡作为他们的总理,利库德集团由此重新执政。2、内氏组成了以利库德集团为主,联合宗教党和其他小党的右翼政府。基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倾向和各联合执政党的性质,内氏一上台就宣布:不把戈兰高地归还叙利亚,不同意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同意对定居点的冻结,等等,并且接连采取了若干强硬措施。内氏的强硬路线使在正常轨道上运行的和平进程紧急煞车,中东上空一时乌云密布。但由于各方的努力和克制,局势没有失去控制,冲突暂时平息。
与拉宾—佩雷斯的立场相比,无疑,内氏更右、更强硬,因而对和平进程的威胁更大,因为内氏是一名一贯主张“大以色列主义”的利库德集团的政治领袖。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内氏的作为较之他的前辈贝京和沙米尔则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在野4年的利库德集团在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调整。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的要求是迫使利库德集团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同样,内氏也只能顺应潮流,才能维持其统治。以色列人既然可以选择他,如果他不能为他们带来“有安全的和平”,那么他们也可以选择别的领导人。
二、急进三步,后退几何
“新官上任三把火”,内塔尼亚胡在摆平内部关系后,在和平进程问题上摆出一副决不妥协的冷面孔,从根本上讲,不仅是为了迎合当时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情绪,把自己装扮成以色列安全的“保护神”,也是为了向他的盟党表明:他将切实执行右翼政府的纲领。然而,人们也不难发现,内氏的举措带有明显的策略上的需要和投机成分。内氏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宣布中止和平进程,撕毁巴以协议(或许他内心有此想法)和各种条约、协议。因此,在阿以谈判中,如果内氏把拉宾—佩雷斯留下的基础作为起点,那么他的回旋余地将很小,或者说,没有;他必须为自己营造一个基点,那么在与阿拉伯方面的讨价还价中,他将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因此,内氏“急进三步”,很可能不是以此作为进击的出发点,而是作为后退的起点。后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在千呼万唤后,内氏被迫于9月4日在埃雷兹与阿拉法特举行会谈并握了手,会谈虽无实质性进展,但接触的渠道开通了,为以后的接触开了一个头。按巴以协议,以色列军队必须在1996年4月前完成在希伯伦的“重新部署”(即撤军)。佩雷斯借口以色列大选,推迟撤军。大选后,这个“烫山竽”留给了内塔尼亚胡。内氏以“最复杂的安全问题”为由,拒绝撤军,并设置重重障碍。希伯伦的特殊性在于:这里有犹太人的祖坟——麦比拉洞穴,犹太始祖亚伯拉罕等人安葬于此;这里有或许是全世界1600万犹太人中最具有民族沙文主义和宗教情绪、也是最好斗的400多名(包括儿童共512人)犹太人。对于撤军,他们的回答仅一个字:NO!政府不得不用3个营的兵力保护他们。作为继续和平进程的关键,各方竭力推动希伯伦问题早日解决,特别是阿拉法特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内外压力下,内氏不得不妥协。目前已接近达成最后协议,以军已在作撤出的具体准备了。
拉宾—佩雷斯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冻结定居点的。它完成了前政府遗留下来的一万套住房的修建;为建“大耶路撒冷区”,在耶城周围地区又新建了3892套住房。由此使占领区的犹太人增加了39%,达15万人。“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任何地方定居”是主张“大以色列主义”的利库德集团的一贯主张,因此,在此问题上,内氏步子决不会比拉宾政府小。扩建或新建定居点无疑给中东和平进程设置了障碍,使巴以矛盾中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更难解决;巴勒斯坦人失去了最宝贵的土地,就被逼上绝路,除了武装斗争,别无出路。定居点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恶性肿瘤,因此,包括以色列盟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致反对以色列的冒险政策,要求冻结定居点。内氏虽在此问题上表明了强硬立场,但是一方面他不会象贝京、沙米尔那样,对此放任自流,使之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把扩建定居点的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交给更右的基础设施部长沙龙;另一方面,扩建或新建定居点需要大量经费,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全国的认同,他的计划不可能完全实现。
最近,传出内氏有意与工党结盟的消息,虽立即遭到否认,但恐非空穴来风。如果今年6月工党领导人选举,鹰派巴拉克取胜,两党结盟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在以色列历史上,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事例屡见不鲜,两党结盟也有先例。当和平进程到了今天这一步,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条件出现了。如两党结盟,在议会将占稳定的多数,执政党受制于各联合小党的程度大大减弱,政治上的回旋余地扩大。然而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将取决于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
三、内塔尼亚胡的底线
内塔尼亚胡是国内强硬派的政治代表。他在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上的妥协,在策略上的调整,是不会背离他的基本原则的,他决无可能成为“佩雷斯第二”。他的基本原则就是他的3条底线。一、不放弃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在叙以谈判中,不存在归还戈兰高地问题。如果将来有一天,以军撤离戈兰高地,那可能是为建立非军事区的需要,叙军也应相应地后撤;如果将来有一天,叙军进驻戈兰高地某地区,那可能是经以色列批准的某种特殊安排,或者是租借给叙利亚的。总之,戈兰高地姓“以”,不再姓“叙”了。内氏这一立场与上届政府完全不同,上届政府是在原则上承认叙利亚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基础上与它进行谈判的。叙利亚当然无法接受内氏的强权逻辑。二、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同意在自己身边出现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是多数以色列人的想法,工党也只是在这次竞选的纲领中删去有关的条文。内氏最近提出波多黎各和安道尔模式,一种主权不完整的政治实体模式,遭到了阿拉法特反对。三、不同意分割耶路撒冷,重申耶城是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永恒首都。内氏限令关闭巴权力权构在耶城的办事处,开放神庙山隧道,其起初用意不在办事处和隧道本身,而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没有商量”。面对内氏的强硬立场,阿拉法特没有从“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立场上后退。
阿以双方将在戈兰高地、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耶路撒冷问题上展开新一轮的斗争,斗争的结果现在还很难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色列政局的变化,人民的意向以及国际社会的积极干预将决定斗争的结果。内塔尼亚胡能不能守住他的底线,令人怀疑。
四、制约因素
内塔尼亚胡手中没有一张王牌,可以确保他无阻碍地推行他的强硬路线,很多因素制约着他。
首先在国内,内氏毕竟只是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佩雷斯,出任总理的。这就决定了内氏政府是非常脆弱的,它的决策能力有限。利库德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异常激烈。这就决定了内氏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强有力的。
制约内氏的主要力量是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动向,人心向背。的确,有150多万选民投了内氏的票,但其中相当一部分选民,只是在他与佩雷斯两者择一之中,选择了他,因为他们认为内氏会给以色列带来“有安全的和平”,他们并不支持利库德的“大以色列主义”。但是,内氏的强硬路线导致和平进程受挫,阿以关系全面紧张,甚至发生流血冲突,“有安全的和平”在哪里?这部分人的态度发生变化或者军队态度的转变最能反映支持内氏阵营的分化,军人在投票的关键时刻支持了内氏,使他比佩雷斯多了29,457张选票。但是内氏并不信任军界,上届政府只是在得到军界的支持后,才得以与巴勒斯坦达成协议。这种不信任情绪在开放隧道后发展成一场真正的危机,事先军方并不知道要开放隧道,巴勒斯坦人上街抗议后,政府派军队进行镇压,军队成了政治家轻率行动的牺牲品。在希伯伦,在黎南部安全区、在戈兰高地、甚至在加沙地带犹太定居区都是这样。军政之间的危机据说已发展到“军事政变的危险增大”的地步。这场危机不一定会发展成军事政变,但它对内氏的决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以色列还有一股势力,支持和平进程的势力正在协调立场,加强团结,不断揭露内氏阻碍和平进程的行径,以“现在就实现和平”运动为主体的和平示威集会已举行多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在支持和平进程的努力中,有一件事引起了世人注意:以色列的总统只是作为超党派的国家统一的象征,其职责是礼仪性的。然而,现总统魏茨曼一反传统,8月25日宣布,如内氏再不会晤阿拉法特,他将邀请他在私宅会晤,内氏被逼,于9月初匆匆会晤阿拉法特。10月中,魏茨曼分别会见了阿拉法特和不愿与内氏会晤的穆巴拉克总统。魏茨曼的行动向世人发出了这样的信息:阿拉伯国家不要对以色列国(不是对内塔尼亚胡)失去信心。对此,内氏很尴尬,也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其次,在国际上,为内氏阻碍和平进程行径叫好的人不多,支持和同情在阿拉伯一边。西欧、俄罗斯等都公开谴责内氏的强硬路线,呼吁回到正常轨道上来。面对和平进程受挫的形势,阿拉伯国家加强了团结,他们协调立场,共同应付局面。黎巴嫩政府拒绝内氏“黎巴嫩第一”的方案,支持与叙利亚保持一致;穆巴拉克在以色列从希伯伦撤军前拒绝会晤内塔尼亚胡;侯赛因在华盛顿四方会谈中,没有旧话重提,而与阿拉法特协调一致。从全局上,阿拉伯国家一再声明:和平是他们的战略选择。表明了继续推进和平进程的决心。在具体问题上,既坚持了他们的原则立场,又有很大的灵活性。从而剥夺了内氏中止和平进程的口实,亦无理由把和平进程放慢的责任推到阿拉伯一边,内氏在国际上孤立了。
保持中东地区稳定是美国战略利益之所在,偏袒以色列则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克林顿连任后,不会改变美国的这一基本立场。在那些美国曾支持的原则问题上,如“土地换和平”,冻结定居点,戈兰高地、南黎巴嫩安全区和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上,克林顿也不大可能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预计在新的一年,内塔尼亚胡将面对更多的制约因素。
马德里和会已经过去了5年,由此开始的和平进程有僵持,有高潮,有曲折。但是谁也没有力量使它逆转,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