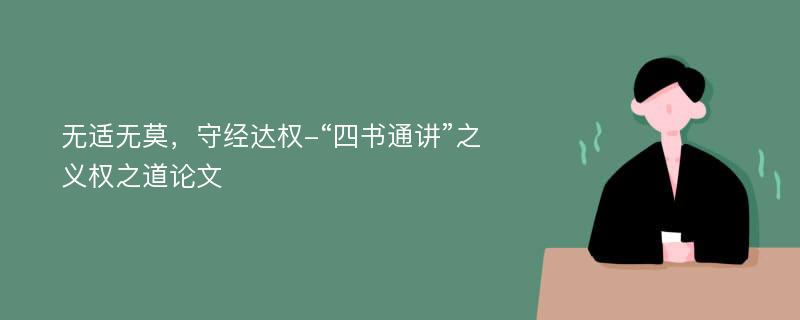
“四书通讲”(七)
无适无莫,守经达权
——“四书通讲”之义权之道
上海 刘强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许多人常将其概括为“仁义之道”。这无可厚非,但若细究起来,“仁”和“义”究竟并非一事。《易传》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显然以“仁义”与“阴阳”“刚柔”一样,皆为对立统一的 不同概念和范畴。所以,如果笼统地将“仁”“义”双称并举、等量齐观,自然有其约定俗成的道理,但也很容易造成对二者不同伦理特性和价值旨趣的遮蔽。“仁义”这一黏合度极高的词,其实有着某种不可“通约”的内在张力。而所谓“仁义之道”,也完全可以拆分为“仁道”和“义道”。“仁道”也即上一讲所揭示的“仁爱之道”,而“义道”的内涵,则可概括为“义权之道”。
“义者宜也”
就“义”字而言,要想明白其真义,必须先从字源学对其稍加追溯。“义”,正体字写作“義”,甲骨文已有此字。其义至少有四:
“左双权从小就是在呼兰区红旗村长大的,村里的亲戚朋友他都熟悉,必要时他带着站经理到村里进一步开发客户。”范好光说。
一曰“仪”。《说文解字》训“義”曰:“己之威仪也,从我羊。”“義”字从“我”,盖谓义出于己,由己决定;“義”字从“羊”,“羊”在“我”上,或与远古宗教祷祝仪式有关。段玉裁注:“義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从羊者,与美善同义。”这是对“义”的民俗学和伦理学解释。就此而言,“义”的行为也就是“美善”的行为。人有“义”心,正如人有“仁”心,皆可为“性善”论张本。
这样的判断实在让今人大跌眼镜,“三观尽毁”。其实,《论语》中很多一时不能理解的道理,只要放在实践中来个“情景还原”,便可豁然开朗。据《史记·孔子世家》载:
三曰“我”。董仲舒《春秋繁路·仁义法》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这是把“义”放在人我关系中考量,以此彰显“义”的原则性和自洽性。
四曰“理”。孟子在谈到“心之所同然”时,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谓理也、义也。圣人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又,贾谊《新书·道德说》称:“义者,理也。”“义者,德之理也。”这里,“义”又与“理”同义。后世义理之学盖由此开出。
此外,“义”字还与“礼”“节”相近,如《论语·学而》有子的“以礼节之”;《礼记·礼运》:“义者,仁之节也。”同书《礼器》:“义理,礼之文也。”《乐记》:“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皆是。同时,“义”还可与《周易》“变易”之“易”相联系,含有“变通”之义。如焦循《孟子正义》在论及人性所以能善之原因时,就说:“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有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岂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①这说明,“仁”与“义”是相伴而行、相辅而成的。种种解读,颇多殊趣。
相比之下,“义者宜也”不仅更易理解,也更能揭示“义”的本质内涵。这一训诂,道出了“义”作为一种“应然性”价值,与“时中”和“权宜”等“或然性”价值的内在联系。因为“义”与“宜”通,故“不宜”之事便是“不义”之事。就此而言,“义”是一种较有弹性的价值判断和处事原则,与“仁”共同构成了儒家所认可的人性基础和道德理想。
“神化”后的陶瓷张力笼罩在臣民身上,如皇帝亲临般时刻提醒烙尽职守与忠心不二,帝王的权力用陶瓷及其权力象征渗透控制旁人,这正是封建社会统治美学的特征。然后,当清廷大厦倾倒,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被赶下龙椅,官窑(御窑乃其最高级别)随之终结,但曾经附着在陶瓷身上的权力并未消失,依然拥有无限的空间占有力。比如那件在2005年拍出2亿多元的《鬼谷子下山》、南京博物馆镇馆之宝《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它们摆在面前,相信没有人会端起它瞧个底朝天。它们所透露的张力和威慑力,依然独一无二,尽管其中掺杂了今天人们同样在乎的金钱成分,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近它们。
而当下崔永元手撕演艺界黑幕,就源于冯导之流在巨大财富的诱惑下,早已贪婪成性的这帮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当下舆情一边倒预判),甚至是身败名裂之巨大风险,直接把本有宿怨未消,又敢和方舟子之流死磕到底的“平头哥”(獾的一种,有敢于和比自己强势的对手死磕到底的胆魄)给生生的惹毛了……本事件极有可能成为“利令智昏”所出的最大昏招的典型范例。
“义”是“无可无不可”的智慧
不过,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义”还代表着一种理性智慧。前面所引董仲舒的“反义为懵”,正说明一旦违反了“义”,人就会陷入昏昧懵懂,毫无智慧可言。在《论语》中,孔子对“义”的解读非常丰富,而其最终指向,则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智慧境界。因为“义者宜也”,故一切价值必须以“合义”为前提和基础。以下试就“义勇”“义信”“义礼”“义利”之关系稍做论析。
(一)义勇之辨。孔子虽然说过“勇者不惧”,但他对“勇”的价值认同,却是以“义”为前提的。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就是“义勇之辨”,成语“见义勇为”即由此出。见到合“义”的事而不去做,这是没有勇气的表现。换言之,不合“义”的事做得再多,也与“勇”无关,甚至有可能是“乱”。故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孔门中最好勇者莫过于子路,但孔子对他的批评也最多,诸如“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论语·述而》),“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等等。盖孔子以为,子路之“好勇”固然是一德性,然若不善加剪裁,则容易铤而走险,最终只能是“不得其死然”。子路后来的结局也印证了孔子的判断。有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义以为上”,其实便是“尚义不尚勇”。也就是说,义勇之间,义在勇先,合乎义的勇才是值得提倡的,不合乎义的勇,非乱即盗。
(二)义信之辨。如我们所知,孔子十分推崇“信”的价值,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言忠信,行笃敬”的话,但他对于片面追求“信”的行为也有保留。我们一般都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君子风度,但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却说: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1.3 妊娠结局判断 产妇妊娠结局:观察产妇的早产、胎膜早破、绒毛膜羊膜炎、产褥感染的发生情况。围生儿结局:观察围生儿的胎儿窘迫、新生儿感染、新生儿黄疸与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情况。
二曰“宜”。《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释名》也说:“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这个解释属于转注式的同音互训,与“仁者,人也”,道理相同。《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里的“义”就可解释为“宜”。
(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这个“孔子负盟”的故事说明,“信”如不合乎“义”,便是小人之信;而要挟之下订立的盟约,是为“要盟”——神且“不听”,何况人乎?此故事亦见于《孔子家语·困誓》,略有异文,孔子所说作:“要我以盟,非义也。”也就是说,“要盟”本不合“义”,若求“必信必果”,不是“硁硁然”之小人又是什么?孔子不听“要盟”,恰恰是合乎“义”的。
孔子目光如炬,对此类不合“义”的“小信”,一概斥之为“谅”。《论语》中两次提到“谅”。一次是在孔子回答子贡“桓公杀公子纠”,而管仲“不能死,又相之”的困惑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匹夫匹妇之为谅”,其实就是“小人之小信”。还有一次,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君子坚贞中正,但不固守于小信。
究竟什么是“谅”?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谅,则不择是非而必于信。”焦循说:“谅者,信而不通之谓。君子所以不谅者,非恶乎信,恶乎执也。”可见,信作为一种价值,必须合乎义。“言必信,行必果”之所以是“硁硁然小人哉”,就因为其最容易陷入“不择是非”“信而不通”的“执”与“谅”中不能自拔!这说明,在儒家看来,人世间一切正向的价值,都不是绝对的,都有一个合理的适用范围,都不应该成为束缚人的枷锁和牢笼!
实验三: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的采样周期Ts=3 μs,采样间隔τ=0.7 μs,干信比取40 dB,所得目标信息如表4所示,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三)义礼之辨。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礼”的地位和重要性自不待言,故孔子谈为政,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修身,则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主张“克己复礼”,要求“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又尝言“六言六蔽”,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又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可见,仁、智、信、直、勇、恭、慎等价值虽属美德,然一旦为人所“好”,皆难免存在偏失,唯“好学”方可救其蔽。值得注意的是,“好礼”“好义”则不在其列。不仅如此,孔子还赞美“富而好礼”者,又以“质直而好义”为“达者”(《论语·颜渊》)。何以如此呢?盖“好学”本身即含“好礼”“好义”之意,故“忠信如丘”易,“好古敏求”难,唯有通过“好学”,方能知礼达义。要言之,礼和义实乃节度与调适所有美德的砝码与权衡。而相比之下,“义”比“礼”更具灵活性,甚至“礼”亦必须合乎“义”。②如《论语·子罕》篇载:
超声刀主机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使刀头产生高达55.5 kHz频率的机械振动,刀头接触组织后带动其高频振动,使内部水分汽化、蛋白氢键断裂、细胞崩解,导致组织被切开或凝固,同时蛋白变性形成黏性凝结物并封闭血管,从而达到切割、凝闭组织和止血的作用。
目前的政府会计制度是以预算会计为基础的。在公共财政方面,事业单位无意识地将财务细化管理作为主要目标。其他类型的财务管理问题都需要进行预算管理,原则上尚未得到解决和实施。
这说明,对于“礼”的追求如果过头,或“奢”或“泰”,都不为孔子所认可。孔子的“违礼”而“从众”也好,“违众”而“从礼”也好,都不是没有原则的首鼠两端,而是是非分明,都遵循了“义”的原则。
(四)“义之与比”。既然勇、信、礼这样的正面价值都有可能在实践上出现偏差,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做才算是“君子”呢?孔子在《论语·里仁》篇里给出了答案: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这话乍一听似乎既无原则,更无立场,实则不然。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绝不仅是道德君子,还必须是智慧君子。这里的“义之与比”的“比”,即靠近义,与《学而篇》有子所言“信近于义”“恭近于礼”的“近”,实即一义。正如“忠恕”之间,孔子以“恕”为主,“礼义”之间,孔子则主张“义之与比”。“义之与比”是强调做任何事,都不能死守教条,不知变通,而是要“义以为上”,因时、因地、因人以制宜。只有这样,人的行为才是合乎“义”的,也是最具智慧的。
《论语·子罕》的下面一章尤为值得注意:
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最初是指地位阶层的差别,如郑玄就说:“贾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说:“如郑氏说,则《论语》此章,盖为卿大夫之专利者而发,君子、小人以位言。”据此可知,孔子的本义并非赞美君子好义,批评小人好利,而是在做一个“应然性”的判断,即在上位的君子因不缺财利,故应当晓于仁义以化民;在下位的小人因为财利易被剥夺,故应当通晓获利之道。后来荀子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显然是从孔子的义利之辨而来。这说明,原始儒家的“义利观”其实是颇具“现代性”的。
此章可谓“夫子四毋”。说孔子杜绝了常人都会犯的四种毛病,能够做到——不主观臆想,不武断绝对,不固执己见,不自我中心。这里的“意必固我”,相当于佛家所谓“我执”或“着相”。一个心胸狭隘、缺乏智慧、不知变通的人,难免会陷入这样那样的“我执”,囿于各种“名相”或“成见”,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君子。可以说,君子一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要能够随时随地破除“我执”,摆落成见,执两用中,从善如流。如何破除“我执”?关键在于“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其实,孔子所反对的绝不是“信”和“果”,而是那个“必”字。任何事,一旦陷入“必”的状态中不能自拔,就一定会远离“义”的智慧。也就是说,“义”作为一种“应然性”价值,在与“时中”和“权宜”等“或然性”价值保持内在联系的同时,也与“必然性”价值划清了界限。换言之,“义”正是对治“必”的一剂良药。而“义”的本质便是“不必”。“不必”,也即“不执”。孔子的高足有若也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认为“信”只有接近于“义”的状态,诺言才可能兑现。
孟子深得孔子“义智”之真传,进一步提出了“惟义所在”的观点: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很显然,这是从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之说演化而来。这里的“大人”即“君子仁人”,正与孔子所说的“小人”相对。孟子以“不必”来解释“义”,等于补充说明了孔子的言外之意。既然“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行径,那么大人君子该怎么做呢?难道要“言无信,行无果”吗?当然不是。一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完美回答了上述困惑和质疑。“不必”不是“无”,而是“不一定”“不必须”,正是对“必”的节制和超越。因为天下之事,一旦“必”了,就有可能陷入“不义”。而要想“义之与比”,就必须摆脱“必”的限制和束缚,让良知和道义真正获得选择和判断的自由。
(五)义利之辨。“义”的内涵中还包括如何处理与“利”的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义利之辨”。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义利之辨。如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其实已隐含着“义利之辨”,也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孔子并不排斥财利和富贵,不过财富显然也并非其真正“所好”。孔子“所好”者何?不过“义”字而已。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两次强调“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就是担心人一旦陷入对财富和物欲的追求,就有可能“绝仁弃义”。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切都以利为先,唯利是图,不仅心态失衡,怨天尤人,而且,也会招致他人更多的指责和埋怨。所以,在孔子那里,义利之辨也成了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
河南省小微企业在不断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下蓬勃发展,但是对于政策的研究可以发现,河南省在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和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因为孔子并不将义与利截然对立,故到了墨子,也就将义利等量齐观了。他说:“仁,体爱也。义,利也。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墨子·经上》)又说:“仁,爱也;义,利也。爱利, 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所利亦不相为外内。”(《墨子·经下》)所以应“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不过,正如熊十力先生批评墨子时所说的:“兼爱兼利,未尝不本于孔子之道。然言仁不酌以义,则仁道不可通也。……墨子非儒,殊不知其所非者,乃当时政俗之弊,正由儒者之道未行耳。”③墨子的这种“以利为义”的义利观显然不无流弊,儒家不得不起而矫正之,孟子就发现“以利为义”,会导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的后果,遂提出“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先义后利”的思想,其实也即《礼记·大学》所谓的“以义为利”。
如上所述,因为“义”的内涵十分丰富和灵活,也就使包括孝悌、忠恕、仁爱等伦理价值的儒学更具弹性和智慧。原始儒学固然重视伦理价值和道德境界,但也十分警惕道德的绝对化、极端化和教条化。换言之,真正的儒家,绝不赞同所谓“道德中心主义”。在世俗的政治生活和道德领域中,诸如仁、礼、孝、忠、信、智、勇等正面价值极容易被过分强调和推崇,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这就难免会造成理论和实践的偏颇和执迷。比如,对于孝道的过分强调,便极易堕入“愚孝”;对于仁爱的过分宣扬,常会导致“愚仁”;对于礼的教条化推崇,又可能导致“礼教杀人”;反过来,对于“利”的极端排拒,又会导致道德的虚伪和悬空。对此,儒学都有及时而又有力的矫正措施。这其中,“义”充当了“价值调节”或曰“道德减压”的安全阀和减速带,故而才有“仁义”“礼义”“孝义”“忠义”“信义”“勇义”等说法。也就是说,不管是多么高尚的道德,都必须合乎“义”。
综上所述,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孕产妇采取阴道分娩成功率较高,待阴道分娩禁忌症排除后可选取阴道试产,以便提高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孕产妇生育质量。
一言以蔽之——“仁”是儒家的大慈悲,“义”是儒家的大智慧。
“义”是人的内在合理性
如果说,孔子对于“义”的阐发,更多指向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智慧,那么,孟子则赋予“义”一种更为刚性的价值内涵,成为君子安身立命的一种道德原则和行动纲领。在孔子那里,“义”与“仁”常常分开说,而在孟子这里,“仁”与“义”则如影随形,不可分割,成为“人性”中最为本原和内在的良知良能,也即所谓“天爵”:
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
拼音中有四个翘舌音的字母,即zh、ch以及sh和r,在这四个拼音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其声母读音,这是历年来教学的难点。为此,可以设计一个学生比较熟悉的生活场景,比如招待客人,四位客人到家中做客,他们都戴着帽子,上面分别写着zh、ch、sh、r四个拼音。客人到家时应当打招呼,客人代号比较难读,需要将自己的舌头翘起来,大家一起读zh、ch、sh、r。学生经过慢慢练习逐渐会读,请客人进门时再巩固四个拼音的认读,这有利于正确地拼读翘舌音。
很显然,孟子是把“仁义忠信”当作上天赋予人类的“本质之性”的。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的“人性论”思想,有效地补充了孔子很少涉及的“性与天道”等本体论和形上学问题,尤其是孟子将“仁”和“义”都作为人性内在德性的原点,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比如,告子就认为“义”是外在于人的道德生命的,提出了“仁内义外”说: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孟子·告子上》)
这一段辩论十分精彩!告子以长、白立论,是站在客体角度看问题,孟子则以“长之”“白之”为说,则是从主体角度看问题。也就是说,敬长的行为看似是因为老者之年长,但敬长之心却是我们本心自具的。孟子“心学”的力量在此显露无遗。在讲“仁爱之道”时,我们提出了“仁”是人的本质规定性,那么同样可以说,“义”是人的内在合理性。“仁”是“情”之源,“义”是“理”之根,只有情理兼备,仁义具足,自然意义的人,方可成为社会、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人。儒学之所以是人学,正在于其义理上能圆融,逻辑上能自洽,实践上行得通。
孟子在论及“浩然之气”时,将其与“义”绾合,提出了“集义”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朱熹《集注》说:“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孟子的“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是说人的浩然之气是长期“集义”“事事皆合于义”的结果,不是“临时抱佛脚”式的一时的正义行为就可以养成的。此即所谓“从量变到质变”,没有“量变”,何来“质变”?王阳明的学生陆澄曾问道:“有人夜怕鬼者,奈何?”阳明回答说:“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何怕之有!”④(《传习录》卷上)可见,“集义”乃是儒家修养的一种“工夫论”,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补充试验:抗体确证试验无HIV特异性条带产生,报告HIV-1/2抗体阴性;出现条带但不满足诊断条件的报告不确定,可进行核酸检测或2-4周后随访,根据核酸检测或随访结果进行判断。补充试验HIV-1/2抗体阳性者,出具HIV-1/2抗体阳性确证报告。
在论及“仁”的价值时,孔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里的“志士仁人”,也可理解为“义士仁人”,因为能够“杀身成仁”,一定是长期“集义”的结果。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志”说: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将此章和上引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曰“义以为上”合起来看,则可发现,孟子的“尚志”,其实是对孔子“义以为上”的再次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志士仁人”一定是能行“仁义之道”也即“居仁由义”的有志之士、大人君子!
孟子的“舍生取义”,与孔子的“杀身成仁”遥相呼应,有效地将“义”的地位提升到了和“仁”并行不悖的重要地位,使其具备了“人的内在合理性”也即天赋“良知良能”的本质内涵。
此外,以往的定义对于存在束支阻滞或起搏等情况所致的ST-T改变,建议对比以往的心电图以判断是否存在缺血,而未提出具体的评价标准。新定义提出:左束支阻滞或右室起搏患者存在ST段与QRS主波方向一致性抬高≥1 mm时,提示存在急性心肌缺血,对于非起搏器依赖的起搏器患者也可以暂时停止起搏以观察心电图改变,但应注意鉴别是否存在电重塑(心脏记忆现象:在一段时间的激动顺序改变后恢复窦性节律时,所出现的持续性T波改变)引起的ST-T改变。新定义还首次提出了存在缺血症状患者新发的非频率相关右束支阻滞与预后不良有关,而溶栓后TIMI血流0~2级的部分心肌梗死患者也可能出现新发RBBB。
孟子的“人禽之辨”,固然以“仁者人也”为原点,但“义者宜也”,同样起到了奠基作用。正是经由孟子,“仁义之道”的结构性基础和本源性价值才真正得以开显和完善。
经权之道,唯义所在
如上所述,“义”是人的内在合理性,但这种内在合理性,仅是就人类的共性而言,具体到每一个个体或者曰“我”的外在行为,“义”也有可能被教条化(所谓“天经地义”),以至走向它的反面。这就必须有一更具智慧性和自由度的“杠杆”予以调节和变通。于是“义道”之外,还须辅以“权智”。这就涉及儒家的“经权之道”了。
“权”的重要性,早为孔子所发现。《论语·子罕篇》载: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孔子将为学的境界分成四个阶段,即“共学”“适道”“与立”“与权”。四者之中,“与权”最为难至。权,本义为秤锤,“权然后知轻重”;这里引申为“权变”。孔子虽然没有提到“经”,但事实上已将隐含着“经权之辨”。“与立”其实就相当于“经”。经者,常也;权者,变也。
(1)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违法招投标不但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而且造成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失控,国有资产流失,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真正揭橥经权之道的是孟子。他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孟子·梁惠王上》)在辟杨、墨时,孟子先肯定子莫的“执中”,紧接着却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这里的“执中无权”,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可与立,不可与权”。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了“反经”的说法:“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反经”的“反”,应该理解为“反者道之动”的“反”;“反经”,不是死守经典,而是通达权变。在《孟子·离娄上》中,关于“嫂溺”的一段辩论尤为精彩: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这个故事涉及“礼权关系”,其实就是“经权之辨”。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经”,则“嫂溺援之以手”,便是“权”;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经”,则舜的“不告而娶”便是“权”。孟子所谓的“权”,即权变、权宜、变通,其实就是孔子所谓“义之与比”,“无适也,无莫也”,以及“无可无不可”。“权”与“经”相反而相成,故权者,必反乎经者也。反经合道方为“权”。程子甚至认为:“权即是经也。”可见,守经达权乃是为学的最高境界。
综上言之,儒家的“仁义之道”其实是本末一体、并行不悖的。如果说“仁爱之道”是“本体”,那么“义权之道”就是“工夫”,二者缺一不可。就经权关系而言,“仁”即是“经”,“义”则为“权”。“仁”的扩充光大,直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义”的反经达权,又可使“万物周流而无碍”。一切正向价值,皆须合乎“义”;一切常道法则,亦当达乎“权”。质言之,权者,义也;义者,权也。呜呼!义权之道,于是乎颠扑不破矣。
①焦循:《孟子正义》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34页。
②刘强:《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04—105页。
③熊十力:《原儒》,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9页。
④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作 者: 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竹林七贤》《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穿越古典》等著作十余种。
编 辑: 得一 312176326@qq.com
标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