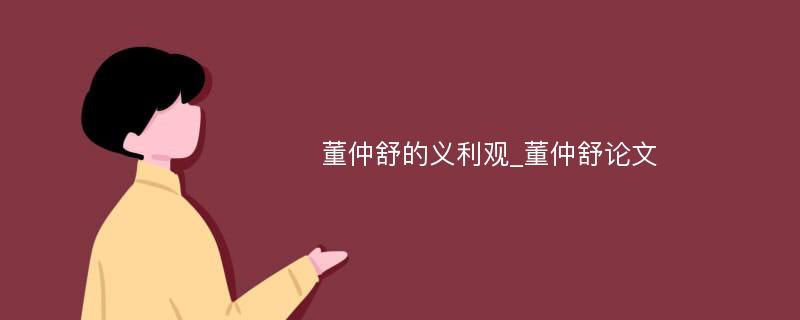
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义利论文,两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义利之辨是历代儒家都热衷的话题。一般而言,每位儒学家都只有一种义利观,但董仲舒的思想却有两种义利观并存。一是义利两有,义重于利;一是义利对立,言义不言利。但从古到今的学者,多仅承认其中的一种义利观,而否认另一种义利观。其实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都是存在的,并有其哲学、人性论的依据,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是相一致的。
一
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分别见于两段话中,一段出自《汉书·董仲舒传》: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谊即义,是说仁人应当明正道义,而不谋计功利。这里正与明相对应,强调对道义的肯定;而不谋与不计相对应,都是对功利的否定。这是一种将道义与功利根本对立,主张只要道义,不讲功利的义利观。
另一段话见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这一段话较上一段话,文句顺序稍异,文字也仅有小异。初看起来,好象含义并无大异。但其中把不计其功,改为不急其功,计与急的一字之异,就使所言之义有了重大的区别。因为,不计是根本不用计较、考虑的意思,而不急则是不以为先、不以为重之义。当不急与不谋相对时,就同不计与不谋相应有了差异。在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上,不计与不谋相对应时,是从根本上否定功利,只讲道义的义利观。不急与不谋相对时,只是将二者视为一种轻重、先后、急缓的关系,而不是根本否认功利;这是一种对义利都有所肯定,但以义重于利的义利观。
这两段话所出的前后文,文字基本一致,又都是董仲舒回答越(一作粤)有三仁的问话的。但是,问话者在《春秋繁露》中作胶西王,而在《汉书》中作江都王。到底问话者是谁,有两种看法。历史上整理《春秋繁露》的宋江右计台本、无锡华氏兰雪堂活字本、周沩阳刊本、王道焜刊本都认为,《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问话者应是江都王。而当今有的学者认为,董仲舒因说灾异下狱后,决不言阴阳灾异,而此段话无阴阳灾异之说,故问话者应当是胶西王。考《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曾先后作过江都王、胶西王之相,一在他对策之后,一在公孙弘用事之后。江都王与胶西王都是汉武帝的兄长,史称一位素骄好勇,一位尤好纵恣,但他们对董仲舒这位名儒,都能给予一定的敬重。出于骄纵的品性,他们都可能自比齐桓公,而向董仲舒提出所谓越有三仁的问题。因而,仅凭《汉书》记载是江都王,就认定《春秋繁露》所记的胶西王是错误的,实难以为据。董仲舒下狱前后,确有言阴阳灾异与不言的差异,但越有三仁是关于古人的具体评价,很难以阴阳灾异来附会,故不能因为这里不讲阴阳灾异,就认定《春秋繁露》的记载是对的,而《汉书》的说法有误。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很难确定问话者是谁,对此最好存而不论。
同样,对这两段话亦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当今有的学者的看法,认为《汉书》所载的文字经过班固的修改;另一种是历史上多数人看法,认为是《春秋繁露》的记载有误。并由此形成了对董仲舒的义利观的不同认识。一种看法以程朱为代表,认为董仲舒的义利观是只要道义,不讲功利,甚至连考虑功利之心都不可有。另一种看法以当今有的学者为代表,认为董仲舒的义利观是义利两有,义重于利。这两种对立的看法,都不承认他有两种义利观。清人苏舆持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正其道不谋其利是体,而修其理不急其功是用,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董仲舒有两种不同的义利观,但他却用体用的关系,把义利两有,义重于利的义利观消融于义利对立、义利不两存的的义利观之中了。
《春秋繁露》出自董仲舒之手,《汉书》成于班固,在没有其他确证的情况下,对这两种说法都不可轻易否定。其实,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两种义利观都是存在的,它们与董仲舒的整个思想体系是相一致的,并有其哲学、人性论的根据。
二
董仲舒的哲学以天为最高概念。他的天有两个层次,一是阴阳五行的自然之天,一是有意志、有道德之天。他的两种义利观,实以两个层次的天为最后依据。而在他的两个层次的天之中,有意志、有道德之天高于阴阳五行的自然之天。事物的发展是由低到高,所以,先分析他与阴阳五行的自然之天相联系的义利观,这就是义利两有,义重于利。在董仲舒的天观念中,自然之天包括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人在内的自然物,即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地阴阳二气,《春秋繁露·威德所生》说:“天,阳气也;地,阴气也。”而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由天地阴阳所生化出来的,《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分为五行。”再由五行产生出万物。但阴阳二气都不能单独产生万物,必须合偶为用,因此,阴阳二气对万物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春秋繁露·阴阳义》所说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同时,阴阳二气不是平等的发生作用,而是以阳为主,以阴为从,故《春秋繁露·基义》说:“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
但是,董仲舒并没有科学的自然之天的观念,说他有自然之天的观念,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他在讲自然之天的同时,又赋予了它人的道德诸属性,如以阳为德、为善、为义、为喜等,以阴为刑、为恶、为利、为怒等。并将阳主阴从说成是一种尊卑关系,依此关系,一切属阳的义项全为尊,一切属阴的义项全为卑。董仲舒的哲学讲人由天生,人副天数,天人合一。当他从自然的阴阳之天出发来论人时,天所生之人在人性上就有了贪仁两种属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董仲舒又以阴阳论说性情,认为人性有性与情两个方面,其中性为阳气所生,情为阴气所出;人性的贪仁分别与性情相应,它们都本于天的阴阳二气,如同天的阴阳缺一不可,贪仁、性情对人性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同天的阴阳有尊卑一样,人性的两个方面也不是平行的,总是以性、仁为主,而以情、贪为从。与天的阴阳两有,人性的性情两有相联系,决定着人天生就是义利两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而“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具体说来,义本于天的阳气,是人性中的性与仁的体现;利本于天的阴气,是人性中的情与贪的体现。它们一养其心,一养其体,缺一不可。但心贵于体,因此,义重于利。在义利观上,就应该是义利两有,但义重于利。可见,董仲舒的这种义利观是直接导源于天有阴阳,并与人性的性情、贪仁两有之说是相一致的。
董仲舒在许多地方都讲到义利两有,不可偏废的观念。他甚至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将义利两有提高到与万物之本相联系的高度: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
这里与天地并称为三本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指教民成就善性的圣王;万物也非指自然万物,而是指被圣王教化的民众,因为孝悌礼乐对自然物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对人才起作用,而孝悌礼乐可归结为道德的义,衣食则是物质的利,实际强调的是义利两有,不可或缺。
儒家言利总是与人的情、欲相联系,董仲舒讲义利两有,还从肯定情、欲的角度加以论说。《春秋繁露·天道施》说:
故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音,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
食色之情只有在不合礼的情况下,才会引起争乱;但在礼的节制下,就是正当的、合理的。礼对食色之情的节制,并不是要夺去人之情,而是要安其情。情是如此,欲也是这样。《春秋繁露·保位权》说:“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欲只要在礼的节制下,同样是合理的;而且,连圣人也不可能使人无欲。这种在礼的节制下,承认情与欲的合理性、必不可少性,也就是对利的合理性、必不可少性的认可。因此,董仲舒的义利两有对利的肯定,是以礼的节制为前提的,这是董仲舒义利两有的义利观的重要特点。
正是由此义利观所决定,董仲舒并不一般的反对言利。因而,他主张给予人民一定的物质利益保障,提出限民名田、薄赋敛、省徭役、什一之税等主张。《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对上说:“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供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悦从上。”在他看来,只有给予人民一定的生活资料,得到基本的物质利益保证,社会才能得到治理。这是他肯定义利两有的落足点。但是,他的义利两有始终是将义置于利之上,是以重义轻利的原则来承认利的合理性的。故《春秋繁露·王道》说:“君子笃于礼,薄于利。”而当人们将利置于义之上,甚至与民争利时,董仲舒则给予坚决的反对与痛斥。他在《天人三策》中就十分严厉地批评那些与民争利的高官豪强,认为他们是造成“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的社会根源。为了防止好利、争利对义的危害,董仲舒提出建立度制,使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得到各自与之相应之利,以化解由好利、争利引起的社会动乱。这种利必须合于度制的观念,是董仲舒义利两有、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一个重要的规定。他的这种义利观虽然肯定义利两有,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利,但始终是将义放在第一位,而将利放在第二位的。
三
董仲舒的义利对立,言义不言利的义利观,则是以其哲学上的有意志,有道德之天为依据的。他在讲自然之天的同时,又把天视为百神之大君,具有对人赏善罚恶的意志,以及主宰人类社会的无上权威。而且,直以天为道德的体现。《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正如他言自然之天,要给天加上道德的属性,他讲有意志、道德之天,也总是要依借自然现象为说。如以自然界的春夏秋冬,为天的喜怒哀乐之志;并将自然界的一些异常之物,称之为瑞应,讲成是天对帝王良好政治的褒奖;又把自然界的干旱、水灾等灾害,称之为灾变,说成是天对人君政治黑暗的谴告,如此等等。
自然之天与有意志、有道德之天,在董仲舒的哲学中都具有将自然现象与人的道德、意志混杂在一起的特点。但是,在各个具体场合,二者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一般而言,他以自然现象出发来论天时,虽然给天加上了并不存在的意志、道德的属性,但意志、道德的属性是用来说明自然之天的,这时的天就是自然之天;而当他从道德、意志的角度来讲天时,虽然也借自然现象为说,但自然现象只是用来论证天的道德、意志的,这时的天就是意志、道德之天。在自然之天之中,道德、意志是被错误的附加到自然物上的;而在道德、意志之天之中,自然现象则是用来论证天的道德、意志的依据。因此,董仲舒两个层次的天,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天。但正是他有两个层次的天观念,才最终导致了他的两种义利观。
由道德、意志之天出发,人从天那里只能获得仁义等道德的属性。《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人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也说:“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所具有的一切道德属性,都是天理在人性的反映。这种天有仁义,人有德行的天人合一,是他天人合一的最重要的规定。在董仲舒的人性论中,只有从道德之天那里获得的仁义,才决定着人的本质。
关于这一点,董仲舒曾反复加以论说。《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故超然有以狄,物 疾莫能仁义,唯人能为仁义。
《天人三策》对此讲得更为明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灿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贵指人特出于万物的独特品质,是人与万物相区别的本质特点,这是说人的本质在于仁义的道德属性。而人的本质与人性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观念,人性是指人的属性的全部,人的本质只是人性中决定人之为人的部分。尽管人从自然之天那里获得性情、贪仁两种性格,性情、贪仁都是人性的内容,但它们并不能都决定人的本质;决定人的本质的只能是由道德、意志之天赋予人的仁义道德。因而,他的自然之天在人性论上,只讲到人的属性是什么,而只有他的道德之天才深入到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既然只是有意志的道德之天赋予人的仁义诸道德属性,那么人从自然之天那里获得的性情、仁贪,只有仁、性才是人的本质,才是善;而贪、情则是与人的本质根本对立的恶,因而,有意志的道德之天在人性上对于情、贪之欲是坚决禁绝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是以阴之行也,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魂常厌于日光,乍全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缀其情以应天?”
循此而言,董仲舒在义利关系上就持一种义利对立,只承认义,而否认利的义利观。《春秋繁露·竹林》说“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人应当“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在他看来,义利之分就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就只能讲义,而不能为利、为生;否则,就会成为禽兽。《春秋繁露·玉英》说:“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义,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认为人从本质上讲是善义的,人不能为义,都是利的危害所造成的。他甚至将利与妄相提并论,视为盗乱之本。《春秋繁露·天道施》说:“利者,盗之本也;妄者,乱之始也。”在此意义上,义利的关系就不是一种可以共存的关系,而只是一种不相容的对立关系。因而,人们在义利观上就应该义利不两存,只讲义,不言利。
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他的义利两有的义利观,是与天有阴阳、人有性情相联系的,而无论是对天的阴阳、人的性情的认可,还是对义利两有的承认,都只是一种事实判定。但他从有意志的道德之天来讲人的本质只能是仁义的道德,论说义利对立的义利观时,则上升到了价值判定的高度。因此,我们可以将前一种义利观称之为事实层面的义利观,而将后一种义利观称之为价值层面的义利观。价值判定高于事实判定,故在董氏的两种义利观中,义利对立的观念要高于义利两有的观念。这也与他的哲学以有意志的道德之天高于自然之天,他的人性论以人的本质重于人的其他属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对于不合礼义之利的否定与反对,较之对利的肯定有更多的论述,而且,语言更为激烈,这已有诸多论著早已指出,本文勿需重复。
应该指出的是,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所言之利其实是不同的。义利两有的义利观所言之利是受礼的节制之利,而义利对立的义利观所言之利则是不受礼义节制、而与礼义根本对立的。正是对利的两种不同规定性,才决定了董仲舒两种义利观对利的不同态度。因而,准确的讲董仲舒的义利两有之利,并不是一般地认可利,而只是承认有礼节制之利,对于违反礼义之利他是坚决反对的;他的义利对立之利,也不是要根本否认利,而是否定与礼义根本对立之利。因此,他的两种义利观虽然一在强调义利两有,一在强调义利对立,但二者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有相通之处。他的义利两有重在义利的统一性、并存性,而义利对立则重在义利的对立性、排斥性。
义利本来就存在既相容、又相排斥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一直是儒家义利观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在董仲舒之前,孔子、孟子比较强调义利对立的一面,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则比较重视义利两有的一面,《荀子·大略》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在义利观上已经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看法。
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综合地吸收了孔子、孟子与荀子的义利观。同时,他又从哲学与人性论的角度,对两种义利观提出了哲学与人性论的理论根据;他对义利两有、义利对立之利作出区分,使利的观念在儒家义利观的发展史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因此,他的义利观是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综合性的重大发展。这同他在人性论上对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作出了理论总结是相一致的。
儒家以伦理为第一要义,因而,将义置于利之上,一直是儒家义利观的基调。董仲舒也不例外,即使他讲义利两有,也是以义重于利为前提的;而他的两种义利观,又以义利对立为重。循此发展,以义根本否定利,乃是其必然的结论。在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中,实已表现出了这一倾向。后来宋明理学家喜谈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不言其“不急其功”,大谈存天理,灭人欲,决非偶然。但是,董仲舒所否定的利是背离礼义之利,他对合于度制之利还是给以肯定的。
标签:董仲舒论文; 春秋繁露论文; 儒家论文; 义利观论文; 义利之辨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人性观论文; 汉书论文; 人性论文; 国学论文; 道德论文; 于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