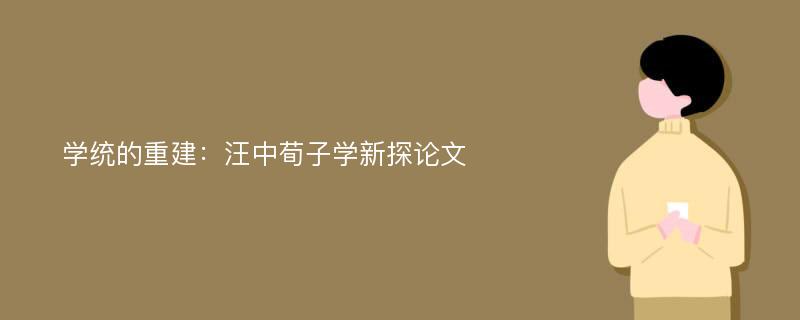
学统的重建:汪中荀子学新探
邓国宏
(贵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乾嘉前后,在《荀子》一书获得充分校释、整理的同时,学者对于荀子之生平事迹及学术源流亦开始进行了考辨,这突出地表现在汪中(1744-1794)身上。汪中的荀学考辨工作不仅开创了荀子研究的新的问题领域和考证形态,背后更体现了乾嘉学者在儒学、经学的传统内为荀子争取正统地位并以此为其汉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在原始儒学、早期经学中寻找道统、学统之依据的努力。
关键词: 汪中;荀子学;学统重建;乾嘉汉学
一、汪中的荀学考校工作及其内容
彭公璞在其博士论文《汪容甫学术思想研究》中注意到,在卢文弨校《荀子》完成的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年),汪中亦在进行《荀子》的考校工作。[1]133他指出,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四十一年丙申”条记载汪中校读《荀子》过程甚详,云:“《荀子校本》卷一后题:‘丙申二月校’;卷三后题:‘四月二十七日,归自江宁校’;《非十二子》篇后题;‘是日雨’;卷五后题;‘五月四日校《王制篇》完,前两日老母受寒,汗之乃解,又理脾胃数剂’;卷十五后题云:‘是日母氏病风湿,某未得亲书案,比小愈,始校此篇。’”[2]附录17汪中《荀子》考校工作的完成时间,年谱此条未载,但据“六月二十二日汪中敬问端临大兄阁下”① 此信内容与年谱“四十一年丙申”条记载相合,知其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信函,其言:“荀子,今藉得宋本校过,所补正甚多,而刘向一序,则张天如《百三名家》亦未收入,此尤可宝也”,[2]430则知其《荀子校本》的工作六月已经完成。而在同年卢文弨《书荀子书后》言自己以前已将荀子校一过,是年得“影钞大字宋本”,极赞其善,喜不自胜,亟取以校其前本,正其错误盖十有八九,[3]141-142其中提及汪中之《荀子》校语一条。综上记载,可知卢文弨和汪中的《荀子》的考校工作均在是年初步完成,并且二人在校书过程之中有过交流。卢校《荀子》最终成果在十年之后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荀子笺释》由谢墉刊行,大为风行。而汪中《荀子》校释成果未曾刊行,且今已佚失。不过,汪中列名《荀子笺释》所参订七家之一,后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杂志》亦对汪中的校订成果做了充分吸收。又“幸哉有子”汪喜孙从《荀子杂志》中将其父《荀子》校释成果摘出,编入《汪氏学行记》中,后人因此始得集中览其周详。
经过这三个步骤,孩子们当时似乎都理解了“茫茫”的意思。可是我教完了《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这篇课文,教下一篇课文《水上飞机》时却傻了眼。
当然汪中对于荀子研究的贡献,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对荀子生平与学术源流的考辨。依严灵峰编著《周秦两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国荀子书目录》《荀卿子通论》(附《荀卿子年表》)成书出版迟至汪中死后20余年的嘉庆二十年(1815年),但其基本成稿的具体时间仍有待考订。温航亮在其博士论文《汪中思想研究》中推测:“很可能在校勘之后,汪中便撰写了《荀卿子通论》以及《荀卿子年表》”。[4]53依前引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丙申“六月二十二日汪中敬问端临大兄阁下”信函,汪中已特地提出“刘向一序,……此尤可宝”。刘向《孙卿书录》的内容除《荀卿新书》十二卷32篇篇目外,主要即为荀子生平事迹与学术之记述。[5]1182而汪中《荀卿子通论》及《荀卿子年表》之内容亦不出荀子生平系年与学术源流之考辨,与刘向叙录探讨的问题绝为相类,且时有引述刘向叙录之言。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推测,汪中之作《荀卿子通论》及《荀卿子年表》乃是由于刘向《孙卿书录》的内容而引发,因而其写作之初步酝酿当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完成校对《荀子》书后即有。但是其写作完成则大概不会早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为卢校谢刻本《荀子笺释》之谢墉序、钱大昕跋均有与荀子生平、学术相关论述而未提及汪中之论。据《容甫先生年谱》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甲辰汪中“春仲,从谢侍郎北上”“为谢侍郎撰《展义论》”,又有“皇玄孙诞生颂代谢侍郎作”;[2]附录27乾隆五十年(1785年)乙巳汪中“有事宝应,得石门画像于射阳之双敦。钱少詹事为书楹帖云……”。[2]附录28可见《荀子笺释》刊行之前两年中汪中与谢墉、钱大昕犹有频繁来往,① 《清史稿:列传九十二·谢墉》记载“墉以督学蒙谤,然江南称其得士,尤赏江都汪中,尝字之曰:“予上容甫,爵也;若以学,予於容甫北面矣!”谢墉如此推崇汪中,如其知晓汪中的《荀卿子通论》之作不容不在《荀子笺释》“序”中提及。 汪中若有《荀卿子通论》及《荀卿子年表》之作,谢墉、钱大昕不容不知,知而于序、跋相关论述中不提及汪中亦为不可理解。后之郝懿行于《荀子补注》后附之《与李月汀璋煜比部论杨倞书》即提及汪中《荀卿子通论》之关于杨倞的考证观点。[5]1241综上可知,汪中之《荀卿子通论》及《荀卿子年表》完成当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其生命的最后九年里。
关于《荀卿子通论》之内容,原文兹不赘引。马积高先生对其内容有一概括说明:“《通论》凡三段,其第二段辨《韩诗外传》及《战国策》所记荀子答春申君语出《韩非子》,非荀子语;第三段考证杨倞生平,皆属考据文字。第一段则以‘荀卿之学出于孔氏,尤有功于诸经’两语为纲目,其于第二语论证特详,遍及荀子与诸经传授的关系……,其于第一语则惟考证其师承。”[7]302
各个年级都会出现类似的错误,说明教师对此类错误不够重视,也说明对于学生来说此类错误根深蒂固。如何杜绝此类错误的发生?笔者觉得落实数线上的小数表示的两种意思是根本,除此之外可借助边画弧线数格子的方法来突破。如果采用数分隔线的方法,则强调起点不数。
关于《荀卿子年表》,温航亮概括其内容为:“以赵、齐、秦、楚四国为经,始于赵惠文王、楚顷襄王元年,终于春申君之死,共60年,将史籍中四国的有关记载与《荀子》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相对照,以大致确定荀子一生的经历:齐泯王末年,荀子50岁‘始游学于齐’,到齐襄王时‘最为老师’;齐襄王18年,荀子‘去齐游秦’,第二年,由于‘入秦不遇’,荀子又前往赵国;齐王建初年,荀子‘复自赵来齐’;齐王建十年,由于齐人向齐王进谗言,荀子‘乃适楚’,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八年后,春申君由淮北徙封于吴,但荀子仍然担任兰陵令;又过了12年,楚考烈王卒,李园杀春申君,荀子被废置不用,此后他便住在兰陵,着书而终,并葬在兰陵。”[4]54另外,“关于荀子的卒年,汪中依据《荀子·尧问篇》《盐铁论·毁学篇》和《史记·李斯传》中的有关记载,认为在秦统一天下之后。又根据刘向《叙录》《史记·六国年表》,认为春申君死的时候,荀子己经137岁了。而荀子因为李斯相秦而不食,李斯相秦在春申君死后18年,则荀子至少有155岁。”[4]54
汪中关于荀子生平、学术之考证的具体结论,尽可以争论。在这方面,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本文不打算叙述。② 关于荀子与诸经的关系,可以参见马积高《荀学源流》第八章,张小苹《荀子传经考》;关于荀子生平系年的研究,王天海《荀子校释·附录》之“五、荀子行历年表辑录”提供不少资料,学者亦可由其指引参考各位作者之研究。 但是其思想史意义却须重加分析和肯定,这将是本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如马积高先生所言“《年表》及所附考证于有关荀子生平之史料搜罗已尽,排比勘合,亦颇用心,于后学不为无功”,[7]301-302又如张小萍言“汪氏的考论虽然短小,但他广泛搜罗了各种与荀子相关的传经源流,又结合了《荀子》本文,证据充分、论证充实。……汪氏的考论在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荀卿传授群经的观点也多为名家所承”,[8]5二人均肯定了汪中考证工作之学术上的意义。田富美亦指出,“汪氏跳脱当时普遍就荀书的字句词汇考证型态,提供了另一种考证荀子学术的方式,呈现了清儒考证多元化的趋势特征。”[9]91概而言之,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及《荀卿子年表》开创了荀子研究的新的问题领域、新的考证形态,并为之搜辑了详实的文献材料,成为后来对于此一问题学术考辨的基础。
二、学统重建的努力——汪中荀学考证结论背后之意蕴
其实,与上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汪中通过荀子与诸经传授的关系、荀子与孔子及其弟子之传承关系的考证所要证成之结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对于乾嘉思想界之重新发现与肯定荀子地位与价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谓:“其书(引者注:《荀子》)晻昧了七八百年了。乾隆间汪容甫著《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俱见《述学·内篇》)。于是荀子书复活,渐成为清代显学。”[10]358梁启超先生认为,乾嘉时期《荀子》研究的复兴,汪中著作之带动影响巨大。马积高先生认为梁氏此论表明汪氏之论、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影响”,[7]303因为“在儒家经学备受推崇的清代,仅凭传经这一点,就已足恢复汉人孟、荀并称的传统,益以师授渊源有自,荀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学大师的地位就更难动摇了。”[7]303可以说,汪中的考证并不纯粹是在考索荀子之历史地位和功绩,还给荀子一个历史的公平,而且要在儒学、经学的传统内为荀子挣得一个正统的地位。所以其《荀卿子通论》言曰:“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2]413荀子不仅作为周孔之传的正统地位得以贞定,而且具有了乾嘉经学学术典范的形象。乾嘉学者为其经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在原始儒学、早期经学中寻找道统和学统上的依据,而汪中于此特别抉发出来的人物就是荀子。
其实,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并不完全是从师承及经典授受来论证荀子在儒学中的学统地位,他也有从思想实质方面来肯定荀子思想与正统周孔儒学的联系。田汉云指出:
如果将汪中对贾谊的表彰与对荀子的表彰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汪中肯定了荀子之学出于孔子,又以传经的功绩将孔子的学说传于后世;而贾谊之学又渊源于荀子,后世的经学、辞章之学又源于贾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由周公到孔子,再到荀子,再到贾谊,然后是后世学术的清晰的发展路线,汪中自己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路线称之为“孔荀”儒学授受统系。[4]58
彭公璞亦有相同论述:
据笔者调查,部分职业中学在教学方面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首先是对教材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教师不能很好地把握所授知识的难易度和深广性,无法掌握在具体的教学中做到哪些知识必讲,哪些能力该强化;其次是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是按照教材的具体要求实施,但这些要求又不能与学生的实际结合,导致了语文课堂上出现目标不明确的状况;再次对学生的语文知识及能力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只是在期中、期末由任课老师出一两套题或学校抽题的形式进行测试,无法全面地检测学生的语文水平,也不能全方位检验教师的教学效果。
温、彭二人都认为,汪中之论通过孔子、荀子、汉儒之学术授受联系的肯定,将荀子以及汉代学术纳入儒学学统,是“汉学与孔子的对接”。[4]58而汪中自身所代表的乾嘉学者又自认宗奉汉学,其学术乃是对于汉代学术的继承与发展。这样乾嘉汉学与周孔儒学正统的联系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样的学统说具有与宋明儒者之道统说相抗衡,为乾嘉思想学术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意味。关于此一点,温航亮认为,乾嘉学术仅靠崇扬汉学比宋学更古,并不足以为汉学建立其在儒学内部的合法性;为达致对于汉学合法性的充足论证,乾嘉学术必须为汉学找出与孔子之间的联系,汪中的工作就为这种联系找出了可靠的证据。其论以为:
乾嘉学术作为宋明理学的一种反动,直接站在其对立面,最后必然要求打破理学家建立起来的、并赖以存在的“孔孟”授受的学术统系,并建立新的统系说。如果不为汉学找到与孔子相联系的证据,仅仅依靠汉学是比宋学更为古老的一种学术形态,显然是很难在儒学内部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的。汪中的《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序》等研究著作,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直接以解决这一问题为目标,但由此发现的荀子和孔子、贾谊和荀子之间学术上的内在联系,却为论证汉学与孔子思想的联系找到了可靠的依据。”[4]57
以上温、彭所论均为灼见,但还只是论及汪中从儒学一般传承(师承与经典授受)方面将荀子及汉儒纳入儒学学统的意义,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汪中关于荀子思想学术之传承的考证,持守宋明理学之道统说的学者仍可以在承认其结论的同时而对荀子之道统地位不予承认。师承与经书的授受并不能为论证“汉学与孔子思想的联系”提供充分和可靠的证据。纵然师承及经典之授受关系俱在,但他们仍可否认荀子及汉儒就获得了孔子儒学的真精神。宋明理学之道统论认为程子、朱子得孔孟儒学千年不传之真精神,本来强调的就是道统在于实质性之儒学精神大义的相续,而不在外在形式之师承传袭与经典授受。宋明理学家及现代新儒家学者否认荀子、汉儒之道统地位,都是认为荀子及汉儒思想精神不符合他们所贞定的孔孟大义。他们基本没有涉猎荀子、汉儒与孔子之师承授受关系的问题,但如果向他们提及孔、荀及汉儒之间的这种授受关系,他们大多恐怕也不会否认,因为也用不着反对。师承与经典授受,虽然也是一种重建学统的证据,但那只是一种外缘的证据,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汪中的考辨重建了儒学学统,“为论证汉学与孔子思想的联系找到了可靠的依据”,[4]57既是一种过度的溢美,又遗漏了汪中更为重要的论述精神。
在汪中的思想中,先秦学术流变的“源”(即“太史之官”)和“流”(即“诸子”),都与“礼”息息相关,所谓学术发展变化,不过是对“礼”的认识的变化过程,“礼”正是由“史”而“诸子”的先秦学术源流的主角。不但如此“古之史官,实秉礼经,以成国典”,“礼”还是一个国家施政的根本依据。[4]65
此论认为,汪中虽仅只考索孔、荀及汉儒之间的授受联系,未曾论及此一学术传承在后世之继承与演变;但其意甚为显明——清代朴学即为孔荀一系学术传统的复兴;所以,汪中的论述就具有了赋予清代朴学以合法性、正当性的意义,且具有与宋明理学道统论相抗衡的思想意图。
汪中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儒家学派孔荀一系的学术流变进程;此一学派由孔子发端,经过子夏、仲弓传至荀子;再由荀子传授至汉初经学诸家,三传至贾谊;之后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等人皆有研习。由是观之,汉代学术无论经今文学、经古文学派皆受其沾溉。正是有了荀子的贡献,汉学与原始儒学才血脉相连,贯通一体。[1]138
彭公璞亦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其论述更为仔细明白,尤其注重揭示汪中之论对于乾嘉汉学寻找自身学统上之正当性的意义。其言道:
学者们多有注意,经过汪中的考证,一条由周、孔经荀子到汉儒的学统表之而出。温航亮认为:
汪中推崇荀子,似有过于孟子。这不仅是考虑到荀子在传承经典方面的特殊作用,同时也着眼于荀子思想的重大价值。他特别点明:“荀卿所学本长于礼。”他又具体指陈了《荀子》为二戴《礼记》所取资,并说曲台之礼乃是荀学之支流余裔。既然《礼记》在后来亦升格为经,《荀子》应在儒家学统中占有何种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汪中这样看问题,与清代朴学家以礼学代替宋儒理学的宗旨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汪中尊崇荀子的深意,在于整合先秦儒学的思想资源,重建儒学的理论体系。[2]前言12
开展科学研究,是高校的三大功能之一,科研是高校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石。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地方高校逐渐成为我国高院校的主体部分,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地方高素质、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近年来,地方高校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的态势,而且高校之间的竞争也成为常态,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核心竞争力,科研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已成为衡量一所地方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科研核心竞争力可为地方高校带来持续长久的优势。如何准确地评价地方高校的科研核心竞争力已成为政府部门和高校关注的焦点。
综上所述,“汪中的考证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儒学学统重建的企图”[9]102已是毫无问题的,仅此一点在乾嘉时期其意义就已不可低估。周积明更为具体地认为乾嘉学者存在一种重建礼学学统的倾向,汪中《荀卿子通论》的写作是其表现之一,[12]56-60其观点得到田富美的呼应。[9]102而温航亮在《荀卿子通论》的片段之外对于汪中思想的整体考察使得我们对于汪中此一溯源荀子重建礼学学统的努力之具体意涵有了更为明晰和深入的理解。其言曰:
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云:“《史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于荀卿则未详焉。”似乎他考定孔荀一系的学术源流仅仅是出于“补史之阙文”的考证趣味,但细读其文,则可发现他实“有大义寓焉”。虽然对于孔荀一系在汉以后的流变,汪中没有再论及,但从其学术倾向以及所处的以“汉学”为号召的清代朴学背景看,汪氏的意见是很明确的:孔荀一系的学术传统在清代再次得到恢复,清代朴学就是这一传统的正统继承者。由于从孔子到荀子的学术系统渊源有自,其授受关系明白可考,故这一系统在儒学内部具有学术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现实意义是赋予了清代朴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汪中考镜孔荀一系的学术源流,实际蕴含着重建学统,与宋明理学道统论相抗衡的思想意图,目的是要打破官方理学的权威主义、独断主义,为朴学话语对抗理学话语寻求理论上的支持。[1]139
其意以为,汪中特别点明荀子学长于礼以及《荀子》与《礼记》密切关系,即是从礼学的侧面肯定荀学与儒学、经学之正统精神一致。另外他也特别注意到,汪中强调荀子之礼学与儒学正统之联系,与清代学者主张“以礼代理”[11]的学术倾向是一致的。
此论具有重大的认识意义,它意味着汪中对于礼学学统的重建并不止于经学、儒学传统之内而言,而是将子、史之学也包括进来了。温航亮认为,在汪中的先秦学术史观中,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的整个秦汉学术传统,都是以礼为核心的。其言汪中:
张新文指出,一年来,全省发展改革系统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在重大规划、重大工程、重点战略、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重大活动和重大任务等方面,推进办成了一批事关发展全局和长远的大事要事,为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省发改委党组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省委巡视为契机,坚定不移地以党建促发展,营造了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塑造了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当他的研究视野扩展到诸子学时,便发现了由“史”而“诸子”的先秦学术发展史,认为儒学和其他诸子一样,都来源于“古之史官”。“古之史官”的最根本理论依据在“礼”,因而后代的学术传统也以“礼”为最根本的源头。“古之史官”又依据“礼”“以成国典”,因而“礼”又是经世思想的根本依据。事实上,汪中表现在一些文章中的“用世”思想,正是从“礼”的思想出发的。此后的扬州学者即在汪中的基础上以“礼”来解说经典,并且打出了“以礼代理”的旗帜,希望以“礼”为经世的工具来实现汉学的现实价值。[4]摘要1
唐以军告诉记者,2018年3月,一名尼泊尔留学生旅游时,在丹江口水库溺水,当地群众及其同伴边报警,边通过急救人员电话指导,对其进行救治。同伴在专业急救人员到现场前,争取到挽救时机,最后患者成功复苏。他表示,急救科普非常重要。
In the intensive reading of English,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use of"infiltratio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ollow these three stages.That is,before intensive reading,duringintensivereading,and after intensivereading.
在汪中的思想中,礼学的学统不仅是儒学的学统,而且是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的整个秦汉学术的学统,因而也理应成为后世一切思想学术的正统。在这思想学术之正统中,荀子与周公、孔子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所以他倡言“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2]413在这样的学统理解之下,“以礼经世”的思想观念成为汪中衡量一切学术的标杆,诸子之中不仅儒家的荀子、贾谊,而且墨子的一些思想由此也得到其积极的评价。所以汪中的子学研究既有其根据王官之学散为百家的学术史认识而来的对于诸子各家思想的广泛包容,又有其“以礼经世”的核心关怀,而不是泛滥无主。也许正是因此,温航亮才认为,“汪中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极力提倡先秦诸子之学,即使有这种提倡的姿态,那也是希望通过对诸子的研究,正确地理解和阐发儒家一直以来所追寻的‘先王之道’”。[4]73在这样的认识下,汪中对于荀子生平及学术的考证、表彰所具有的意涵得以真正准确的定位。如果借用周积明的说法,乾嘉学者存在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那么在汪中那里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汉学学统、经世学统、礼学学统的重建其实是同一个学统的重建,而荀子在这个学统中无论是从那个侧面来看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结 论
总之,经过汪中的论述,荀子不仅作为周、孔之传的儒学正统地位得以贞定,而且具有了乾嘉思想学术之典范的意义。乾嘉学者就这样为其以“通经”“明道”“经世”为核心内容的思想学术理想在原始儒学、早期经学中寻到了道统和学统上的依据。这一新的道统和学统理解,虽然不废孟子,但对于《孟子》进行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新的诠释① 代表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焦循的《孟子正义》。 ;更为重要的是将被宋明理学家们所排除的荀子重新纳入进来,并给予特别的肯定。在这一新的学统和道统理解之中,体现的不仅是汪中,也包括其他许多乾嘉学者对于如何“整合先秦儒学的思想资源,重建儒学的理论体系”[2]前言12的普遍思考。
参考文献:
[1]彭公璞.汪容甫思想学术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哲学院,2010.
[2]汪中.新编汪中集[M].扬州:广陵书社,2005.
[3]卢文弨.抱经堂文集1-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温航亮.汪中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哲学系,2008.
[5]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九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马积高.荀学源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张小苹.荀子传经考[D].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1.
[9]田富美.清代荀子学研究[D].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6.
[10]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1]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周积明.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J].江汉论坛,2002(2).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9)01-0034-05
基金项目: 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贵大人基合字(2014)014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乾嘉时期的荀子学研究”(17JYC720002)
收稿日期: 2018-09-10
作者简介: 邓国宏(1984-),男,湖北黄梅人,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孔学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哲学与先秦儒家哲学(荀子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范文华)
标签:汪中论文; 荀子学论文; 学统重建论文; 乾嘉汉学论文;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