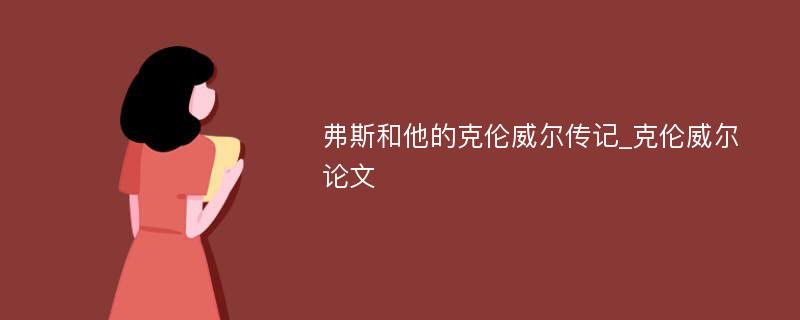
费尔斯和他的《克伦威尔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伦威尔论文,尔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1)01-0065-11
查理·费尔斯的《奥立弗·克伦威尔和清教徒在英国的统治》(以下简称《克伦威尔传》),初版于1900年,1934年出了第2版,后又被牛津大学出版社收入“世界古典丛书”[1]。
自从17世纪以来,有关克伦威尔的著作,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据统计到本世纪40年代时已达3692种。到现在,总数当在4000种左右。洛玛斯夫人在为卡莱尔的《克伦威尔书信言论集》最后一版(T.Carlyle,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1904)所编的书目中,开列了约2800种有关书籍。1929年艾勃特又编订了一个新的书目,增加了700多种新书,不过其中大多在偏僻的地方已出版过,只有150种是初次出版的。到了40年代艾勃特又对这个书目进行补遗,使总数达到3692种。[2](PP959-972)此后几十年,关于克伦威尔的著作,仍有学者专门论述。[3]最近几十年,关于克伦威尔的著作,可参见拙著《研究克伦威尔的史书评述》。[4]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不但内容广泛,而且思想差异很大,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更是褒、贬、臧、否,应有尽有,可说是千差万别。颂扬他的人,说他在行动领域中的地位正像莎士比亚在艺术领域中的地位一样,“是古往今来,英国人中最伟大的人”。[5](P113)责骂他的人,说他是世界上曾有过的最臭名昭彰的暴君之一;他之所以成为国家元首,完全是通过他对自由事业的背叛和他对那些曾与他共同为争取自由而战斗过的卓越的爱国者们的卑鄙的欺骗和无情的背弃。[6](P267)有人在讲到这样两方面极端的评论时曾说:“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样被人说得更好或被人说得更坏了。”[7](P694)也有很多人把克伦威尔说成是好坏参半的人物。休谟说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优秀的人物,甚至是一个卓越的天才”。然而他却是“靠了欺骗和暴行才使他成为国家第一把手的”。[8](P401)拿克拉兰敦典型的话来说:克伦威尔是一个“勇敢的坏人”。因为他“既有那么多的受到咒骂、应入地狱的罪恶,又有些引起若干人长期怀念的美德”。[9](P97)
在如此庞杂的著作中,有一本书却受到近代历史学家的一致推崇。这就是上述费尔斯的《克伦威尔传》。这本书虽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就其内容所涉及的政治、军事、宗教领域及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而言,其取材之丰富、严谨;论述之清晰、扼要,都是他书所不及的。当它在1900年初版以后不久,著名历史学家特里威廉就称赞它是同类著作中的“最高权威”。[10](P527)当代研究17世纪英国史的著名学者希尔和艾尔默等人,也异口同声,一致推崇,说这书“毫无疑问是克伦威尔传记中最好的一本”。[6](PP270-301)[11](P114)
费尔斯于1857年出生于设菲尔德的一个钢铁厂主家庭,1883年到牛津定居,担任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1903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学术研究,集中于17世纪的英国历史。在他学术活动的早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曾担任英国国家档案委员会的委员、英国海军部特拉法加战役委员会委员,出版了许多17世纪英国史的史料和当时人的回忆录、日记,包括著名的《克拉克文件》。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使他熟悉了研究领域中的大量原始资料,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对所运用的资料的鉴别、取舍,都可驾轻就熟。
除了1900年出版的这本《克伦威尔传》之外,费尔斯重要的学术著作还有:《克伦尔的军队》(Cromwell's Army,1902)、《内战时期的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 during the Civil War,1910)、《护国公制的最后年代》(The Last Years of the Protectorate,1909)。最后这部书是他继承和完成他的老师和朋友伽狄纳的多卷本英国史(1603-1656)未竟之作。(注:伽狄纳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即埋头从事17世纪英国史的写作,他仔细搜集考证大英博物馆、国立档案馆以及巴黎、马德里、威尼斯、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等地档案馆的资料。按年、月,直至逐日记述从1603年詹姆士一世即位起的英国史,终于出版了巨著A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1603-1642,10Vols(1883-1884);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1642-1649,3Vols(1886-1889);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re,3Vols(1901)。他本来想把事件写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写到1656年时,已年老体衰并于1902年去世。费尔斯即按老师的遗愿写了The Last Years of the Protectorate 1656-1658(1909),把历史写到克伦威尔去世为止,后费尔斯的学生戴维斯(G.Davies)又继续写了The Restoration of Chaslas Ⅱ,1658-1660(1955)。)此外,费尔斯还在《英国历史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为《英国名人传记词典》撰写了多达275条的人物传记,[12](P76)该词典中有关17世纪英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几乎全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戴维斯又将他的遗稿编辑出版,其中包括《马考莱的英国史评注》(Commentary on Macaulay's History of England,1938)、《历史与文学论集》(Essay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1938)、《克伦威尔军队的团队史》(Regimental History of Cromwell's Army,1940)。
费尔斯还积极从事学术团体的组织工作,他创建了英国历史协会,并两度担任该会会长(1906-1910;1918-1920)。在1913-1917年间又担任了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这本《克伦威尔传》是在伽狄纳和费尔斯本人多年研究17世纪英国史的基础上写成的。书中内容大都以第一手的资料为依据,凡书中所引用的重要史料,都经过了广搜慎选,并加以严格考证。如关于克伦威尔企图移民到美洲新英格兰一事,当时及后世有许多不同说法,费氏经过多方分析,认为有些说法属于揣测不实之词,其中只有一个说法“与已确证的说法相吻合,基本上是可信的,不应轻易地将之当成虚构而弃之不顾”。[1](P37)关于克伦威尔死后埋葬地,也是众说纷纭。著者逐一对之进行分析,然后指出,克伦威尔肯定是葬在伦敦的康纳特广场,“在现在的康纳特广场所在地街道的一、两码深地下,在走过这里的人的脚步下或马蹄下,正埋着伟大护国公的遗体”[1](P444)。在史料缺少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在有关论述中剔抉、分析,务求言之有据。克伦威尔少年时期默默无闻,史料甚少。费尔斯即细心在同时代人的记载中找到少数有关资料,予以记述。书中说:“克伦威尔在大学里学习了多长时候,我们不知道,不过,他在离开时并未取得学位,这是肯定的”。[](P6)当代有些小册子说在1642年10月间的埃吉山战役中,克伦威尔“甚至根本未在战场上出现”。但费尔斯根据当时人的一份日记,经过分析后指出:克伦威尔上尉不但参加了这次战役,而且是属于“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军队,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军官之列。[1](P82)如果资料欠缺,确实无以为据,也不妄加论断,而是根据多种旁证,详加剖析。关于克伦威尔是否交纳“船税”的问题,就是这样。强迫征收“船税”,是查理一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而克伦威尔又是坚定地站在反对国王横征暴敛立场上的,人们很容易推想,克伦威尔必定会坚决拒交“船税”。然而著者并不以此而想当然地遽加论断,而是对许多资料进行研究、推敲,最后得出了克伦威尔可能也交了“船税”的结论。[1](P30)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为了巩固他的个人统治,试图同长老派“妥协”,然而这种秘密的尝试性的勾结,“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著者通过细心钻研各种史料,在克伦威尔给罗伯特·哈蒙德及沃顿勋爵的信中,体察到克伦威尔这种心迹,联系其他有关资料,从而推论出克伦威尔这时的重要政治态度。[1](P246)
虽然费尔斯和伽狄纳在学术研究上有共同之处,但对伽狄纳叙述历史时就事论事,枯燥乏味的风格,费尔斯却不以为然。他更注意在不失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对历史叙述的文字进行适当的修饰和必要的归纳综合,以便不仅陈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表象,而且也挖掘其内涵的实质和特征。他曾对马考莱的著作进行评注,说明他对马考莱那样以生动文笔记述历史的爱好。[13]
费尔斯除了研究历史之外,还喜爱诗歌,对民谣也颇感兴趣。同时在业余时间还从事收藏绘画和雕刻,“对17世纪的绘画和印刷品有无比的知识”。[14](P223)他的著作也显示出一种优雅的风格,遣字造句,洗炼而凝重。书中对有些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历历如绘。当记述长期议会初期的主要领导人皮姆时,用几句生动的描述把皮姆的作风和言谈特点勾画了出来。书中说,当时在政治党派尚未形成之际,皮姆掌握了议会中的斗争策略,利用议员之间的矛盾,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他对国王政府的腐败行为进行揭露时,能够抓住要害,条分缕析,“他有时用庄重崇高的词语,或者把当时的情感凝缩为简短、尖锐的语句,这些话像谚语一样流行了起来”。[1](P47)书中在描绘某些历史事件时,抓住主要特征,浓墨重彩的寥寥几笔,就将事件的氛围烘托得生动逼真。1647年8月初,在伦敦召开的长老派议会,企图挑动暴民反对军队,军队闻讯,即向伦敦进发,计划去讨伐议会里的长老派。对此,书中写道:议会里的长老派议员“每当侦察兵进来报告军队暂停前进的消息或其他报导时,他们就大声喊叫:‘决一死战!’但每当侦察兵带来军队向前推进已逼近他们的消息时,他们就连声叫嚷:‘谈判!谈判!谈判!’”[1](P166)使人阅读后如身临其境,对长老派议员色厉内荏的姿态产生深刻印象。
书中对克伦威尔在几次关键的事件中的言行和思想感情更加以细腻具体的描绘。如关于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解散长期议会的情况时写道:当克伦威尔听说议会将很快通过新的选举法时,立刻赶到议会。“他的穿着和平时一样,不像个将军,也不像个士兵,而是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穿了一件黑色便装和灰色的毛线袜。”他冷静地坐着,然后“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取下帽子向议会发表讲话。起初,有好一会儿,他赞扬议会,称赞它的工作以及它对公共事业的关心,然后话题一转,说到议员们的不义行为,对正义事业的失职,谋取私利及其他错误。他越说越激动,将帽子又戴到头上,在议会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开始对着一个议员,接着对另一个议员,严厉地斥责他们。他没有指名道姓,而是用手势表明他所讲的是谁;这些人腐败,那些人生活堕落;这个人是骗子,那个人是不公正的法官……”[1](P316)当时的情景跃然纸上。
书中在讲到克伦威尔年老体衰的情况时,举了一个例子,1657年克伦威尔的签名和1651年所签名的笔迹已有明显的不同:“原来雄浑有力的笔迹,在6年以后,已显得软弱无力。”[1](P432)还讲到克伦威尔在晚年感到公务沉重,懊悔当年不该放弃悠闲的乡村生活而担任繁重的职务。1657年时他说:“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一个哲学的论题,即一个重要的职位,显赫的权威,实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他后悔当初不该放弃了宁静的乡村生活而选择了坐上最高宝座,从而蒙受烦恼和兴衰不定的痛苦。“我宁可居住在我的森林边去放牧羊群,也不愿掌管像这样的政府。”[1](P432)这些叙述,实耐人寻味。克伦威尔的晚年,既不像秦始皇时代的李斯,在被腰斩于咸阳市前,慨叹不复能与其子牵黄犬逐狡兔,享受游乐;或者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丹东,当1794年春上断头台时,徒然向往于贫穷渔夫得与清风明月为伴的悠闲;也不像彼得大帝时代的权臣孟什科夫,失势后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在寒夜孤灯之下,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唏嘘。他一生的发展轨迹,可说是一帆风顺,1653年,当上护国公了,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应该志得意满,为什么有如此悲怆的心情?别的独裁者的晚年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的矛盾不安?(注: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朱元璋在晚年“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遍找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时刻警惕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性格变得更加残酷横暴”。(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280页)到1965年第4版时,在序言中说上述文字是“严重错误”,“经指出以后”即将之删除。(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页)并将最后一节从“晚年的悲哀”改为“辛勤的一生”。联系到吴晗后来的悲惨遭遇,岂不令人感慨万端!)
书中许多地方引用了当时马维尔、沃勒、弥尔顿等人的诗句和民间流传的民谣,作为当时人对所发生的事件和人物的舆论反映。1647年11月,国王查理一世从看管他的汉普顿宫逃到了怀特岛上的卡里斯小溪堡。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克伦威尔故意让查理一世逃走,以便加之逃亡罪,将之打倒,由他自己掌握政权。在马维尔的著名诗篇中,对此即有反映。诗中说克伦威尔——
带着恐惧和希望,/编织了这样一张网;/似乎是查理自己想要逃到,/卡里斯小溪狭窄的小岛;/从而使这个王室出身的演员,/将会去把悲剧性的断头台加以装点。[1](P180)
1653年春克伦威尔以武力驱散了议会,这本来是从议会民主制向军事专政倒退的行为,但当时不论是贵族和平民大多只是对议会里议员的败德和腐化行为感到不满,而对克伦威尔解散议会的行为却表现出轻佻的欢欣。在当时流行着一首民谣,形容克伦威尔在议会指手划脚的言行和议员的惊慌失措的情形——
勇敢的克伦威尔/走进了议会,像个精灵,/他发怒的面孔,/吓得议员们口呆目瞪;/“走吧!”他说,“你们坐得够久了;/难道你们,还想坐在这里,/直到世界末日来临!”[1](P319)
当英吉利共和国建立以后,有些人认为克伦威尔奉行的外交政策,会把共和制的理想推行到国外去;他在国外的赫赫战功,“将标志着所有被压迫民族历史上的新纪元”。[1](P304)但克伦威尔的军队在爱尔兰的暴行,却使很多共和主义者大失所望。当他建立了护国公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后,有些人趁机献媚邀宠,诗人沃勒等人急忙以阿谀之词,对他歌功颂德。[1](P312)费尔斯在书中引用这些诗歌和民谣,使本来就以洗炼、优美文笔而见长的内容,更生色不少。这书不仅成为一部史学名著,即使从文学角度来看,也属上乘之作。
在有些段落,著者还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在讲到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时指出,在亨利八世时,议会不过是国王用来任意处理宗教及政治事务的驯服工具。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议员们也不过是女王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也发发牢骚,但总的来说,是听话的。但宗教改革以后,乡绅们依靠掠夺教会的财产而迅速致富,工商业者也随着经济的繁荣而聚敛了大量钱财。由于经济力量的增长,乡绅和工商者逐渐不再甘心忍受国王的压迫和限制;而地方政府的发展,又增加了乡绅们政治锻炼的机会,于是议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克伦威尔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就发生在查理一世和他的议会的争吵发展到完全破裂的时候。”[1](P9)书中在讲到从共和制向军事专政转变的时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社会上的左翼激进派反对类似君主制的护国公制,但是这种对护国公制的攻击,反而巩固了克伦威尔的地位,因为英国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能够维持秩序和保护财产的政府。克伦威尔就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在赖德洛和巴克斯特的发言中,都清楚地讲到了这一点。[1](P337)以前,克伦威尔是一个旧体系的破坏者,现在却以社会拯救者的面貌出现。从革命开始以来,经过了腥风血雨的反复斗争,才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而从共和制过渡到护国公制,却是和平地、未经过流血的武装斗争。就好像自然界经常发生的变化一样,各阶层人民对克伦威尔独揽大权,建立专政的行为,既不积极反抗,也不积极支持,而是以一种解脱的心情,消极服从。
著者对17世纪革命时期英国军事史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费尔斯说过:“内战不仅是敌对原则之间的斗争,而且也是物质力量的冲突。”[15](PⅦ)曾写了许多有关军事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在1902年出版的《克伦威尔的军队》一书,被认为是至今为止所有关于英国军事史方面最好的一部书。[14](P224)在《克伦威尔传》中关于军事方面的论述,对交战双方,特别是对议会军的战略计划、战术运用、战役过程及结果,以及武器配备、后勤给养、官兵的精神气质,直到战役发生时的环境,包括地形、山川、气候、道路、桥梁等,都作了详尽具体的叙述。特别是对埃吉山、马斯顿荒原、普列斯顿、邓巴、伍斯特等几次大战役,更作了细致入微的记载和分析。
克伦威尔的军队在历次战斗中,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其主要原因为何?书中在有些地方也有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这支军队所以具有旺盛的战斗精神,严格的纪律,是因为组成这支军队的大多数士兵和一部分中、下级军官,都是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人民,并且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具有反封建的决心;把他们的事业看成是上帝的旨意,神圣的使命。克伦威尔身为议会军的统帅,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他曾说:“我宁愿要一个穿着粗布上衣的下级军官,只要他懂得为正义而战并热爱他了解的东西,而不要一个你们称之为‘绅士’,而其他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人。”[1](P96)
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宗教信仰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政治思想也密切地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书中强调,清教是革命事业的核心;认为在克伦威尔那里,“宗教自由比政治自由更重要”。[1](P475)他曾批评克拉兰敦的《英国的叛乱与内战史》一书中“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这书作为一部关于宗教革命的书,但其中关于宗教的因素却被忽略了”。[16](P119)
书中引述了一则轶闻:有一次克伦威尔请画家莱利为他画像,他向莱利说:“莱利先生,我希望你要发挥所有的才能把我的像画得真正像我;不要对我讨好,而要把我脸上的所有粗鲁的样子,粉刺、赘疣等等一切都画上。否则我连一文钱也不给你。”著者接着说:“毫无疑问,护国公会向为他写传记的人发出同样的要求。”[1](P445)统观全书,费尔斯并无隐恶扬善,刻意粉饰之处,包括当时人对克伦威尔所作所为的责骂和贬斥,书中都如实加以列举。如1647年李尔本等平等派人士痛斥克伦威尔为“暴君、变节者和伪君子”;在平等派的一份小册子中写道:“你几乎不能和克伦威尔讲任何事情,他只是将手放在胸前,目光向上,向上帝祈祷,他甚至会在猛击你下面的第五根肋骨的时候,还会悲泣、嚎哭和忏悔”。[1](P244)共和主义者赖德洛等人认为,克伦威尔所作的任何变革,其惟一的目的,无非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本来“国家在短时期内即可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幸福境界的,但只是由于一个人[克伦威尔]的野心,使得所有善良人们的希望都消失了”。[1](P467)书中还列举了克伦威尔在征讨爱尔兰时的残暴行为,使爱尔兰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战争中死亡,一个英国军官说:瘟疫和饥馑遍及爱尔兰全国,在某些地区,“人们走过二三十哩方圆的地方,都看不到一个活的生物;无论是人、牲畜和禽鸟”。[1](P259)对英军在西印度群岛的残暴血腥行为,也有同样的描写。[1](P402)
费尔斯本人也对克伦威尔的一些行为进行了批判。当他讲到1653年克伦威尔依靠武力解散了长期议会时说:“长期议会所代表的立宪政府的理想,终将超过克伦威尔的军人力量……将议会解散,军队将扯掉自己身上一直赖以掩盖其行动的、极其可怜的合法性外衣。”“克伦威尔的一生都试图将军事力量套上宪法的外衣,使它看上去有某种特色,以达到可能改变其面貌的目的,但他失败了。”[1](P319)护国公制建立以后,许多“有良知的人”不再支持他,他新引进的人中,许多都是朝三暮四只贪图个人利益和名位的政客。[1](P477)这些都说明书中并无为克伦威尔文过饰非之意。
然而,我们看到,当费尔斯离开叙述历史事实而对克伦威尔进行总的评价的时候,却说了许多显然是过分的话。如说:“克伦威尔无论作为一名士兵或是一位政治家,都远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英国人都要伟大得多。而他既是一名士兵,又是一位政治家。”[1](P459)又说:“克伦威尔所取得的胜利,更多的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其次才是他的军队的素质。他的军事事业上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起步很晚。……克伦威尔在听到枪声和在指挥一个中队时,已经43岁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未经过军事训练的乡下绅士怎么能打败在欧洲经过最著名的军官专门训练的士兵呢?回答是,克伦威尔具有一种天赋的作战才能。”[1](P460)这种把军事斗争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克伦威尔个人天才的论点,未免过甚其词。军事战争并非如两个棋手之间的对奕,士兵并非无生命的棋子,任凭棋手的调遣。战争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去进行的。任何一个优秀的统帅,如果指挥一个士气低沉、纪律涣散的队伍,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古往今来的军事史都可说明这一点。
看来,费尔斯对克伦威尔评价上的这种天才论,也并非是他刻意要对克伦威尔阿谀粉饰,而是由于费尔斯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社会地位和文化教育的影响。费尔斯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工、商业正迅速发展的时候。宪章运动业已平息,社会相对稳定,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正在全世界各地区扩展。费尔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并在伽狄纳辉格派史学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在他的周围,到处弥漫着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下,费尔斯回顾为英国资产阶级开辟道路,为英国海外扩张创建功业的克伦威尔,当然禁不住会产生欢欣感佩之情。难怪有人说,在伽狄纳和费尔斯笔下的克伦威尔,好像是“穿了乡下服装的格拉斯顿”。[17](P31)
费尔斯的书初版于1900年,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及克伦威尔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经济背景材料。另外,它未能揭示革命所以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注: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书籍,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包括以社会经济变动来解释革命,见C.Hill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ivil War,Puritanism of Revolulion(1986),pp.13-40,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Ja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ⅨⅩ(1959),pp.376-401.)书中说,内战“从未成为一次社会性的战争,而是一场意见和思想之战”。[1](P71)对内战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只停留在当事人以上帝和“神意”所作的借口之上。1647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在伦敦郊区的辩论会上,当辩论到国家政体,关于国王和上议院的地位时,平等派坚持君主制及上议院都必须加以废除,但克伦威尔回答时却说,假如上帝的意旨是消灭国王和上议院权力的话,上帝是能够做到的,无需军队去撕毁协议,使自己声誉受辱;他们应该等待上帝的安排,去执行他们当前明确的职责[1](P176)。后来,克伦威尔又说,关于政府体制问题,“如与基督相比,仅是一堆粪土而已”[1](P178),毫不重要。然而他在与平等派的代表激烈争论时,却死命抱住君主政体和上议院不放。到后来,即使他和独立派其他领导人不再相信查理一世时,他们仍不肯放弃君主政体。1648年春,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领导人讨论了废黜查理一世,让威尔斯亲王或约克公爵接替王位的计划。只是由于亲王不愿意接受而公爵逃到了法国,该计划才未能实现[1](P185)。当1653年克伦威尔建立护国公制,以一种军事独裁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引起国内人士的广泛反对,但克伦威尔用镇压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反对者。一个著名的长老派卡拉米对克伦威尔说:以武力镇压“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在10个人当中将有9个人会反对你”。克伦威尔回答说:“那好,假如我解除了9个人的武装,而把刺刀交到第10个人的手中,难道事情还办不成吗!”[1](P410)可见克伦威尔也很清楚他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现实的物质力量。费尔斯对此未作出深一层的分析。
书中有些章节企图列举事实来否定这次革命的社会阶级斗争性质。如说,在内战双方的阵营都有许多贵族,而且有些贵族的家庭成员分别站到敌对的阵营中。“在埃吉山,登比伯爵和多费伯爵在国王卫队的指挥之下,而他们的儿子费尔丁勋爵和罗奇福德勋爵却在[议会军]艾赛克斯指挥下作战”。在克伦威尔的家庭中,他的叔父和堂兄都是狂热的王党分子[1](P720),接着写道:“总的来说,这次战争是以光荣的人道的方式进行的……,除了在战争激烈的时候,很少发生流血的情况。”[1](P73)对此,应该指出,上层社会人士及其家庭成员分别参加到敌对阵营的状况,并不能作为否定革命的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因为一方面少数事例不能一概应用到整个社会上去,类似上述的情况,不仅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有,即使在以后的许多次大革命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另一方面,队级出身,不能作为划分革命中阶级界限的惟一标准,还应研究某一社会阶级出身的人其经济来源及其社会关系等因素,有些贵族出身的人,其经济来源是从事资本主义经营。[18](P17)这样就不能只按其阶级出身来解释他在革命中的立场。特别是在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因素深入农村,大批贵族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成为“新贵族”,他们站在反封建王党的革命阵营,就不足为怪了。另外,还必须考虑革命斗争双方的纲领及其实际影响。如果制订的纲领是打倒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那么拥护这个纲领的人,即使是出身于贵族,也是属于资产阶级阵营的。(注:近年来,有一批英、美历史学家列举历史资料,否定对17世纪英国革命的社会阶级分析,特别是所谓的“修正派”历史学家,把传统的史学观完全否定。甚至也否定了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些观点已引起另一批历史学家的反驳,论战正在进行之中。)
费尔斯只用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冲突来解释17世纪的革命事件,对一些历史现象的实质未能深入分析,受到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当代一个历史学家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历史学家伽狄纳和费尔斯的研究方法的严重局限性,可以说并不仅在于他们对经济的缺乏兴趣、对阶级作为历史动力的缺乏了解,而且他们对在近代社会中的宫廷[在朝]和乡村[在野]的紧张关系相对忽视;同时他们对等级、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这些对当代人都是熟知的重要性也认识不够。”[19](P26)
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作为中等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站在政治斗争的中间立场上,在他右边的有封建王党和长老派,在他左边的有平等派等激进民主派。他左右两方都有敌人和朋友,随着斗争的发展,敌友也不断变换。费尔斯作为一个中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在思想感情上和克伦威尔声息相通。他既对克伦威尔反对封建王党给予积极评价,又对平等派等激进民主派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反感。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对平等派领导人李尔本的评价上。书中对李尔本的评论只用了寥寥几句话,而且是用了含混的冷冰冰的语气,说李尔本是“精力充沛的演说家和极为固执、勇气非凡的党派领袖”[1](P240),在另一处,即他在《英国名人传记词典》中关于李尔本的条目内容比较详细,但一方面说李尔本“时刻准备牺牲自己去攻击任何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又说“他的激烈的利己主义,使他成为一个危险的斗士,他经常地由于个人的愤怒而牺牲公众事业”。[20](P75)这种评价,受到了伯恩斯坦的反驳,后者认为费尔斯的评论不公平,因为“李尔本争论的发言,都是为了重要的公众利益”。[21](P162)
费尔斯在书中不但对平等派评价加以贬抑,而且显然对他们的作用不加重视。1647年秋,平等派对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的保守政策日益不满,即在10月15日拟订了自己的一份纲领《军队事业》。其中心思想是论述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要求废除王权和上议院,同时提出一些社会经济改革的要求,如停止圈地,将已被圈的土地归还农民,废除专卖权,取消什一税等。[22](PP196-222)《军队事业》的内容和独立派已在此前拟订的《军事建议纲目》有原则的不同,至此,平等派和独立派的分歧日益激化。克伦威尔在议会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对《军队事业》作了百般攻击[23](P512)。为了抑制平等派思想的蔓延,克伦威尔提议在1647年10月至11月8日在伦敦郊区的普特尼教堂召开会议,由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代表参加。会上围绕平等派拟订的新的更重要的纲领《人民公约》展开争论,中心问题是国家政体即国王和上议院的地位和选举权即实行普选权或者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问题,双方展开互不相让的激烈论战。从政治、思想角度来看,这次争论是17世纪英国革命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它不仅对当时的革命发展,而且对以后一段英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对克伦威尔本人来说,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以费尔斯的学力和思想水平,他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且,更令人注意的是:普特尼会议争论的详细记录,即有名的“克拉克文件”是经过费尔斯亲手仔细整理加以出版的,(注:1647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议会在伦敦郊区的普特尼教堂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和平等派代表就国家政体军问题和选举权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全军会议的秘书威廉·克拉克用自己的速记方法记录了这次会议的发言,后来,克拉克在担任驻苏格兰的蒙克将军秘书时,利用空暇将速记稿整理复原。1891年费尔斯又将此稿细加整理出版,是为《克拉克文件》(Clarke Papers)。1938年伍德豪斯又将《克拉克文件》编选注释,以《清教与自由》一卷本出版。A.S.P.Woodhouse,Puritanism and Liberty.参见G.E.Aylmer,The State's Servants (1973),pp.261-262).)他对会议的全部内容一定知之甚详,然而奇怪的是,他在《克伦威尔传》中,对此事的论述却不够详细具体。另外,他在书中说,在这次辩论会上“最后还是克伦威尔获得了胜利”[1](P179)。这也是不符事实的。(注:在10月28日至11月8日举行的普特尼辩论会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各自坚持立场,未取得一致意见。会后,11月11日与会的平等派代表赛克斯比等15人在伦敦署名发了一份“若干鼓动员致他们团队的一封信”(A Letter from Several Agitators to their Regiments载A.S.P.Woodhouse,Purtanism and Liberty,p.452),其中说,会上经过长期争论通过了平等派在《人民公约》中第一条提出的关于普选权的要求。这信在会后不久在伦敦公开散发,可见不会是杜撰的,然而在会议记录《克拉克文件》中却没有会议对选举权表决的记录,究竟是何原因?是独立派高级军官将这天记录撕毁,或是这天会议秘书克拉克因事未记,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疑案。不过,在这次会议上,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未取得胜利,则是肯定的。参见拙著《欧洲史论》第202页。)
和对上述一些过于粗略的记述相比,书中对查理一世被送到断头台斩首一事的记述却无微不至,而且是带着对受难国王的深切同情的笔调[1](PP223-226)。当写到1649年2月9日埋葬国王遗体时,引述当时人的记载说,天空原来是晴朗的,但很快开始下大雪;黑丝绒棺布上被厚厚地盖上了雪,并完全变成了“纯洁无邪的”白色。这对送葬者来说,“似乎上天作出了一个象征,以表明他们死去的君主是清白无辜的”[1](P226)。这样的词句,不仅表达了作者对“过激”的流血事件的反感,也反映了他保守的政治立场。
书中有个别地方,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史实不太确切。如关于1647年5月底6月初,议会军的掌旗官乔伊斯带领骑兵前往关押国王查理一世的霍姆比城堡,把国王押解到军队驻地纽马凯是根据克伦威尔的命令[1](P160),而美国学者阿勃特则认为,“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以肯定或否定克伦尔在这个事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23](P452)但根据具体资料,乔伊斯离开纽马凯前往霍姆比城堡时,克伦威尔正在伦敦。乔伊斯在霍姆比城堡抓到国王那一天,克伦威尔才离开伦敦。当费尔法克斯听说国王被抓到纽马凯军队驻地时,立刻派了三个连队来保护国王,而克伦威尔是支持费尔法克斯的这一意见的。克伦威尔写信给护送国王回去的华莱说:“要用除了武力之外的一切办法使陛下回去。”但因为国王不愿回到霍姆比城堡,这一命令才未执行。根据这样的情况来分析,这事不可能是由克伦威尔下令进行的。另外,关于1648年12月6日“普莱德清洗”时,从议会中被驱逐出去的人数,当时人的回忆录和各种记载,说法不一,因而后世各种著作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本书说,12月6日“普莱德上校和一些带枪的步兵阻塞住下议院的大门,抓住某些想要进入的议员,并用武力将另一些议员赶回去。这样的行动持续到7日,共逮捕了45名议员,有96名其他议员被赶走”。[1](P210)但根据现代学者对各种资料考证,除了那些被囚禁起来的议员,被阻止在议会之外不得进入议会的议员共186人。[24](P212)
三百多年来历史学家对克伦威尔的评价,各色各样,极不相同,当代一个历史学家讲到这一现象时说:“历史学家给了我们许多不同的克伦威尔。”[6](P517)费尔斯这书对克伦威尔的评价,也只能看成是“许多不同”评价中的一家之言。不过,这书虽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整个来看,它至今仍然是同类著作中一本高质量的古典性的史学名著。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一点反倒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的,即任何一个人在观察历史的时候,都不免会把自己在现实社会中体验到的思想感情用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去。对克伦威尔评论的史学也充分反映了这种现象。本世30、40年代,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曾把当时对法西斯独裁暴君的憎恨,施加到对克伦威尔的评价上。1937年英国出版了两本克伦威尔传记,一本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独裁者的悲剧》(M.Taylor,Oliver Cromewell,A Dictatir's Tragedy,1937);另一本是《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M.Ashlcy,Ch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1937)。在意大利30年代出版了一本《克伦威尔传》(E.Momigiano,Oliver Cromwell,1932),人们在这些书中可以看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身影。在丘吉尔所写的《英语民族的历史》一书中,有关克伦威尔时代的章节,也是在1938-1939年写的,书中把克伦威尔“或多或少地当成了20世纪的独裁者”。[26](P25)不过,丘吉尔富有政治经验,他知道,克伦威尔毕竟是生活在三百年以前,不能把他和当代的暴君相提并伦,所以后来他在书中告诫人们:“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的独裁者不是一种类型”;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政治罪行而被处死,也没有发生过不经审判而长期监禁人的事。[26]如果把克伦威尔与现代的独裁暴君机械地相对比,则不仅歪曲了克伦威尔,也冲淡了现代暴君血腥残忍的面目。我们在评论克伦威尔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到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中,从本质上去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