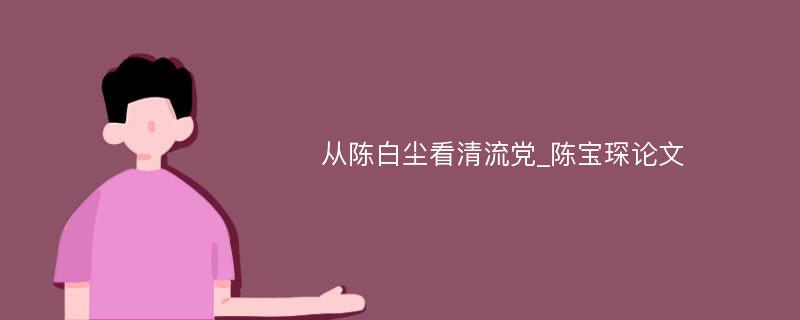
从陈宝琛论清流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流论文,陈宝琛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恍然。”(注:陈宝琛:《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摹本》, 《沧趣楼诗集》卷六第15页。)这是陈宝琛在清王朝正趋灭亡的辛亥年(1911年)春天写下的诗句。星转斗移,沧桑变迁,朝代兴亡,仕途沉浮,给他留下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在他已觉恍然的同光时代,他究竟做了些什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印迹?却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和探究的。
一、清流要角
陈宝琛(1848—1935年),福建闽县人。 曾祖陈若霖乾隆丁末(1787年)进士,历任知府、四川盐茶道,官至云南、广东、河南、 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卒。祖父景亮官至云南布政使。父亲承裘任刑部郎中。在这样显赫的官宦人家中,陈宝琛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治四年(1865年),宝琛中举人,三年后,中进士,在翰林院供职,“校书中秘,粗窥柱下之典章乘传”。以后又充日讲起居注官,任右春坊右庶子。至光绪九年(1883年)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第二年因丁忧守制回籍,直到二十五年后才重新回北京任官。
陈宝琛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清王朝标榜“新政自强”的同治、光绪时代。刚刚从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民众起义烽火中喘息下来,清王朝又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内战,民主凋敝,吏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满汉地主阶级之间权力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派系之间围绕着统治权力的分配以及如何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矛盾重重,斗争激烈。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独裁权力还处于向慈禧太后集中过程中,她还无法完全控制朝局。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从翰林院中涌现出了一批勇于议政、抨击时弊的文人,“几几乎有宋元祐之风,一时遂有清流党之目。”(注:朱祖谋跋:《涧于集》奏议。)陈宝琛即成为清流党的重要人物。 ”当是时,公(陈宝琛)与宗室侍郎宝廷、张学士佩纶、张文襄之洞并以直谏有声天下,想望风采,号为清流。”(注:陈三立:《赠太师陈文忠公墓志铭》,《碑传集三编》卷八。)
陈宝琛并不是所谓翰林“四谏”之一(注:黄浚一度认为“四谏”指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 张之洞(见《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7页),后又无确考(同书第129页)。 《红柳庵诗话》、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中译本第3册第490页)则认为指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但陈宝琛自己认为,“四谏”之名,“时称张(佩纶)、宝(廷)、何(金寿)、黄(体芳),文襄尚未在讲职也。”(《沧趣楼诗集》卷7页6。)看来“四谏”得名于张、宝、何、黄同任侍讲学士之时,陈宝琛、张之洞后来之所以被误为“四谏”,不仅是因为他们后来担任了侍讲之职,而且也以犯颜直谏著名于世。),在清流党中,交往最密切的是张之洞、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于同治二年(1863年)入翰林,四年之后,陈宝琛、宝廷同入翰林,因此,陈宝琛与张之洞“订交最早,情文相生”(注:徐一士:《一士谭荟·陈宝琛》。),“接膝京师,谬引同志”(注:陈宝琛:《张文襄公墓志铭》,《碑传集补》卷二。)。至1882年初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他们之间有长达近十五年的密切交往。宣统三年,因张之洞竭力推荐,陈宝琛官复原职。不久张之洞在京去世,他悲痛异常。在祭文中写道:“吾之交公也以天下,哭公也亦以天下,而无所谓私。独以三十年之离索,犹及生存数面,濒危一诀,差亦非人之所为。”
同治十年(1871年)张佩纶入翰林,陈宝琛与他的友谊与日俱僧。仅以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上旬的记录为例,即可见一斑:
十月初一日:夜,伯潜(陈宝琛字)前辈来谈校《文文忠祥传》。
初四日:早过伯潜前辈、实孚、汝翼,均少谭即返。
初五日:晚伯潜前辈至,……去已月午矣。
初八日:晨过伯潜。
初十日:与伯潜夜谭。这样频繁地往来,彻夜长谈,可见情义深笃。1903年,张佩纶去世的消息传来,陈宝琛痛哭流涕,“特千里唁之”:“雨声盖海更连江,迸作辛酸泪满腔。一酹至言从此绝,九幽孤愤孰能降!”(注:陈宝琛:《入江哭篑斋》,《沧趣楼诗集》卷三第1页。)“君才十倍我,而气亦倍之”(注:陈宝琛:《检篑斋手札怆然有感》, 《沧趣楼诗集》卷三第3页。),为张佩纶的遭际而惋惜、而悲愤。
二张系军机大臣李鸿藻最为亲信之人。当时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之谐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90页。)从陈宝琛与二张的关系看,在重大问题上不可能不受李鸿藻的影响。陈宝琛十分清楚,“与文正(李鸿藻)常过从者,为二张,文襄与篑斋也。二君与文正,或为戚属,或为前后辈,谊不能自远”,他自称“生平谒文正仅二次”。虽然如此,“沧趣(陈宝琛书斋名)之于光绪初有局,其分野何属,似未能脱高阳(李鸿藻)二张之范围也”(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64—65页。)。这个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
与陈宝琛气类相投的还有宝廷、吴可读等。这是两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吴可读《请免外国使臣跪拜疏》向来被视为顽固的代表作,其实它充满了机智、讽刺和作者的个性。它完全使用了顽固派的语言和逻辑,却推导出了与顽固派截然相反的结论。接着又主张“其事又不足以争”,“度吾时未可与争,势未可与校,则当别求吾自强之道。”而这“别求吾自强之道”,正是洋务派的主张。这份奏折以嘻笑而荒诞的语言、敏捷而机智的思路满足了顽固派与洋务派双方的需要,解决了盈廷聚讼半个多世纪而迫在眉睫的外交难题,功不可没。光绪五年(1879年)他又以尸谏请为穆宗立嗣,给慈禧太后出了个大难题。陈宝琛对吴可读的风节十分佩服:“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有“我交侍御恨已晚”(注:陈宝琛:《吴柳堂御史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沧趣楼诗集》卷七第16页。)之句。宝廷“生平多欲程朱之书”(注:《长白先生奏议》卷首,年谱。),但生活放荡不羁,淡于功名利禄,最后以游妓自劾罢官。陈宝琛认为他“数年来忠谠之言,隐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当不为一眚所掩。”(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58页。)宝廷晚年生活落魄,饮酒过度,宝琛劝他“垂老可应思止酒,无官端不为忧贫。”宝廷死后,宝琛思念老友,还想再看一下宝廷留在鼓山上的题句,竟寻觅不得,意甚怆然。“国门一出成今日,泉路相思到此山。……飘零剩墨神犹攫,剔遍荒苔夕照间。”(注:《沧趣楼诗集》卷一第1、5页。)在宝琛悼念张佩纶的诗句中,还把宝廷与张相比较:“竹坡(宝廷字)最坦率,君亦任纯真”(注:陈宝琛:《检篑斋手札怆然有感》,《沧趣楼诗集》卷三第3页。),可见交谊之深厚。宝廷与二张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由其子寿富受业二张门下可见一斑。
陈宝琛在翰林院期间,主要就是与这样一些清流名士密切交往,互相提携,砥励气节,抨击时弊。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徐一士谈到,“陈于同治间入翰林,光绪初年,与之洞及张佩纶、宝廷等同为清班中最以敢言著者,主持党议,风采赫然,锋棱所向,九列辟易”(注:徐一士:《一士谭荟·陈宝琛》。)。他们的政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流党人的基本政治倾向。
二、词苑直臣
陈宝琛在翰林院期间,几乎参与了清流党所有重要的活动。他的主张,基本上体现了清流党对如何摆脱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困境的回答。
第一,提倡士大夫气节,整肃纲纪。“光绪初元,孝钦后秉政,任用老臣。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注:李肖聃:《星庐笔记》第16页。)加以捐班充斥,吏治更加腐败。“清流”就是针对这股“浊流”而兴起的。陈宝琛认为,对官吏的奖惩处分,“轻重之间,有关臣僚风气甚巨”。他与其他清流一样,把整肃纲纪视为要务,即便是君父懿旨,如有不合,也敢于“抗疏沥陈”。他指斥副都御史程祖浩“见一尚书侍郎卑躬屈体”,“其志气风骨均不足以表率台僚”。“风宪之地,纲纪攸关,诏书诰诫,必及言者。倘使柔媚者据高位,则在下科道诸臣相习成风,志气衰靡,日即消亡,必至无一人敢言。”万青藜以“三经参劾之身而靦然为六曹长”,“以顽钝无耻之人、背公营私之辈,既不足以董正僚属,又安望其长育人才。”两江总督刘坤一“嗜过好深,广蓄姬妾”(注:王玉棠:《刘坤一评传》认为,这一时期刘坤一的表现“实与一般守旧派官僚无异。思想保守顽固,不愿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愚昧地排斥新兴事物。”而受到弹劾罢官,则主要是因与李鸿章在政坛上争衡。但就陈宝琛此奏而言,与李、刘争衡并无什么关系。)。即使对军机大臣宝鋆,也公开指责他“屡次请假在危疑扰攘之时,畏难巧卸,不恤成败,接见僚属,谈笑恢谐,全无至诚忧国之色。”(注:陈宝琛:《星变陈言折》,《陈文忠公奏议》卷上。)庚辰午门一案,尤显陈宝琛犯颜直谏的勇气。光绪五年(1879年),慈禧遣太监去醇王府送礼。太监违制出午门,为值日护军阻止。太监恃势动武,并向慈禧诬告。慈禧便向慈安“哭诉被人欺侮,谓不杀此护军,则妹不愿复活。慈安怜而允之。”刑部在两宫太后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曲法拟流”(注: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附杂记数则。),但慈禧仍觉所判太轻,命将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右庶子陈宝琛决心“上书极谏”,左庶子张之洞也表示支持,另片上奏,并劝宝琛“措词不宜太激,张佩纶则认为“精义不用可惜”,宝琛遂仅“改正义为附片”(注: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六年。),原疏抗争,认为“二百年中,但有太监犯罪而从严者,断无因与太监争执而反得重遣者。”因此,“本朝宫府肃清,从无如前代太监假威福之事。”要求特旨饬谕内务府约束太监,“如有骄纵生事,不服稽查者,必当从严惩办。”附片更奏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不再加重处罚午门兵丁(注:陈宝琛:《请申明门禁折》、《密请懿旨特宽午门兵丁罪名片》,《陈文忠公奏议》卷上。)。当时恭亲王奕 “手张、陈两疏示同列曰:‘此真可谓奏疏矣!’”(注:《抱冰堂弟子记》。)疏上之后,如石投水,留中数日后,慈禧太后终于改变态度,“谕此案可照原议,毋庸加重。”陈、张奏章虽然没有改变刑部在慈禧太后淫威下“曲法”的结果,但毕竟对其肆意妄为有所扼制。
第二,支持洋务运动。据何刚德回忆,“当中法未战之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钞之。”(注: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第33页。)陈宝琛的洋务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光绪七年(1881年)写的《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中(注:《陈文忠公奏议》卷上。)。他充分论述了办洋务的重要性,认为“洋务至重也,办洋务至公也。以至公之心,办至重之事,非遍天下人知之,合天下人谋之不可”。因此,“务使朝廷上下尽识夷情”,在这“既开数千年未有之局”中,“图数千年未有之功”,表现了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针对举国上下对外国时事茫然无知的情况,陈宝琛把“知外事”列为洋务六事之首。他还对清政府的外交机构设置、人才选拔、外交政策制订程序等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建议。他认为,总理衙门大臣由军机大臣兼任有“操纵难施”、“才力不及”之弊,应改设通商院,“位六部下,理藩院上”。总理衙门章京改为曹属,“与其按国合股,不如因事立司。责任较专,规制亦协部曹。”其司职人员,“无非熟于洋务之人。”他建议,“嗣后各国修约期近,明诏中外臣工,令咸得条议,或人自为议,或数人一议,不议者听。部院司员、外省官绅县说帖呈长官代奏。”这样集思广益,其利有四:一是“聚天下俊才各抒所见,必有以补总署诸臣智虑所不及。”二是“外国决疑定计,必下议院。《烟台条约》借口商情不便,至今未行。则彼有所求,我亦可援臣民之言以折之。”三是可以“破除成见,屏黜空言,风气日开,人才辈出。”四是朝廷“即所议之优绌,别其才识浅深,以备缓急之用。”这种决策民主的思想是陈宝琛从西方议会制度得到的启示。他急切地希望进一步了解西方,认为“今日情势,中外交涉之事,有日增,无日减,所最急者,能周知情伪之人耳。”中国外仅二、三使臣,学童出洋“易为异俗所化”,主张派翰林院中“年力强盛、志节端亮者或十人或十数人,给其廪饩,留其资俸,令游历各国,毕览其山川政教土俗民情”,“如是则十数年后必有一二卓绝者明审彼中情伪而得所以驾驭之方,则洋务永无乏才之虑也。”清流党人的用世之心,跃然纸上。他还针对中外“斗争词讼之事”日益增多的情况,建议“参合中西律意,订一公允章程,商布各国,勒为科条”。这一主张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侵略者的治外法权,但对于克服“华人用华律、洋人用洋律”、“洋律畸轻,华律畸重”的弊端,促使我国法律的改革与进步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80年代初,陈宝琛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自造铁路”的主张(注:《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六第31页。)。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陈宝琛在代刘铭传拟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注:见《陈文忠公奏议》卷上,《刘壮肃公奏议》卷二。)中高度肯定了建筑铁路对于国家经济和国防的重要意义。奏折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在国防上,“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在经济上,“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奏折大胆地建议,建造铁路的资金,可以通过筹借洋债来解决。这份奏折递上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大论战。
对于顽固派之误国,陈宝琛痛心疾首。在《请收回琦善专祠成命片》中,陈宝琛强烈地抨击了顽固派:“设当初起时,琦善稍有人心,力图搘柱,则彼方畏威怀德不暇,何至侵陵觊伺,日甚一日,蔓延而不可收拾也。”“今天下议论洋务者,言及琦善二字,虽孺子小夫,莫不疾首痛心,同声唾骂,目之为祸国之罪魁。”(注:《陈文忠公奏议》卷上。)奏片之起,虽然是因陕甘总督杨昌浚奏准为琦善设立专祠之事,但从当时顽固派竭力阻挠和反对,以至朝廷明令“铁路断不宜开”来看,陈宝琛此片的确是有感而发,有愤而发的。中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计划整整被推迟了十多年,失去了自主建造铁路的机遇。
第三,坚持抵抗外来侵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边疆危机普遍发生之时。围绕着如何掌握外交主动权以摆脱危机,清流党人的立场既不同于顽固派昧于大势、盲目主战,也不同于奕、沈桂芬、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忍让妥协的路线。
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之后又入侵琉球。1879年乘中俄伊犁交涉之际,日本吞灭了琉球,随即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朝鲜。这使清政府重新面临“海防”与“塞防”如何兼顾的问题。有不少人主张与日本迅速了结琉球案,通过向日本示惠忍让以瓦解日俄联合,从而赢得与俄在伊犁交涉上的成功。陈宝琛全面分析了中、日、俄三国间的外交形势,认为“中国之力终不能禁日本之通俄,日本之亲我与否,亦视我之强弱而已。中国而强于俄,则日本不招自来;中国而弱于俄,虽甘言厚赂,与立互相保护之约,一旦中俄有衅,日本之势必折而入于俄者,气有所先慑也。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便者,又势所必至也。”也就是说,无论中国与日本有无盟约,日本趁中俄交恶扩张势力势所必然,因此,中国首先必须“专意俄事”,然后“拥未撤之防兵、待将成之战舰,先声后实,与倭相持。”他把收复伊犁,“匡复琉球”,视为“中国自强之权舆、洋务转折之关键也。”(注:陈宝琛:《论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改折》,《陈文忠公奏议》卷上。)这是一个塞防与海防并重,以塞防促海防的外交方略。
但正是在这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崇厚却与俄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自然引起了清流党人以及清政府中其他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等坚决主张惩办崇厚、重订条约。陈宝琛有关这一事件所上奏折,《陈文忠公奏议》只收入《论俄事界务商务宜并争折》、《附陈俄军情形片》、《请明功罪以示劝惩折》三件,但实际上,陈与二张的奏疏是一体的。据陈宝琛回忆,“自俄事起,公(张之洞)及张幼樵(佩纶)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注: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六年。)三人“前后疏二十余上,卒将崇厚所订十八条全废。”(注:《抱冰堂弟子记》。)清政府最后改派曾纪泽与俄重新谈判,多少挽回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败。俄事交涉的转机,也使清政府转变了对日本的态度,废除了中日间达成的初步妥协。
为了加强塞防和海防,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陈宝琛又呈递了意义重大的《论东三省、台湾宜慎简贤能折》,建议在东三省仿行内地的制度,将军加督抚衔,以便满汉官员兼用;福建督抚同城,将巡抚移驻台湾;新疆底定之后,“宜早建行省,以策久安”。新疆、 台湾于1884、1885年相继建立行省, 而东三省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才改建为行省。
1883年,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前线浴血抵抗,清政府则举棋不定。陈宝琛批评政府“谋越太疏、御法太怯,先机屡失”,坚决主张立即出兵支援刘永福,“设令援绝力穷,在越南则坏其长城,在中国则失一前敌,因循坐误,虽悔何追”!(注:陈宝琛:《请急越南折》,《陈文忠公奏议》卷下。)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法必战的原因。第一,法国之侵占越南,目的在于进一步入侵中国,“假如法竟有越,则琼州孤岛,唾手可取,广东各口,一苇即达。”第二,如果中国示弱于法,列强的“日肆凭陵”将有增无已,“沿海之边隅皆越南也”,“环瀛之雄国皆法人也”。第三,“外侮不祛,内患将作”,洋务自强失去其实际意义。第四,中国具有战胜法国的有利条件:法人新得越南,人心未附;法兵伤歼甚众,兵力不厚;法人兵费十倍于中国,饷源难以为继。他告诫清政府,“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道咸以来,覆辙具在,不远之鉴也。”(注:陈宝琛:《论越事不可中止折》,《陈文忠公奏议》卷下。)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改变以守求和的外交方针,掌握最高统治权力的慈禧太后则利用前线失利的形势,清除恭亲王奕的势力,并采取“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的阴谋,向清流党开刀了。
三、清流党与李鸿藻
在讨论陈宝琛及其清流党在这一时期政治作用时,不能不涉及到他们与李鸿藻的关系。李鸿藻号称“领导清流”,“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注:李宗侗、刘凤翰:《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288页。)。李鸿藻为什么能对清流党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呢?能不能仅仅以南党北党之争来解释呢?
清朝政府内部存在党派、门户之争,这是封建政府的固有弊病。以李鸿藻为首的北党与以沈桂芬为首的南党之间的纷争,除了权力之争外,更多的是“以政见异同”(注:《清史稿》卷四三七,赞论。)引起的。这种“政见异同”并不能简单地以顽固派和洋务派为标准而断明其是与非。
李、沈党争往往因对外政策主张歧异而激化。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奕、文祥等人即制订了严守和约、徐图自强的内外方针。但自七十年代中以后,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列强侵略要求的扩大,严守已有和约的政策实际上已不可能。奕、沈桂芬等推行了一条退让、妥协的外交政策,而李鸿藻则主张采取强硬的抵抗政策。 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兰孙(李鸿藻)以津事与宝(鋆)、沈(桂芬)两公争于上前”(注:《翁文恭公日记》,同治九年六月十九日。),因李在军机处势孤力单,天津教案以诛民流官、崇厚赴法道歉了结。在收回伊犁的对俄交涉中,“沈桂芬主崇厚议,鸿藻不可,争于廷,持之甚坚。卒治崇厚罪,遣使改约。”(注:徐世昌:《李鸿藻传》,《碑传集补》卷一。)在这些重大外交问题上,李鸿藻的立场是可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李鸿藻的坚持和清流党的努力,促使了清王朝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初外交政策方面出现了某种转折。李鸿藻之所以能得到清流的拥护,对外政策上立场相同,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李鸿藻具有敢于直谏、正色立朝的封建大臣风范,也是为清流所仰慕的原因。如在诛太监安得海问题上,“恭邸(奕)、文(祥)、李(鸿藻)两公颇持谠论,事遂决。”(注:《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八年八月初六日。)在谏阻重修圆明园时,李鸿藻也是敢忤旨意,“始终争执,事竟得止”。(注:徐世昌:《李鸿藻传》,《碑传集补》卷一。)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人弹劾大臣、犯颜直谏的风骨与李鸿藻如出一辙。李之于沈桂芬,党争虽然激烈,但不同于封建官场中那种毫无廉耻的倾辄。慈禧太后曾听信荣禄谗言,借口放沈桂芬为贵州巡抚。但恰恰是李鸿藻“坚不承旨。谓本朝从无以军机大臣、尚书出任巡抚者。沈桂芬在军机多年,并无坏处,臣等皆深知之。如太后不收回成命。臣等万不能下去。”(注: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二,第46页。)慈禧太后最终收回成命。这种为政敌而抗旨的风节,在封建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李鸿藻与清流党一样,崇尚理学。李鸿藻“性至孝,为学守程朱,务实践,不苟言笑,持躬勤约,有若寒素,与倭仁最善,以道义相切。”(注:徐世昌:《李鸿藻传》,《碑传集补》卷一。)清流党人也是以“维持名教为己任”,对洋务派“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极为不满(注: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清流党》。)。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人都有很深的理学修养,提倡看《近思录》、《程朱文集》等“第一等书”,并耻于“读而不践”(注:《长白先生奏议》卷首,年谱。)。他们之抨击时弊、犯颜直谏的勇气,未尝不得益于他们的理学修养。但作为年轻一代的理学家,他们并没有站在顽固派的立场上,拒绝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提倡名教是并行不悖的。“变法储才”(注:张佩纶:《涧于日记》庚辰下,第1页。)是“定天下之大计”的两个方面。合格的洋务人材必须具有高亮的风节。他们对于“吏治日偷”(注:宝廷折,《光绪朝东华录》总483页。)的抨击和对洋务企业腐败现象的揭露,都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而进行的。由此也确定了他们与顽固派在政治上的分野。李鸿藻由恪守理学门户而变为变法维新的敌人;张多洞则成为洋务派的后劲,在思想上虽然落伍于康梁维新派,但政治上仍不失为维新变法的同盟者。即使脱离政坛达二十五年之久的陈宝琛,在资政院开院后,即“请昭雪戊戌六君”(注:李肖聃:《星庐笔记》第20页。)。清流党与其后台李鸿藻思想水平之差异无论在甲申之前还是在以后都是显而易见的。
四、宦海风波
清流党人在同治末、光绪初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清王朝统治二百余年来“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创了文人公开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新风气,对于清王朝苟且偷安、吏治日坏、纲纪废弛的腐败趋势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作为没落封建王朝的补天派,赤手空拳的清流党根本无力支撑行将崩溃的封建统治,无法阻挡封建末世的滚滚浊流。甲申年(1884年),是清流党人的祭年。
清流党人于甲申年被赶出政坛,是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长期矛盾冲突发展的结果。
清流党人以整饬吏治、力挽颓风为己任,到处弹劾贫官污吏,为朝野瞩目,不可避免地引起官场的恐惧与仇恨。张佩纶去陕西查办事件,“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陈宝琛的弹劾对象也是上至军机大臣,下至封疆大吏。虽然他们“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称人意”,但他们既以道学家的理想来澄清封建官场上人欲横流的污泥浊水,也就不免“苛以责人”(注: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第8页。)。至甲申年,朝廷内外对清流党人已是侧目而视、踵足而立,既恨之,又畏之。
同治末、光绪初,正是慈禧太后加紧集中权力的时期,迫切需要立威以驭御臣下,制服强悍的督抚。清流党人在弹劾贪官污吏时,“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意,故所言无不行。”(注: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第153页《张佩纶》。)但是清流党人并非慈禧太后随意支配的工具。在宫廷内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斗争中,清流党人往往是支持奕。“盖同治末年,大乱初夷,群有致治之望。其时柄政者为李高阳及恭邸,而清流实隐佐之。”(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63页。)对于慈禧太后一些破坏朝制的恣意妄为,清流党人更是公然抵制,大有不收回成命誓不甘休之势。这些都不可能不使慈禧太后衔恨于心。
第三,由于师门、地缘、辈份的不同,在清流内部发生了分裂。“君子不党”,这种分裂使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实践之间发生了深刻的矛盾。1880年沈桂芬去世,南北党争告一段落。1882年翁同禾以帝师入军机处。“佐常熟(翁同禾籍隶江苏常熟)者,亦为后起之名士,盛伯熙(昱)、文芸阁(廷式)、王可庄(仁堪)、丁叔衡(立钧)、张季直(謇)等是。”(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63页。)由此而形成了所谓后清流党。翰林院本为清闲之所,出路也多,“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但至光绪年间,“馆选太滥,人才拥挤,……平均牵算,每人约须九年可得一差。”(注: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第3页。)利用师门、地缘、辈份等各种关系竞争升迁和放差的机会,演变成了党同伐异、互相倾辄的门户之争。在甲申年,前、后清流的冲突也激化了。
1882年,李鸿章因丁母忧守制百日,由两广总督张树声调署直隶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在京专意结纳清流,为乃翁博声誉。”(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31页。)于是,张树声上奏请调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此事为陈宝琛参劾,谓疆臣不应奏调天子近臣(注:见《陈文忠公奏议》卷下。),事成僵局。张树声请王仁堪之弟王仁东“求解于张侍讲(佩纶),猝不得见,又意相牾也。”(注:陈毅:《李文正公家传》,《碑传集三编》卷一。)“树声甚恐,颇虑其挟恨为难,非排去不安。”而张佩纶后台为李鸿藻;欲去佩纶,非先去鸿藻不可。于是,王氏兄弟与张华奎说动盛昱,上疏弹劾军机大臣,“并劾丰润君(佩纶)保徐延旭之谬,又牵连及于高阳之偏听。”(注:《翁文恭公日记》甲申三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借题发挥,乘机解散以奕为首的军机处,最终清除了奕的势力,完成了独裁权力的集中。“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太后又下旨将张佩纶、陈宝琛和吴大澂分调会办福建海疆、南洋和北洋事宜,“用违其才”,张佩纶因闽江失事而被罢官,而陈宝琛则以前保唐炯、徐延旭临阵脱逃,照滥保匪人例,降五级调用,后以丁母忧回籍守制,“终德宗世,不复出。”
前期清流党随着张佩纶、陈宝琛的罢官而失败,朝廷上下弹冠相庆。后期清流党则更深地卷入了统治阶级最高层的斗争—帝、后党争中去了。甲申年,由此而成为清流党的祭年。
标签:陈宝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花随人圣庵摭忆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张之洞论文; 同治论文; 慈禧论文; 张佩纶论文; 光绪论文; 陈文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